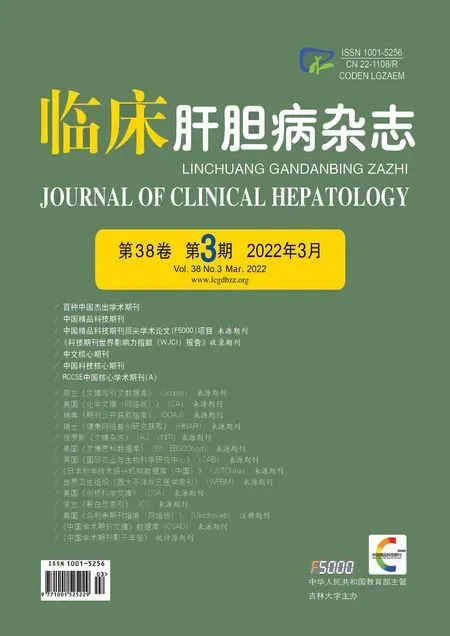肝癌術后重癥患者圍手術期低血壓的危險因素分析
王 斌,梁漢生,馮 藝,安友仲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a.重癥醫學科,b.麻醉疼痛醫學科,北京 100044
2020年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癌癥統計數據[1]顯示,我國肝惡性腫瘤發病超過41萬例,占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第5位;死亡人數高達39萬,位居我國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第2位。外科手術是目前治療肝癌的主要手段[2-3]。隨著越來越多復雜的肝癌術式進入臨床,更多危重患者有機會接受手術治療。此類手術創傷大,病情復雜,圍手術期循環不穩定和低血壓是導致患者病情重、預后差的重要因素[4],術后多轉入重癥監護病房(ICU)。目前,針對肝癌術后轉入ICU重癥患者圍手術期低血壓的相關研究尚不多見。本研究旨在通過回顧性分析肝癌術后重癥患者的臨床資料,明確圍手術期低血壓發生的危險因素以及圍手術期低血壓對預后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4年1月—2019年12月于本院因原發性肝癌或轉移性肝癌行手術治療后轉入ICU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入院診斷為肝癌并行手術治療;(3)外科手術后轉入ICU繼續治療,慢性健康與急性生理評分≥10分。排除標準:(1)資料不全者;(2)圍手術期發生麻醉意外或呼吸心跳驟停等意外事件者。肝臟手術類型主要為肝部分切除和少量右半肝切除、左半肝切除、肝中葉切除等。將術中或術后需要血管活性藥物(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苯腎上腺素、腎上腺素)持續泵入維持血壓者納入低血壓組,其他患者納入非低血壓組。
1.2 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預后相關信息,包括院內病死率、ICU住院時間、總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以及發生急性腎損傷、低氧血癥、肺部感染、心肌損傷情況;同時收集所有患者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BMI、肝臟手術史、合并癥(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慢性腎功能不全)、肝臟基礎疾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脾大、腹水、脂肪肝)、術前實驗室檢查(Alb、WBC、Hb、PLT、PT、APTT和纖維蛋白原水平)、手術情況(手術時間、開腹手術、腹腔鏡手術、肝門阻斷時間、多部位手術)、麻醉情況[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以及全憑靜脈麻醉、誘導后低血壓、術中最低體溫、失血量等情況]。
急性腎損傷定義為術后48 h內患者肌酐上升≥26.5 μmol/L或7 d內肌酐上升至基礎值的1.5倍以上或尿量<0.5 mL·kg-1·h-1持續超過6 h者[5]。低氧血癥定義為術后血氣檢查氧分壓/吸入氧濃度<300 mmHg者[6];麻醉誘導后低血壓定義為麻醉誘導后平均動脈壓下降超過30%。肺部感染定義為術后胸部X線或CT檢查可見肺部滲出并伴有咳嗽咳痰及發熱和WBC水平升高者[7]。心肌損傷定義為術后48 h內出現肌鈣蛋白i或肌酸激酶同工酶-MB異常者。肝硬化定義為既往合并病毒性肝炎或大量飲酒等相關病史,實驗室檢查示血清Alb水平下降、膽紅素升高、PT延長或B超、CT檢查可見明確影像學表現或內鏡發現食管胃底靜脈曲張或肝活組織檢查有肝小葉形成者[8]。患者手術操作類型包括開腹手術、腹腔鏡手術,經歷開腹、腹腔鏡中任何1項或多項。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因原發性肝癌或轉移性肝癌行手術治療后轉入ICU患者422例,其中男282例,女140例,年齡21~91歲,其中低血壓組107例,非低血壓組315例。
2.2 預后指標 整體院內病死率為1.9%(低血壓組3.7%,非低血壓組1.3%)。相較于非低血壓組,低血壓組患者ICU住院時間更長,機械通氣時間更長,術后發生急性腎損傷、低氧血癥者、肺部感染更多(P值均<0.001)(表1)。

表1 兩組患者預后指標比較
2.3 臨床資料 相較于非低血壓組,低血壓組患者合并冠心病和腹水者更多,術前Alb、PLT和纖維蛋白原水平更低,手術和肝門阻斷時間更長,開腹手術者更多,失血量更大(P值均<0.1)(表2)。

表2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2.4 多因素分析 將上述有統計學意義的臨床指標納入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時間、失血量是肝癌術后患者圍手術期發生低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更高的術前Alb水平是其保護性因素(P值均<0.05)(表3)。

表3 肝癌術后患者圍手術期發生低血壓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在我國,肝惡性腫瘤發生率呈增長趨勢,肝癌外科手術數量也隨之增加。肝癌重癥患者更多合并凝血功能障礙、代謝紊亂、低蛋白血癥及腹水等合并癥,術中及術后更易出現出血和低血壓等情況[9],術后多轉入ICU進行支持治療。因此,探析肝癌術后重癥患者圍手術期出現低血壓的相關危險因素并分析其對預后的影響,將為臨床治療提供有益證據。
本研究中,肝癌術后轉入ICU重癥患者圍手術期低血壓發生率高達25.4%,總體病死率為1.9%,其中低血壓組病死率達3.7%;低血壓組患者機械通氣時間和ICU住院天數均較非低血壓組顯著延長,AKI、低氧血癥和肺部感染人數明顯多于非低血壓組。上述結果與既往研究[10]相符,即使很短時間的低血壓也會導致組織灌注不足,增加術后發病率和病死率。外科手術過程中出現低血壓的情況較為常見,而動脈血壓降低可能導致心臟、腎臟等重要臟器出現缺血而導致臟器功能損傷[11],還會加重全身炎癥反應[12]。氣管插管時間延長和全身炎癥反應的發生也將增加患者肺部感染及低氧血癥等并發癥的風險[13],導致患者住院時間延長和病死率增加。
本研究顯示,行肝癌手術的重癥患者圍手術期低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為手術時間和失血量,而更高的Alb水平是其保護性因素。
手術時間往往與手術復雜程度和創傷呈正比,本研究患者多為開腹手術,手術時間的延長將導致液體蒸發增加,而這類液體丟失為隱性丟失,更易導致容量不足。手術時間延長同時意味著全身麻醉時間延長,更多麻醉藥物的應用使血管張力下降、心臟功能抑制,進而導致低血壓[14]。由于麻醉誘導等因素可導致血壓迅速降低,術中輸液多在手術初期速度較快,而后期速度減慢,且常以晶體液為主,而晶體液在血管內半衰期較短,隨著手術時間的延長,大量血管內液體滲出至組織間隙,血管內容量下降更易出現低血壓。手術時間延長,患者氣管插管時間延長,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患者術后感染性休克的風險也會增加。
出血量增加可導致失血性休克的風險增加。有研究[15]顯示,手術時間延長與失血量呈正相關,一方面與手術延長導致組織和血管損傷帶來的直接失血有關,另一方面與手術后炎癥反應導致血管滲漏造成的隱性失血關系。也有研究[16]顯示,手術時間延長與手術經驗有一定相關性,經驗的相對不足亦可導致手術損傷和失血增加。既往研究[17-18]顯示,大出血患者術后低血壓等合并癥發生率增加,住院時間延長,病死率增加,與本研究結果相近。
術前更高的Alb水平是肝癌患者圍手術期發生低血壓的保護性因素。血清Alb水平可以反映患者的一般營養狀況和肝儲備功能[19]。較高的白蛋白水平提示患者肝臟基礎疾病相對較輕,肝功能、出凝血功能較好,手術中出血風險較低;腫瘤侵犯范圍可能也相對較小,利于手術的實施,縮短手術時間。此外,Alb本身具有多重生物功能,更高的Alb水平有利于提高血漿膠體滲透壓,減少血管內液體外滲,保障血管內容量水平[20],同時還可提高機體免疫力,降低感染發生風險,從而降低感染性休克的發生率。
在單因素分析結果中,低血壓組相較于非低血壓組患者合并冠心病和腹水者更多、術前血小板和纖維蛋白原水平更低、肝門阻斷時間更長、開腹手術者更多,上述特征亦應引起重視。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時代,越來越多的外科患者合并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手術應激刺激下可能誘發心肌梗死及心功能不全。針對此類患者,應加強術前超聲或心肌酶篩查,以發現潛在心肌缺血患者,提前干預。同時,術前充分補充液體,防止麻醉誘導后低血壓,減少心血管事件[21]。臨床上肝癌患者合并腹水者多見,應積極行腹部超聲排查腹水,對合并腹水患者積極補充人血白蛋白,補足有效循環血容量,有利于患者圍手術期循環狀態穩定。肝硬化患者往往合并肝功能減退、脾功能亢進,PLT、纖維蛋白原水平下降多見,出血風險高。針對此類患者,術前需積極輸血、補充凝血底物調整患者凝血狀態,備足手術用血以應對術中出血增加風險。肝門阻斷時回心血量減少,血壓降低,且肝臟代謝麻醉藥物能力下降,麻醉藥物對循環的抑制進一步凸顯。同時,肝門阻斷時間延長導致患者代謝性酸中毒的可能性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低血壓發生風險。因此,肝門阻斷時間應盡量縮短,阻斷肝門時需提醒麻醉醫師減少麻醉藥用量、加快輸液速度以及準備好碳酸氫鈉等糾酸液體以應對低血壓風險。開腹手術患者液體蒸發量增加,為維持循環穩定,圍手術期應注意補充隱性丟失的液體量。
綜上所述,肝癌術后重癥患者圍手術期低血壓發生率高,低血壓患者ICU住院、機械通氣時間延長,AKI、低氧血癥、肺部感染發生率增加。手術時間延長和失血量增加是肝癌術后患者圍手術期發生低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術前較高的Alb水平是其保護性因素。因此,行肝癌手術前,應充分設計個性化手術方案,縮短手術時間,調整肝功能,維持術前較高的Alb水平,或可減少患者低血壓的發生,從而改善預后。本研究系回顧性研究,且樣本量有限,研究結論尚需大樣本前瞻性研究加以驗證。
倫理學聲明:本研究方案于2021年2月7日經由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號:2021FHB024-001。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王斌、安友仲、馮藝負責研究設計;王斌、梁漢生負責收集分析研究數據;王斌負責起草、修改文章關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