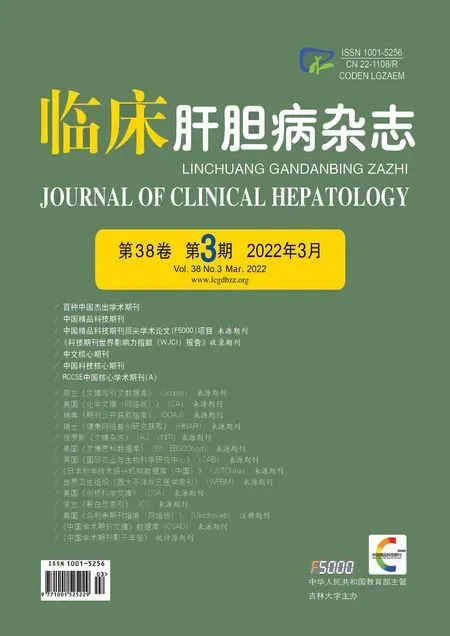缺氧誘導因子對肝細胞癌的作用機制及臨床意義
李宏一,羅業浩,羅筱凡,吳 笛,秦黃冠,藍紹航,呂 挺,龐宇舟
1 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壯醫應用基礎研究重點實驗室,南寧 530200; 2 湖北民族大學 醫學部,湖北 恩施 445000
根世界衛生組織[1]估計,2030年將有100多萬患者死于原發性肝癌。原發性肝癌包括肝細胞癌(HCC)、肝內膽管癌和混合型肝細胞癌-膽管癌,其中HCC占比約85%[2]。HCC的發生是一個逐步的過程。慢性肝炎病毒感染、過量飲酒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可導致肝臟炎癥和組織損傷,是HCC的主要病因。肝損傷可擾亂肝血管系統、正常血流和O2供應,形成一個缺氧的微環境。缺氧的Kupffer細胞、巨噬細胞和肝細胞可激活肝臟中的肝星狀細胞,加快膠原蛋白沉積,導致纖維化和肝硬化,從而進一步加劇缺氧。缺氧也可影響不同免疫細胞(如NK細胞)的活動,并抑制HCC微環境中許多不同類型免疫細胞的浸潤和積累,包括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髓源性抑制細胞(MDSC)和中性粒細胞。O2水平隨著HCC的發展而降低,從而促進免疫抑制微環境的形成[3]。缺氧誘導因子(HIF)是參與細胞對缺氧適應的核心參與者,并受氧感應脯氨酰羥化酶的調節。缺氧通過氧化還原效應和HIF的穩定作用影響細胞生長的諸多方面。HIF亞型可能通過改變代謝、生長和自我更新對腫瘤生長產生不同的影響,并可能高度依賴于環境。HIF通過促進血管生成影響癌細胞的遷移、侵襲和轉移、增殖,促進糖酵解,治療抵抗,免疫逃避等方式影響HCC的發病和進展[4]。探究HIF對HCC的作用機制及臨床意義,有望拓展診治HCC的新方法。
1 HIF的特性
HIF是異二聚體,由α-亞基(HIF-α,包括HIF-1α,HIF-2α/EPAS1和HIF-3α)和β-亞基(HIF-β,包括HIF-1β/ARNT1、ARNT2和ARNT3)組成。在人類和其他脊椎動物中,存在3種不同的HIF基因。在有氧(常氧)的情況下,HIF-α相互作用并與vonHippel-Lindau(VHL)蛋白結合,從而激活泛素連接酶系統,導致HIFa的蛋白酶體降解,HIF-1α蛋白的表達被抑制到非常低的水平。而在缺氧期間,脯氨酰羥化酶不活躍,導致HIF-α穩定并與HIF-1β二聚。二聚化后,HIF易位至細胞核,與包含序列5[0]-[A/G]CGTG-3[0]的啟動子區域內的E-box樣缺氧反應元件結合。HIF激活控制細胞氧穩態的基因,包括紅細胞生成/血管生成和線粒體代謝有關的基因。缺氧細胞通過主要由HIF調控的轉錄和轉錄后機制對抗壓力。這些分子變化使細胞能夠適應缺氧,主要通過轉用糖酵解來降低耗氧量,并減少細胞分裂(如細胞分裂)所需的能量。大多數實體瘤都有一定程度的缺氧,這與臨床療效有關。HIF活性的誘導上調了涉及癌癥許多特征的基因,包括代謝重編程,細胞增殖、侵襲和轉移以及對治療的抵抗[5-6]。
除了氧依賴性機制外,HIF的表達和活性還受氧非依賴性機制的控制,這些機制調節了基因轉錄、mRNA翻譯、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和HIF-1α亞基的翻譯后修飾。在炎癥反應中,HIF-1α基因的轉錄上調是以NF-κB依賴性方式實現的,并涉及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STAT3)和Sp1。此外,生長因子對PI3K/AKT通路的激活可導致HIF-1α mRNA和蛋白質合成增加。HIF-1α也通過與其他蛋白質的結合而受到調節[7]。
2 HIF在HCC中的作用機制
2.1 HIF通過促進糖酵解使HCC適應低氧應激 常氧環境中的細胞將葡萄糖轉化為丙酮酸,丙酮酸進入三羧酸循環并在線粒體中氧化磷酸化,最終產生三磷酸腺苷。腫瘤細胞則表現出葡萄糖消耗增加和向糖酵解的重要代謝轉變,丙酮酸轉化為乳酸。即使在有氧條件下,腫瘤細胞中的這種代謝轉變依然存在,被稱為Warburg效應[8]。通過AKT和HIF-1α介導的MAP17表達上調,將促進Warburg效應[9]。腫瘤細胞通過在無氧糖酵解中來產生能量,相關研究發現這一過程主要由HIF-1α調節。許多參與糖酵解的關鍵酶是HCC細胞中直接的HIF-1α靶標,包括PGK1、PGAM1、HK2、ENO1、ALDOA、GPI、GAPDH、LDHA、PFKFB4和PKM2等[10],同時HIF-1α可誘導多種糖酵解蛋白同種型(包括GLUT1和GLUT3)的過度表達和活性增加,這對于糖酵解通量控制十分重要[11]。此外,HIF-1α增加了線粒體相關酶的表達,如丙酮酸脫氫酶激酶1,其可抑制丙酮酸轉化為乙酰輔酶A,從而減少線粒體的氧化磷酸化水平和耗氧量[12]。而HIF-2α影響脂質代謝來進行能量代謝,如缺氧下,PI3K/AKT/mTOR通路可能是HIF-2α調控HCC的脂質代謝途徑,進而促進HCC適應無氧環境的重要機制[13]。總的來說,研究顯示HIF從不同途徑促進了HCC的糖酵解,以適應低氧應激。
2.2 HIF通過促進血管生成促進HCC生長 HIF-1α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表達的主要調節因子。在缺氧條件下,高水平積累的HIF-1α上調VEGF等一系列血管生成因子的表達,增強相關mRNA的轉錄,最后促進腫瘤血管生成[14]。HIF-2α也是調節肝細胞中VEGF和其他血管生成因子的主要HIF[15]。HIF-2α主要作用于血管生成相關基因,包括VEGF、促紅細胞生成素、VEGF受體2(VEGFR2)、血管生成素和酪氨酸蛋白激酶受體TIE-2[16]。
除VEGF外,許多其他信號分子在缺氧條件下也通過HIF依賴性機制高表達,包括胎盤生長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β和基質衍生因子1[17-19],均可促進腫瘤中的血管生成。ANG樣蛋白4也被鑒定為HIF-1α的基因靶標,其可通過調節血管細胞黏附分子和整合素β1的表達來影響HCC血管生成和轉移[20]。因此,HIF促瘤血管的生成可促進HCC的生長。
2.3 HIF通過介導侵襲轉移促進HCC進展 HIF誘導的腫瘤擴散的機制包括上皮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TWIST等基因的激活和GLUT1等參與癌癥代謝的轉錄因子的激活。EMT涉及多種類型的腫瘤和多種腫瘤轉移機制[21]。在HCC細胞中,缺氧條件下可通過SNAI1、SIP1、TGFβ、ROS、Notch、NF-κB、Wnt/β-catenin、PI3K/AKT等途徑的活化來誘導EMT,上皮細胞轉變為可移動的基質細胞,獲得遷移到遠處部位的能力[22]。細胞外基質(ECM)重塑在腫瘤侵襲和轉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參與ECM的幾種酶沉積和重塑受缺氧和HIF的調節,包括基質金屬蛋白酶、2-酮戊二酸5-雙加氧酶、賴氨酰氧化酶、膠原蛋白脯氨酰4-羥化酶等,同時通過HIF-1α依賴性機制,可下調HCC細胞中金屬蛋白酶2組織抑制劑的表達[23]。HIF-1α/LOX通路通過依賴于肝炎反式激活蛋白X的機制,參與ECM重塑和促進HCC轉移[24]。
此外,微小RNA(microRNA,miRNA)也與腫瘤的遷移和轉移密切相關。例如,miR-23是一種常見的致癌基因,研究[25]顯示,miR-23a/b可以通過VHL-HIF-1α通路促進HCC的發病進展。通過抑制SMC4可顯著抑制HCC細胞的遷移,而HIF-1可通過轉錄調節和抑制miR-219來增加SMC4的表達。因此,HIF-1/miR-219/SMC4調控通路可能是促進HCC的遷移和轉移一種機制[26]。此外,HIF-1α/miR-671-5p/TUFT1/AKT也可能是一種機制[27]。lncRNA也可促進HCC轉移,lncRNA鋅指蛋白多型2反義RNA1通過調控miR-576-3p/HIF-1α軸促進HCC的增殖和遷移[28]。此外,lncRNA可抑制HCC的轉移,如lincRNA-p21可下調HIF-1α來降低VEGF水平,從而抑制HCC的侵襲能力[29]。因此,需要更多研究從非編碼RNA層面來闡明HIF的作用機制,挖掘非編碼RNA靶向藥物。
2.4 HIF通過介導免疫逃避、癌癥干細胞促進HCC發生發展
缺氧與HIF和腫瘤細胞逃避免疫反應有關。免疫細胞的功能受HIF1依賴性信號機制的調節,在缺氧期間,HIF誘導腫瘤細胞對CD8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和NK細胞產生抗性,其可能是HIF通過AMPK/CREB信號增加IL-10表達,分泌的IL-10通過STAT3信號通路抑制NK細胞的細胞毒性,從而促進HCC的復發和轉移[30]。此外,缺氧可以上調產生腺苷的細胞外酶CD39和CD73的表達,增加其在細胞環境中的濃度。腺苷通過與其A2A受體結合,強烈抑制活化的T淋巴細胞和NK細胞的抗腫瘤功能[31]。HIF還可以通過作用于TAM來抑制對腫瘤的免疫反應。研究[32]認為,TAM通過分泌細胞因子,如IL-10、TGFβ、IL-6、VEGF和IL-8,促進腫瘤細胞的生長、侵襲和轉移。
MDSC具有免疫抑制活性,可使癌癥逃避免疫監視并對免疫無反應。通過MDSC介導L-精氨酸的消耗,阻礙T淋巴細胞增殖,并與T淋巴細胞受體亞基CD3的下調相關,導致T淋巴細胞受體反應降低。肝腫瘤的MDSC水平升高,MyD88-NF-κB通路的激活刺激IL-10的分泌,從而抑制樹突狀細胞中IL-12的表達。MDSC也通過細胞表面的TGFβ和NK受體p30誘導NK細胞失活。此外,MDSC還通過誘導CD4+CD25+叉頭轉錄因子3+調節性T淋巴細胞的產生來抑制免疫反應從而促進了HCC的發生發展[33]。
癌癥干細胞(CSC)在腫瘤的發生、發展、復發和轉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HIF因子可利用各種機制影響CSC的誘導和發育。這些機制可能是通過誘導CSC標記,CD44、ALDH,腺苷/STAT3/IL-6途徑,MAPK/ERK途徑,NOTCH和Wnt信號傳導或其他機制促進CSC的繁殖[34]。缺氧可顯著增強HCC細胞的干細胞相關特性,這種作用可以通過敲低HIF-1α或HIF-2α來消除。此外,HIF-1α特異性干擾RNA處理,在RNA和蛋白質水平顯著降低CSC中CD133的表達。重要的是,EMT激活可以誘CSC特征。Notch1通過與HIF-1α的直接相互作用介導EMT誘導的CSC的過程;HIF-1α上調Notch的細胞內表達可激活EMT并誘導HCC細胞在體外獲得CSC的特征。
迄今為止,大多數研究報道了HIF-1α和HIF-2α對腫瘤生長的積極作用。然而,另有研究[35]顯示,HIF在一些其他癌癥中表現出相反的影響,如缺氧可降低野生型(HIF-1α+/+)胚胎干細胞的增殖并增加細胞凋亡。因此,尚需更多研究探析HIF對HCC生長遷移的具體作用。
總結HIF在HCC中的作用機制見圖1。

圖1 HIF作用于HCC的作用機制示意圖
3 HIF在HCC中的臨床意義
3.1 HIF在HCC中的治療應用 HIF抑制劑有望成為一種有效的HCC治療方法,抑制HIF-1α活化可能有助于阻止癌癥進展,從而使生長的腫瘤細胞缺乏O2和所需的營養供應。當前已發現不同的化合物或藥物可通過不同的分子機制阻斷HIF的活性,包括減少HIF-1α的蛋白合成,代表藥物如mTOR抑制劑、強心苷、拓撲異構酶抑制劑和合成寡核苷酸等;降低HIF-1α mRNA的水平,如前藥AFP-464的氨基黃酮成分藥物;增加HIF-1α的分解,如HSP90抑制劑、抗氧化劑和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藥物;減少HIF亞基的異二聚化,如吖啶黃藥物;減少DNA與HIF的結合,并降低轉錄活性,如蒽環類和棘霉素等[36]。研究[37-38]顯示,一些中藥方劑或中草藥提取物也具有抑制或降低HIF-1α的作用,如益氣化瘀解毒方、水飛薊的提取物——水飛薊素等。
HIF也可能參與了HCC化療藥物耐藥性的發展。索拉非尼是一種具有抗增殖、抗血管生成和促凋亡特性的多激酶抑制劑,但由于產生耐藥細胞,其療效不佳,可能是長期索拉非尼治療后導致補償性生長途徑的激活,或者缺氧誘導的自噬,從而使HIF介導的細胞反應觸發對缺氧微環境的適應性機制。因此,HIF抑制劑可以與現有療法聯合使用,以增強常規療法的敏感性和效果[39]。例如,辛伐他汀可通過抑制HIF-1α/PPAR-γ/PKM2軸,使HCC細胞重新對索拉非尼敏感[40]。此外,有研究[41]顯示,HIF-1α可通過促進HCC干細胞特性,促進其對表阿霉素化療藥物的耐藥。
然而,開展相關臨床研究時必須謹慎。例如,由于HIF抑制劑可能加劇胰島素抵抗損傷,并抑制肝再生。因此,對于因行肝臟手術的HCC患者,應停止HIF抑制劑治療[42]。
3.2 HIF在HCC預后評估中的應用 HIF可通過多種途徑影響HCC的發生發展,也因此被納入HCC預后評估的相關研究中。有研究[43]顯示,HIF-1α相關基因的過度表達與轉移和病死率有關,HIF-1α陽性表達與HCC合并肝硬化患者血管浸潤、TNM分期、HBV感染、腫瘤大小、門靜脈腫瘤血栓顯著相關。如上所述,HIF通過不同方式影響了HCC的發病和進展。因此,HIF相關指標水平的測定有望為HCC預后評估提供價值。
KIAA1199是一種與癌癥轉移相關的蛋白質,其與HIF-1α在許多人類癌癥中上調,機制上與血管浸潤、腫瘤TNM分期、HBV感染、腫瘤大小和肝硬化顯著相關,提示KIAA1199聯合HIF-1α檢測對評估HCC患者的存活時間、預后情況有潛在價值[44]。其他如YTHDF1、DAAM2、H3K9me2、H3K9me3、Rpn10等作為HCC預后標志物也被相關研究[45-48]初步證實了臨床價值,這些標志物聯合HIF-1α檢測或許能夠作為評估HCC預后的新方法。
4 討論與展望
總結現有研究,HIF在HCC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促進糖酵解、血管生成、侵襲轉移、免疫逃避、癌癥干細胞等方式,影響HCC的發生發展以及對治療耐藥,也由此引出了通過HIF靶向治療HCC和評估HCC預后的新設想。然而,HIF在HCC中的相關研究仍有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1)既往研究主要著眼于HIF-1,HIF-2次之,而HIF-3的相關研究甚少。已有證據[49]顯示,HIF3 AmRNA被差異剪接以產生多種HIF-3α變體,這些變體促進或抑制其他HIF復合物的活性,不同的HIF-3變體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功能。(2)已有研究提供了關于HIF-2α在HCC生長和進展中的穩定性、轉錄活性和作用的信息,但在HCC中的確切作用尚存爭議。有研究[50]認為HIF-2α在腫瘤中可能具有某些積極作用。(3)HIF檢測評估預后也存在爭議,且尚不完全清楚HIF-1、HIF-2、HIF-3三者在HCC中存在哪些相互作用。相關研究[51]發現,單獨敲除HIF-1α或HIF-2α未能顯著減小腫瘤體積(HIF-1α敲除后HIF-2α的表達增加,HIF-2α敲除后HIF-1α的表達增加),而同時敲除HIF-1α和HIF-2α之后效果可見腫瘤體積顯著縮小。因此,HIF-1、HIF-2、HIF-3之間是否存在一些相互調控作用及其具體機制?如果存在相互調控作用,靶向HIF-1α治療和HIF-1α評估預后的同時,是否要考慮HIF-2和HIF-3的影響?這些問題有待更多研究探明,以提升相關藥物研發的成功率及HIF應用于臨床的可靠性。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李宏一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及撰寫論文;羅筱凡、吳笛、秦黃冠負責文獻檢索及資料整理;藍紹航、呂挺參與收集數據及修改論文;龐宇舟、羅業浩負責選題、擬定寫作思路,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