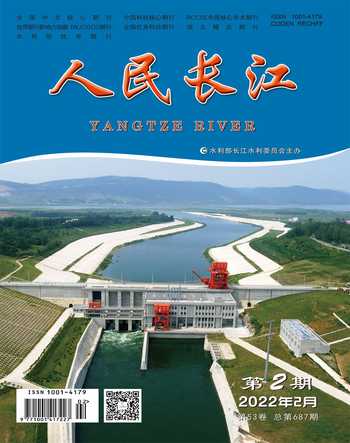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運用方式研究
李肖男 傅巧萍 張松 何小聰 周曼 丁毅






摘要: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是提升水庫綜合效益的有效途徑,但汛期運行水位運用方式應科學協調防洪與興利的關系。在概括性分析三峽水庫水沙特性的基礎上,結合汛期防洪與汛末蓄水的要求,重點剖析了通過汛期預報預泄和汛末預報預蓄開展三峽水庫運行水位上浮運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選擇典型洪水研究了不同方式下三峽水庫運行水位可上浮運用的空間,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風險并提出了應對措施。結果表明:三峽水庫8月下旬前運行水位通過預報預泄的方式浮動至148.00 m,之后至9月上旬采用預報預蓄的方式逐步抬升至155.00 m的風險是可控的。研究成果已指導了三峽水庫不同階段調度運行文件的編制和調度運行實踐,提升了三峽水庫的綜合利用效益。
關鍵詞:水庫調度; 汛期運行水位; 預報預泄; 預報預蓄; 三峽水庫
中圖法分類號: TV697.1
文獻標志碼: A
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22.02.004
0引 言
三峽工程是治理開發和保護長江的關鍵性控制工程,具有
防洪、供水、生態、發電、航運等巨大綜合效益,直接關系到流域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態安全和綠色發展。工程初步設計階段[1],根據長江中下游防洪的需要和水庫“蓄清排渾”的要求,設計三峽水庫每年6月10日至9月30日維持汛期防洪限制水位(以下簡稱“汛限水位”)145.00 m運行,以保留防洪庫容,調節可能發生的洪水,同時使庫區維持較大的水面比降,以利排沙。
汛期運行水位是協調水庫運行管理過程中防洪與興利之間矛盾的關鍵指標。隨著工程由設計轉向運行階段,汛期三峽水庫若長時間按汛限水位145.00 m控制運用,電站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出力受阻,水庫調度的靈活性亦受到制約。為盡量減輕機組出力受阻程度,提高電站的調峰能力和發電效益,更好保障電網安全穩定和機組高效運行,采取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是提高三峽水庫洪水資源利用效益、提升水庫調度靈活性的關鍵措施。
同時,隨著長江上游梯級水庫群聯合調度格局的逐漸形成,三峽水庫作為長江干流有調節能力的最末一級水庫,上游水庫群調蓄對中下游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三峽水庫,流域水庫群汛末蓄水競爭性矛盾已突顯。從長江中下游洪水特性和洪水遭遇規律來看,8月1日后洞庭湖地區開始呈現退水趨勢,9月中旬后宜昌站來水亦開始減退,且8月中下旬以后,宜昌站來水與洞庭湖地區來水遭遇幾率很小,三峽水庫理論上可以逐步釋放防洪庫容,承接興利蓄水。通過提前蓄水和汛末運行水位上浮的方式預存部分水量,以提高水庫的蓄滿程度,減少集中蓄水對長江中下游兩湖地區的影響,增強枯水期長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流量補給能力,充分發揮水庫的供水效益。
國務院2015年批復的《長江防御洪水方案》[2]作為長江流域洪水防御的工作綱領,明確了長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庫可采取汛期適度蓄水、汛末提前蓄水、流域調水補水等措施,合理利用洪水資源。《長江防御洪水方案》反映了長江流域防洪的指導思想,突出了統籌防洪減災和興利的洪水資源化理念。面對三峽水庫水資源利用與管理的多樣化、多層次需求,在保證樞紐工程和長江中下游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從洪水資源利用的理念出發,開展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對提高水電站發電效益、增加蓄水期水量有效供給等效果顯著,對指導水庫實時調度、提升工程綜合效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研究思路
水庫工程設計階段的汛限水位確定一般不考慮氣象水文預報條件,多采用基于統計規律的設計洪水成果、按照規劃設計要求確定汛限水位固定值或分期汛限水位。隨著氣象水文預報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現代監測體系的不斷完善,洪水預測預報水平不斷提高,為汛期水庫實時調度中的運行水位動態控制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
在氣象水文預報水平提升并逐步應用于調度實踐的基礎上,多種基于預報的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方法被提出并成功應用[3-6],如防洪預報調度方式及規則設計方法、預泄能力約束法、改進預泄能力約束法、考慮年內洪水時序變化規律的統計分析法、庫容補償法、分級預泄法等。這些方法的核心思想為充分利用氣象水文預報信息,根據氣象水文的預報預見期、預泄能力約束,采取預報預泄或預報預蓄的方式,確定水位可動態控制的運行區間。
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的研究與應用建立在充分識別長江流域洪水特性的基礎上,根據氣象水文預報水平的發展和長江中下游控制站點的過流能力約束,通過預報預泄或預報預蓄的思路開展研究、優化與實踐,是多種研究方法的集成創新應用。
由于水庫汛期運行水位上浮會占用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特別是對城陵磯地區的防洪空間。如何在不影響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和不增加長江中下游防洪壓力的前提下上浮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科學協調三峽水庫汛期水位上浮與對長江中下游防洪的空間及風險關系,是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的關鍵[7]。
為保證不影響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主汛期水位上浮運行的前提條件是該上浮水位能通過預報預泄方式及時降下來[7],即當預報將發生洪水、三峽水庫需要對長江中下游實施攔洪前,通過預泄將庫水位及時降至汛限水位,以保證三峽水庫有足夠的防洪庫容為長江中下游攔蓄洪水和保證樞紐度汛安全。同時,鑒于警戒水位是中國防汛規定的各江河堤防需處于防守戒備狀態的水位,為盡量不增加長江中下游防洪壓力,三峽水庫汛期水位向上浮動運行及水庫預泄至汛限水位期間,應控制下游主要防洪控制點沙市站、城陵磯蓮花塘站(以下簡稱“城陵磯站”)水位距警戒水位有充足余地,以使水庫預泄后,上述控制站水位仍可保持在安全狀態。考慮到長江中下游防洪原在警戒水位以下設有設防水位,距警戒水位有一定空間,為安全起見,三峽水庫的預報預泄按設防水位作為控制條件,即水庫預泄后,控制站水位不超設防水位(沙市站42.00 m、城陵磯站31.00 m)。
汛末三峽水庫開展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的主要思路為在充分研判流域洪水特性的基礎上,基于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形勢,逐步釋放三峽水庫兼顧城陵磯地區的防洪庫容,通過預報預蓄的方式實現運行水位的上浮運用。同時,汛末三峽水庫上浮運用的幅度應確保荊江地區百年一遇防洪標準不受影響,且庫區淹沒風險可控。
2研究要點
2.1洪水泥沙特性分析
洪水特性分析是開展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的重要基礎。宜昌水文站是三峽水庫壩址設計洪水的代表站,長系列實測資料統計與分析表明[8]:宜昌站年最大洪峰主要發生在7月至8月中旬,占總數的70%以上;8月20日左右是出現年最大洪峰流量相對發生概率較小的弱空檔期,之后出現頻率小幅抬升,至9月中旬后宜昌站來水開始減退。長江中游的荊江河段和城陵磯地區是三峽水庫防洪調度的重要保護區,壩址至城陵磯河段主要區間來水為洞庭湖區來水,宜昌站與洞庭湖洪水遭遇主要發生在6月下旬至8月中旬,8月下旬以后因區間來水快速消退,洞庭湖區基本無洪水發生,與長江干流洪水遭遇幾率很小,且量級不大。因此,從洪水時空分布特性來看,汛期三峽水庫可視來水量級、下游水位站點情況開展運行水位上浮,汛末可結合上下游防洪形勢進一步提升浮動上限。
泥沙問題是影響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受上游水庫攔沙、水土保持、降雨減少和河道采砂等因素的綜合影響[9],建庫以來三峽水庫入庫泥沙大幅減少,2003~2019年年均入庫沙量較論證階段減少約70%。由于入庫泥沙的大幅減少,加之水庫開展庫尾減淤調度和沙峰排沙調度實踐,三峽水庫的泥沙淤積水平同樣低于論證階段。實測數據表明[10]:2003年6月至2019年12月,水庫淤積泥沙18.325億t,年平均淤積泥沙近1.1億t/a,僅為論證階段(1961~1970年的預測成果)的1/3左右。入庫泥沙的大幅減少使得泥沙淤積不致成為汛期運行水位上浮運用的制約性問題。
2.2汛期運行水位上浮方案研究
汛期三峽水庫運行水位動態控制主要基于預報預泄的思路,即當長江中下游主要控制站水位較低、不需要三峽水庫防洪蓄水時,庫水位在一定的變幅范圍內向上浮動運行;當預報將來洪水,或長江中下游河段防洪壓力逐步顯現時,及時開展水庫預泄,且預泄后盡量保障下游沙市站和城陵磯站不超設防水位。考慮不同的預報預見期,三峽水庫在1~3 d內庫水位由上浮的最高水位降至145.00 m,增加下泄流量如表1所列。
進一步分析表明,預泄對沙市、城陵磯站水位影響較為顯著,對漢口、湖口站影響較小。不同典型年對沙市站水位抬升幅度為0.28~2.39 m,對城陵磯站水位抬升0.17~0.71 m,對漢口站水位影響幅度為0.10~0.56 m,對湖口站水位影響0.05~0.27 m。按最不利的預報時間1 d計算,146.50 m預泄后,增加的下游水位可控制在1.00 m以內(見表2)。
以控制泄水時期下游控制站水位影響為條件,按3 d預見期考慮,若沙市站與城陵磯站在設防水位下分別按1.00,0.50 m為控制條件(即開始預泄),146.50,147.00,148.00 m方案可基本消化預泄的影響;150.00 m方案則需分別在設防水位下留1.70,0.70 m(不考慮自然漲水的影響)。
對于三峽水庫汛期通過預報預泄方式開展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的風險主要集中于入庫洪水預報的誤差和下游洞庭湖水系來水的不確定性。對于前者,研究表明[11],按照浮動上限148.00 m控制,即使考慮一定的預報誤差,三峽水庫安全預泄至汛限水位的幾率仍有90%左右;對于后者,隨著氣象觀測技術、數值預報技術以及氣象信息傳輸技術的發展,可引入降雨預報控制條件,提升風險控制水平。研究表明,若預報洞庭湖水系未來3 d無中等強度以上降雨,則運用風險較小。綜合現階段的預報水平和風險控制措施,三峽水庫汛期8月20日以前通過預報預泄開展上浮運用的浮動上限可按148.00 m控制,運用期間應加強上下游水雨情監測和氣象水文預報,預報上游或者洞庭湖區將發生洪水時,及時、有效地采取預泄措施,將庫水位降低至汛限水位。
2.3汛末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研究
根據洪水特性分析可知,8月1日之后,洞庭湖水系已進入后汛期,8月下旬之后,宜昌站與洞庭湖水系發生遭遇的幾率進一步減小,此時段中下游河道水位逐步降低,城陵磯地區防洪需求逐步減弱,三峽水庫具備逐步釋放對城陵磯防洪補償庫容可行性。
三峽水庫汛末運行水位動態控制方式一方面可延續預報預泄的思路,考慮到汛末洪水進一步衰減,水位浮動上限可較主汛期進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若8月1日之后,洞庭四水合成流量在15 000 m3/s以下、城陵磯站水位在29.50 m以下,基本可判定不會形成流域性大洪水或上中游區域性大洪水[12],此時三峽水庫兼顧城陵磯地區的防洪庫容可進一步釋放,三峽水庫可考慮采取預報預蓄的方式開展汛末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總而言之,汛末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的關鍵為在保證荊江地區百年一遇防洪標準的同時,充分論證城陵磯地區的防洪需求,并兼顧庫區的防洪安全。
為此,選擇城陵磯地區汛期末段峰高量大、較為惡劣的1954,1958,1966,1988,1998,2002年等洪水為典型,三峽水庫自汛限水位起調,采用上述典型洪水8月20日、8月25日、9月1日、9月5日等不同節點的同期洪水過程進行攔蓄計算[13],推求了城陵磯地區汛末實測洪水對三峽水庫的庫容需求。結果表明:三峽水庫攔蓄洪量由8月中下旬的45億m3左右減少至9月上旬的5億m3,且9月上旬攔蓄洪量主要發生在防御1966年上游型典型洪水中。典型洪水調蓄分析結果表明,8月下旬以后根據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形勢,三峽水庫運行水位上浮運用的風險較小。在此基礎上,通過系統分析汛期末段水位上浮對流域防洪、庫區淹沒的風險[11],從對長江中下游防洪控制留有一定余度考慮,并兼顧水庫水位控制操作的靈活性,8月下旬三峽水庫運行水位可按不超過150.00 m(上浮庫容25.4億m3)控制。
對于三峽水庫9月上旬的運行水位,若已判定不會形成流域性大洪水或上中游區域性大洪水,水庫運行水位可考慮與興利蓄水銜接,控制三峽水庫9月上旬水位按150.00~155.00 m(上浮庫容56.5億m3)控制。風險分析表明[11],三峽水庫9月上旬運行水位上浮至155.00 m后若遭遇1954年典型或1982年典型的荊江100 a一遇設計洪水,需上游溪洛渡、向家壩水庫預留防洪庫容約20.6億m3配合運用,才能使三峽水庫最高調洪水位不超171.00 m,不致影響對荊江特大洪水的防御能力。
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預蓄調度方式與來水有很大的關系,實際調度時可根據當時水文氣象情勢和預報實時研究決策。
3不同階段成果
試驗性蓄水運用以來,根據前述研究思路,結合氣象水文預報水平的發展,有關各方持續開展三峽水庫的調度運行技術攻關研究,在此基礎上,先后編制形成了2009年國務院批準的《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14](以下簡稱“《優化調度方案》”)、2015年水利部批復的《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15](以下簡稱“《調度規程2015版》”)和2020年水利部批復的《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2019年修訂版)》[16](以下簡稱“《調度規程2019修訂版》”)等具有代表性的調度運行指導文件。
(1) 《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
由于三峽水庫上游最低通航水位為汛限水位145.00 m,考慮水庫實施調度需要,上游最低通航水位可在145.00 m的基礎上向下波動0.10 m。該條件一定程度限制了三峽水庫向下浮動的靈活性。因此,在《優化調度方案》批準之前的初期運行期,考慮泄水設施啟閉時效、水情預報誤差和電站日調節需要,當時的調度指導文件中規定實時調度中庫水位可在汛限水位145.00 m以下0.10 m至以上1.00 m范圍內變動。《優化調度方案》編制研究階段[7],為有效利用洪水資源,在保證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開始嘗試通過預報預泄的思路提升汛期運行水位。此階段,三峽水庫入庫洪水1,2,3 d預見期的預報合格率分別為85%,78%,70%左右(按許可誤差為預見期變幅的20%評定)。因此,根據表2的計算成果,按最不利的預報水平1 d考慮,選擇上浮最高水位146.50 m,即在滿足沙市站水位41.00 m以下、城陵磯站水位30.50 m以下且三峽水庫入庫流量小于25 000 m3/s時(按該階段三峽水電站26臺機組相應的滿發流量控制),庫水位可在146.00 m的基礎上進一步上浮至146.50 m。
(2) 《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
隨著預報水平的提高、運行經驗的積累和上游水庫群投入防洪庫容的增加,為有效應對蓄水期間的旱情,《調度規程2015版》編制研究時,在《優化調度方案》的基礎上新增了9月上旬汛期末段的運行水位動態控制方式,即在確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采取以汛期水位上浮運行的方式,在來水相對豐沛的9月上旬預存部分水量,以協調集中蓄水期水庫蓄水與下游用水的矛盾。對于三峽水庫9月上旬運行水位的上浮問題,主要是在預報長江上游不會發生較大洪水,且沙市站、城陵磯站水位較低時,浮動水位可按不超過150.00 m控制。研究過程中[17],考慮9月上旬宜昌站洪水量級仍然較大,仍需要防范可能的洪水風險,同時鑒于預報水平和對汛末洪水研判水平的提升,此階段水庫預泄時間按3 d考慮,根據表2的計算成果,當沙市站、城陵磯站水位分別低于40.30,30.40 m時,三峽水庫水位上浮至150.00 m可保證預泄后下游控制站點不超設防水位。此外,由于三峽水電站(包括地下電站)全部32臺機組投運,發電引用流量約為30 000 m3/s,《優化調度方案》中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從146.00 m上浮至146.50 m的條件之一“三峽水庫來水流量小于25 000 m3/s”調整為《調度規程2015版》的“三峽水庫來水流量小于30 000 m3/s”。
(3) 《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2019年修訂版)》。
為進一步適應上游水庫群建成投運、水雨情預報水平提升、長江中下游防洪及水資源綜合利用需求提高等調度運行環境的變化,《調度規程2019修訂版》相較于《調度規程2015版》對汛期運行水位進行了進一步優化,一方面汛期上浮運行的預見期按照1~3 d考慮,水位浮動上限由146.50 m進一步提升至148.00 m,同時結合預報水平的發展,從實時入庫流量和未來3 d預報流量兩個方面對入庫流量級別進行了細化。此外,汛末預蓄的起始時間較《調度規程2015版》的9月1日進一步提前至8月21日,9月上旬的運行水位也進一步提高至155.00 m,以更好地協調汛末水庫蓄水與下游用水的矛盾。對于上述優化,其有利條件在于三峽水庫入庫洪水的短期預報水平進一步提高,1~3 d相對誤差均小于9%,預報合格率在90%左右[13]。同時,長江上游溪洛渡、向家壩等水庫群已經投產運行,上游水庫群可通過聯合調度削減進入三峽水庫的入庫洪量,一定程度提升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的靈活性,特別是對汛期末段三峽水庫水位的上浮運用。此外,為了防范6月11日至8月20日期間汛期運行水位上浮至148.00 m運用的風險,基于氣象預報水平,提出了“預報洞庭湖水系未來3 d無中等強度以上降雨過程”的運用條件,以避免三峽水庫水位上浮占用兼顧城陵磯地區防洪的庫容,降低水庫預泄對城陵磯地區的影響。
圖1為三峽水庫不同階段的汛期運行水位浮動上限。縱觀三峽水庫不同階段汛期運行水位變化過程,在保證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優化調度方案》提出汛期運行水位可在144.90~146.50 m浮動。為有效應對蓄水期間的長江中下游用水需求,《調度規程2015版》提出在確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9月上旬可適當預存部分水量,且浮動水位不超過150.00 m。為進一步協調汛末蓄水和長江中下游用水的矛盾、提升汛期洪水資源水平,《調度規程2019修訂版》提出6月11日至8月20日期間,汛期運行水位可在144.90~148.00 m浮動;8月21日至9月10日可利用汛期后段水量相對較多的有利時機,預存部分水量,9月上旬上浮水位可按150.00~155.00 m控制。
通過對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的持續優化,充分提升了汛期洪水資源利用水平,有效緩解了汛末水庫蓄水和長江中下游用水的矛盾,提高了水庫汛后蓄滿的保證程度。計算表明:通過汛期運行水位優化,《調度規程2019修訂版》的汛期運行運用方式相較于《調度規程2015版》,可增加多年平均年發電量約15億kW·h,可提高汛末蓄滿率約1.6%,充分保證了三峽水利樞紐綜合效益的發揮。
4調度運行實踐
2009年以來的實時調度中,伴隨著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中小洪水減壓調度和防洪調度的運用,三峽水庫主汛期6月10日至8月31日的最高攔洪水位基本都在150.00 m以上,且多數在155.00 m以上,最高為2020年的167.65 m。
表3為2009~2020年三峽水庫歷年主汛期特征水位統計情況,從水位進程來看,8月20日的水位基本在150.00 m,最高為2020年的161.81 m,最低為2011年的145.81 m。汛期末段由于開展了汛末提前蓄水運行實踐,加之汛末時段的防洪減壓調度,8月31日的水位基本在148.00 m以上,最高為2020年的161.14 m。
為了區分中小洪水減壓調度和防洪調度對汛期運行水位運用的影響,選擇汛期入庫流量相對較小的2011年和2017年為代表。圖2和圖3分別展示了2011年和2017年三峽水庫6月10日至9月10日出入庫流量過程和水位運用過程。可以看出,三峽水庫主汛期通過預報預泄、汛末通過預報預蓄的形式開展了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庫水位基本在汛限水位以上運行,洪水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時,在有充分把握確保長江中下游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實時調度中汛期運行水位浮動上限仍有一定優化空間。
應該來說,試驗性蓄水以來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運用方式的研究與優化,是建立在充分辨識洪水時空變化規律的基礎之上。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包括預泄能力約束法、分級預泄法在內的多種方法,應用了預報預泄和預報預蓄等不同方式,合理挖掘了下游河道泄流能力、降雨洪水預報和水庫自身攔蓄能力的潛力,兼收并蓄,引領了該研究領域的發展,并成功應用于水庫的調度運行實踐,提升了工程的綜合效益。
5結語與展望
試驗性蓄水以來,面對日趨緊張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需求,伴隨水文預報水平的提高、上游梯級水庫群的建成和運行經驗的積累,按照“問題導向、科學研究、應用實踐、形成規程”的模式,三峽水庫汛期水位運用方式保持持續優化,汛期水位浮動空間逐步抬升,有效協調了防洪、發電、蓄水、供水、減淤等多目標需求。
展望未來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進一步優化的方向,隨著烏東德、白鶴灘水庫的投運,金沙江下游梯級水庫群配合三峽水庫防洪調度的空間和靈活性得以提升,可重點從以下兩方面開展:
(1) 無論是預報預泄還是預報預蓄,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運用有賴于氣象水文預報的支撐。當前,三峽水庫入庫及下游控制站3 d內的氣象水文預報成果可滿足實時調度需求,為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運用提供有力支撐。同時,4~7 d水文預報成果基本可用,可對流域水文氣象情勢的發展趨勢有較大的把握。目前《調度規程2019修訂版》中三峽水庫減輕中游防汛壓力的中小洪水調度方式已經考慮了未來5 d的氣象水文預報條件。建議進一步研究提升中長期預報水平的方法,考慮引入氣象預報產品,延伸預見期,為汛期運行水位浮動上限的提升提供基礎預報支撐和風險控制抓手。
(2) 由于三峽水庫汛期不同時段洪水時空分布規律不同,長江中下游的防洪需求亦有所變化。結合宜昌及洞庭湖區控制站點的洪水統計特性,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上浮運用的上限和運用方式可根據不同時段的洪水規律予以細化,比如按6月下旬以前、6月下旬至7月底、8月上中旬、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方式對時段進行細分。在此基礎上,結合水庫預泄對長江中下游控制站點的影響,相應主汛期6,7月份三峽水庫運行水位浮動上限可考慮在148.00 m的基礎上進一步抬升;進入8月份以后,根據流域的水雨情形勢,在有把握流域性大洪水或上中游區域性大洪水不會發生的前提下,三峽水庫兼顧城陵磯地區防洪庫容可進一步提前釋放,相應三峽水庫通過預報預蓄方式上浮運行水位的時間亦可提前。
參考文獻:
[1]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報告[R].武漢: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1992.
[2]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防御洪水方案[R].武漢: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2015.
[3]邱瑞田,王本德,周惠成.水庫汛期限制水位控制理論與觀念的更新探討[J].水科學進展,2004,15(1):68-72.
[4]任明磊,何曉燕,丁留謙,等.汛限水位動態控制域確定方法研究發展動態綜述[J].水力發電,2016,42(6):61-65.
[5]郭生練,鐘逸軒,吳旭樹,等.水庫洪水概率預報和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J].中國防汛抗旱,2019,29(6):1-4.
[6]王俊,郭生練.三峽水庫汛期控制水位及運用條件[J].水科學進展,2020,31(4):473-480.
[7]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三峽水庫汛期水位運行控制方式研究[R].武漢: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2009.
[8]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三峽水庫水文情勢研究[R].武漢: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2009.
[9]許全喜.長江上游河流輸沙規律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6.
[10]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泥沙公報2019[R].武漢: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2020.
[11]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三峽水庫汛期運行水位動態控制研究報告[R].武漢: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2020.
[12]陳桂亞.三峽水庫對城陵磯防洪補償庫容釋放條件分析[J].人民長江,2020,51(3):1-5,30.
[13]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上游水庫群聯合調度模式下溪洛渡、向家壩、三峽三庫洪水資源利用研究[R].武漢: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2018.
[14]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R].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2009.
[15]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R].北京: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2015.
[16]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三峽(正常運行期)-葛洲壩水利樞紐梯級調度規程(2019年修訂版)[R].北京: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2020.
[17]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三峽-葛洲壩梯級樞紐正常運行期調度規程相關專題分析報告[R].武漢: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有限責任公司,2015.
(編輯:劉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