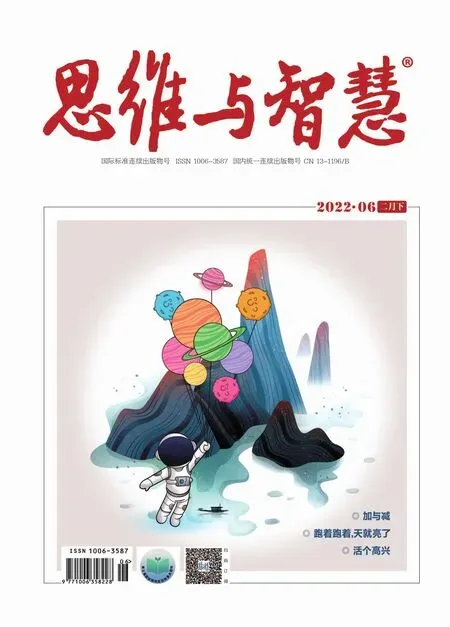劉靖:解鎖“唐朝黑科技”粉蠟箋技藝
◎ 汪小年
最現代VS最傳統
1997年的7月份,在安徽巢湖鄉下黃麓鎮的老房子里,25歲的劉靖在琢磨著一件大事——“復活”失傳百年的宮廷御用紙粉蠟箋。
啥是粉蠟箋?恐怕有很多人不了解。粉蠟箋誕生于唐代,因其制作原料中含有吸水的“粉”和防水的“蠟”兩種主要原材料而得名。粉蠟箋表面平滑細密,易于書寫,可保存幾百年不變質。古時皇帝書寫圣旨,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粉蠟箋。但隨著清王朝的覆滅,粉蠟箋的制作工藝也失傳了。
可劉靖為何要“復活”粉蠟箋呢?“原本我做的是最現代的廣告工作,后來卻做起了最傳統的紙箋加工。”劉靖笑說命運的吊詭。之所以這樣選擇,“首先是為了完成我父親的心愿吧,再加上后來結識了我的愛人,她是我家廠里第一代員工,我也就更安心地在黃麓扎下來了”。
原來,20世紀80年代,劉靖的父親劉錫宏在安徽省外貿部門從事文房四寶出口業務,有一次,一位日本客戶略顯遺憾地對他說:“粉蠟箋是中國最好的紙,只可惜現在再也造不出來了。”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對紙箋有著特殊感情的劉錫宏。
后來劉錫宏全身心地投入到粉蠟箋的研制中,并于1992年成立了合肥“掇英軒”文房用品研究所,后由于成本原因將其搬回老家巢湖黃麓鎮,改造成家庭工廠,一邊生產簡單的紙箋產品,一邊研究傳統紙箋加工技術。“掇英軒”意為拾掇最好古紙的地方,可見劉錫宏想恢復這項失傳技藝的強烈心愿。可惜歷經多年,粉蠟箋始終沒有研制成功。
榮寶齋“一戰成名”
父親的苦心孤詣,劉靖看在眼里,記在心里。1997年,劉靖辭掉省城工作回到老家,不顧鄉鄰的非議,毅然接手了“掇英軒”。在父親的建議下,劉靖打算從復活粉蠟箋著手。
由于之前閑暇時跟著父母干過紙箋加工的活,彼時劉靖已熟練掌握了紙箋加工技藝,整個流程做起來得心應手,關鍵在找尋配方。
劉靖收集了一些不成功的粉蠟箋,又到當時的安徽省博物館、涇縣宣紙博物館尋找館藏的實物進行對比。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讓“粉”與“蠟”融合的問題。粉吸墨,蠟拒墨。粉多了,紙張容易斷裂;蠟多了,紙張不易書寫。要解決這個矛盾,原料的選用至關重要。“我們把市場上能看到的礦物粉、蠟、膠等各種輔料都買回來,4個月的時間,在老鼠橫行、條件艱苦的老屋里,我經過幾百次的試驗,最終試出了合適的配方,做出了一張質量上乘的粉蠟箋小樣。”劉靖和父親激動不已,馬上拿著樣紙找到了省文房四寶研究所所長田恒銘,田所長試筆后對這張小樣大加贊賞,認為它可與明清粉蠟箋相媲美。至此,這種失傳百年的手藝終于在劉氏父子手中重生。
1998年梅雨季節,劉靖承接了日本客戶的幾百幅手繪描金粉蠟箋訂單,沒想到竟出了問題:紙箋上用銅粉手繪的仿金圖案一兩個月后全變黑了,原來銅粉遇潮氣會變黑,粉蠟箋做好后須晾干、防潮。沒辦法,粉蠟箋只好全部返工,劉靖和工人們不分晝夜地奮斗了3個月,最后三天三夜都沒合眼。
這次“驚心動魄”的意外倒逼著劉靖去“升級”粉蠟箋。后來,劉靖輾轉從上海買來金色珠光粉試驗,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一點也不變色。“后來,我們就用金色珠光粉代替了銅粉,用在粉蠟箋、泥金箋、金銀印花箋等紙箋上,這在當時還是個不外傳的秘密。”劉靖笑著說。
1999年底,為了打開國內市場,劉靖和父親帶著改良后的粉蠟箋,風塵仆仆地趕往北京榮寶齋。榮寶齋的業務經理袁良頓時眼前一亮,試筆后感覺很不錯,當即就買下他們帶去的所有粉蠟箋產品。第二天,榮寶齋營業大廳最核心的兩節柜臺被騰空,放上了劉靖的粉蠟箋。大廳中間幾根柱子上的字畫也被撤下來,掛上了他的4幅作品。榮寶齋曾評價道:“掇英軒粉蠟箋制作技藝可代表中國傳統手工制紙之最高技藝。”
得到榮寶齋的認可后,掇英軒生產的粉蠟箋在國內的市場隨之被打開,劉靖憑借復活傳統粉蠟箋工藝“一戰成名”。
盡心盡力做非遺傳承
“我們掇英軒現在除了粉蠟箋,還相繼恢復和生產了泥金箋、絹本木版水印箋、流沙箋、金銀印花箋、刻畫箋等。”劉靖如數家珍般數出了他的“佳作”。這些作品大大豐富了我國紙箋品種。2008年,以劉靖為代表傳承的“紙箋加工技藝”被國務院批準、文化和旅游部評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他本人也于2018年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紙箋加工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為了傳承這項技藝,他多年堅持為學生和更多人開班授課,2019年由他擔任副主編之一的“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項目《中國手工紙文庫·云南卷》及《中國手工紙文庫·貴州卷》上、下卷也相繼出版發行。非遺傳承、著書立說、培訓工人,這幾乎成了劉靖生活的重心。下一步,劉靖將有更大的手筆,黃麓鎮上占地14畝的“紙箋加工技藝傳承基地”已拔地而起,他將會盡力讓更多人接觸和愛上這門傳統技藝。
(田龍華摘自《戀愛婚姻家庭·養生版》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