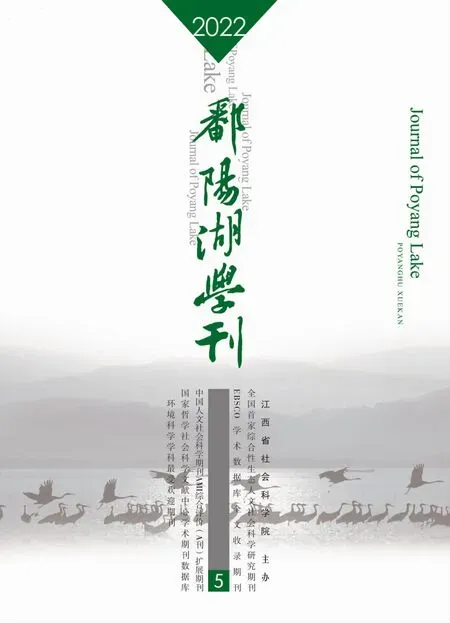近20 年來美國內戰環境史研究趨向
⊙朱守政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戰爭史研究出現了環境史維度分析的轉向,①參見Ferenc M.Szasz,“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the Land: Gruinard Island,Scotland,and Trinity Site,New Moxico as Case Studi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no.4,Winter,1995,pp.15-30;Edmund Russell, War and Nature:Fighting Humans and Insects with Chemicals from World War I to Silent Spr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Richard P.Tucker and Edmund Russell, 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Charles E.Closmann,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9.環境史學者紛紛利用戰爭留下的生態遺產來分析軍事沖突之下人類與環境之間發生的互動。隨著環境史與新軍事史相互交叉影響,西方史學界對傳統美國內戰史以人物和事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理念進行反思。學者們不再局限于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領袖的研究,而是選擇更廣泛的參與者和戰爭構成因素進行研究,并把非人類生物納入探討的范疇。如一些學者所說,美國內戰是“一個不僅影響了人類,而且改變了自然系統、重塑了原本復雜的人類、他者生物和物理環境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生態事件”。②參見Judkin Browning and Timothy Sil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20,p.4.這場持續了4 年的南北戰爭,不但讓奴隸制度走向瓦解,更重要的是讓人們重新認識了自然荒野。環境史視角的引入,為內戰史書寫增添了更多的分析角度和結構層次,為進一步認識美國環境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窗口,在解構以往內戰是二元因素(經濟和道德層面)所激化的奴隸解放沖突論之后,賦予了第三重生態的歷史解釋。特別是在杰克·坦普爾·柯比(Jack T.Kirby)發出對內戰史研究的呼吁之后,①Jack T.Kirby, Mockingbird Song: Ec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South,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8.(該書榮獲2008 年班克羅夫特獎)關于南北戰爭的環境史討論逐漸受到內戰史和環境史學界的重視。②2001 年11 月5 日,聯合國大會宣布每年11 月6 日為防止戰爭和武裝沖突破壞環境國際日,也鼓勵了內戰史研究的環境轉向。
當前國內對美國內戰環境史的研究尚屬一個新領域,甚至因為一直以來內戰史研究被傳統方法所壟斷而被稱為“老戰場中的新戰斗”,研究成果主要是對一些作品的介紹或對其作為一個新領域出現意義的簡單評價。如賈珺在《為什么要研究軍事環境史》中提出環境史是內戰史研究的新興影響力,羅超在《美國史學界關于內戰記憶研究述評》中注意到內戰記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③賈珺:《為什么要研究軍事環境史》,《學術研究》2017 年第12 期;羅超、高春常:《美國史學界關于內戰記憶研究述評》,《世界歷史》2020 年第2 期。王光偉在分析內戰中的傳染病問題時,對造成傳染病傳播的歷史環境也表示了關注,參見王光偉:《美國內戰中的傳染病及其對戰爭進程的影響》,《世界歷史》2019 年第3 期。雖然作者并未就相關問題展開敘述,但卻為包括本文在內的后續研究進一步梳理美國內戰環境史提供了啟示。
一、內戰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及發展
2001 年,內戰史研究和環境史研究聯盟的支持者、班克羅夫特獎獲得者杰克·柯比(Jack T.Kirby)著文呼吁人們要關注內戰環境史。他認為,此前關于內戰史的研究已經很多,但是生態維度的內戰史分析寥寥無幾,甚至可以說還沒有出現,④Jack T.Kirby,“ The American Civil War:An Environmental View,”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July,2001,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tserve/nattrans/ntuseland/essays/amcwar.htm,August 10,2022.美國內戰“是第一場現代戰爭,因此在類別和規模上極大地不同于以往的美國軍事沖突”。⑤Lisa M.Brady, War upon the Land: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Landscapes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p.1.炮彈有效射程的提升意味著戰爭毀滅能力的升級,火車為前線輸送源源不斷的兵力和軍需物資在客觀上又為長時間戰爭創造了可能。歷時4 年的南北戰爭讓內戰的足跡深入到美國整個景觀之中,乃至改變了國家機器。如保羅·薩特(Pual S.Sutter)所說,美國自然保護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立法是內戰的產物;隨著美國農業部的成立以及《宅地法》(Homestead Act of 1862)、《莫里爾土地法》(Morrill Act)的通過,美國國家農田環境發生了重大歷史變革,促生了諸多環境管理部門;⑥Pual S.Sutter,“Waving the Muddy Shirt”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p.233-234.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內戰史大部分是發生在戶外的”,⑦Kenneth W.Noe,“ Fateful Light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eather and Climate to Civil War History,” 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16.為什么內戰史和環境史兩個既有趣且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領域是彼此區分開來,而不是相互合作?⑧Jack T.Kirby,“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 Environmental View,”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July,2001,http://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tserve/nattrans/ntuseland/essays/amcwar.htm,August 10,2022.《美國內戰:一個環境視角》可謂第一篇嚴格意義上以人與環境關系來考察內戰(或者任何戰爭)的文章,盡管柯比撰文的目的不是明確提供這場戰爭的歷史,而是為各種研究提供急需的主題建議,①Lisa M.Brady,“The Wilderness of War:Nature and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0,no.3,Jul.,2005,pp.21-47.但作者的疑問卻凸顯了其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傳統軍事史專業性較強,且該領域的學者多為軍人身份,他們更傾向于對戰爭整體情況進行敘述,寫史的目的比較清晰,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為軍事理論研究提供素材,二為頌揚戰爭軍事英雄和高超的戰術。②許二斌:《“新軍事史”在西方史學界的興起》,《國外社會科學》2008 年第4 期。他們可能考慮到戰爭中的環境因素,但并不會選擇環境史視角來分析戰爭。其次,就地域空間而言,“內戰史屬于東部地區討論話題,而環境史出身于西部,兩者有空間上的阻隔”,③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1.史家的學術背景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彼此間的結合。再次,與傳統史學相比,環境史是一門新學科,它提倡用人與環境的關系來解釋歷史變化,強調生物的歷史能動性,這在“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傳統中顯然是一種另類的存在,就史學的學科地位來看尚處邊緣。這也解釋了為何內戰環境史如此姍姍來遲。
不過這種情況很快隨著環境史學科的壯大和新軍事史的發展出現轉變。柯比的呼吁在2002 年的美國環境史學會年會的小組會議上得到了回應。④Richard P.Tucker and Edmund Russell, 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 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4,p.vi.此后,學者們紛紛對內戰爆發的原因、過程及戰后影響開始了環境史維度的論述。內戰這片曾經的殺戮戰場,很快成為環境史耕耘的“沃土”。泰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直接在他的作品中指出,“內戰是一場爭奪糧食的大作戰”,⑤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89-98.南北方不同耕作模式在戰爭的進程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馬克·費格(Mark Fiege)也提出了幾乎同樣的看法:“他們為各自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而戰,對自然和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造成了那些分歧。”⑥Mark Fiege,The Republic of Nature: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d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p.201.而這一分歧“根源于南北方對于美國西部的未來規劃”。⑦Mark Fiege,“Gettysburg and the Organic N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Richard P.Tucker and Edmund Russell,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ity Press,2004,p.94.對于戰爭進程中南北雙方物資供給方面的矛盾,“約翰·馬耶夫斯基(John Majewski)認為,南方的酸性和營養不良的土壤抑制了其戰前的經濟現代化,而北方擁有驚人的產量,能夠連續種植,生產優質的牲畜飼料,并為穩定多樣的大型經濟提供了堅實的生態基礎”。⑧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0.關于內戰的生態思想影響,學者們開始反思將荒野保護和國家公園概念的誕生歸因于工業主義的反應,浪漫主義和超驗主義的影響,以及交通與旅游的刺激的做法。威廉·德弗雷爾(William Deverell)還發出了“根據內戰重新審視國家公園運動的啟動”的呼吁,認為飽受戰爭蹂躪的共和國當下急需來自自然的那種古老的心理慰藉和精神鼓舞。⑨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4.當美國內戰趨近于解決奴隸制這一道德問題時,面對人類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有些人開始了另外一種思考:“人們如何協調他們對大自然的濫用與他們保護大自然的需要(和義務)?”“人忘了,上帝把對地球的用益權賜予他,并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他的消費需要,更不是為了滿足他恣意揮霍的需要”。①羅德里克·納什:《大自然的權力:環境倫理學史》,楊通進譯,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 年,第44—45 頁。這場美國歷史上傷亡極大、牽扯到整個國家,甚至影響世界未來格局的南北戰爭,不但在戰后對國家統一、奴隸的解放和南方種植制度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南北方的土地景觀造成了空前的影響。其影響不僅體現在農業景觀方面,而且體現在包括文化、軍事和社會景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開啟了美國的生態理念。
2011 年10 月,第三屆“非內戰”年會進行了以“藍色、灰色和綠色”為主題的內戰史討論,這是第一次專門討論內戰環境史的學術會議,《藍色、灰色和綠色:一部內戰環境史》這部代表性著作即為此次會議的結晶。②該書收錄的文章皆來源于第三屆“非內戰”年會。Brian A.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vii.2012 年,內戰史權威雜志《內戰史》(Civil War History)開辟了有關內戰史與環境史相結合的專欄,并特邀梅根·凱特·尼爾森(Megan Kate Nelson)擔任客座編輯,由麗薩·布萊迪(Lisa Brady)等學者執筆對內戰環境史的發展歷程、理論范式、實證研究及未來預想進行了論述。同年,專業期刊《內戰時期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Civil War Era)也專門由斯蒂芬·百瑞(Stephen Berry)組織了一期“內戰時期研究的未來”的專題討論,同樣作出了把人與生態關系列為內戰史未來研究重點的論述。③Megan Kate Nelson,“Guest Editor's Note,” Civil War History, vol.58,no.3,Sep.,2012.這意味著內戰環境史研究隊伍、成果已經初具規模和關注熱度。據統計,2006—2017 年間,美國環境史學會(ASEH)年會共設軍事主題的討論組或圓桌會議56 個,文章或發言192 篇,其中關于內戰主題的討論量排在第三,僅次于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主題的討論量。④賈珺:《為什么要研究軍事環境史》,《學術研究》2017 年第12 期。如約翰·麥克尼爾(John R.Mc-Neill)所指出的,未來極具潛力的環境史研究領域應該包括內戰環境史。⑤John R.McNeill,“Future Research Need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gions,Eras,and Themes,”RCC Perspectives, no.3,2011,pp.13-15.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本文的撰寫才成為可能。當然,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書寫目的并不是為了使非人類生物能動性取代人類的歷史能動作用,而是為了展現在那種不對等和不可預測的軍事環境背景下兩種不同的能動性是如何進行相互影響和對抗的。⑥參見Chris Pearson, Mobilizing Nature: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 and Militarization in Modern France, Manchester:Mancheter University Press,2012,p.6.
今天,距美國內戰爆發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以環境視角重新對19 世紀60 年代的美國南北戰爭進行解讀,除了對戰爭引發的自然生態的破壞進行論述之外,同樣意在對生態環境在戰爭中所起到的能動作用展開討論,改變傳統以“人類為中心”的內戰史研究范式,擴大內戰史研究的領域和主題,為人們認知美國歷史上環境主義運動的發源增添新的視角。
二、內戰環境史研究的主要議題
如麗薩·布萊迪(Lisa M.Brady)所說:“內戰可以被視作美國人對于自然的理解和互動。”⑦Lisa M.Brady, War upon the Land: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Landscapes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p.2.新世紀以來,隨著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豐富,內戰環境史研究在南方森林與農業景觀變遷、內戰時期的動物及美國生態思想形成等多個議題上有了更深入的推進。戰爭與環境如何相互影響,自然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塑造了內戰?內戰環境史家為了證明環境在內戰過程中絕非偶然或短暫地作用于戰爭,自然環境和自然力量影響著戰爭的整個進程,他們從多個維度對內戰的歷史進行了新的敘述。
(一)內戰與農業景觀
南北戰爭雖然沒有徹底解放黑人并解決美國存在已久的種族問題,但是北軍奉行的“焦土政策”和“向海洋進軍”戰略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自然環境和南方的農業景觀。如莫爾丁(Erin Stewart Mauldin)所言:“內戰并不是單純的軍事或政治事件,而是一次深刻的環境事件。”①Erin Stewart Mauldin, Unredeem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ivil War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Cotton Sout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4.有著現代軍事院校背景的內戰主要將領[如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威廉·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等,他們皆畢業于西點軍校]深知“掌握自然的軍隊,即掌握了戰爭的主動”,②Mark Fiege,“Gettysburg and the organic Natur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Richard P.Tucker and Edmund Russell,Natural Enemy,Natural Ally: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ity Press,2004,p.100.他們充分考慮并借助了自然的力量,極大地加深了美國人與北美自然的互動。例如,在1863年5 月的昌塞勒斯維爾戰役中(Chancellorsville),李將軍利用了茂密叢林提供的掩護場所擊敗了擁有兩倍軍力的約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將軍,成就了著名的以少勝多的弗吉尼亞南部戰役;③John R.McNeill,“Woods and Warfare in World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9,no.3,Jul.,2004,pp.389-340.為了拖延敵軍的行軍速度,少將托馬斯·新德曼(Thomas Hindman)甚至敦促阿肯色州的老百姓砍倒道路兩旁的所有樹木,并在必要時刻“燒掉所有東西”。④Joan E.Cashin, War Stuff:The Struggle for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106.內戰不但直接破壞了自然景觀,而且間接地影響了農業景觀結構。黑人奴隸解放、牲畜的大量死亡和日益退化的土地讓南方原有的自給自足經濟走向瓦解,高額的棉花價格誘發的種植熱潮進一步搶占了糧食作物的土地空間,最后就如麗薩·布萊迪(Lisa Brady)所言,“南方單一的棉花種植依賴降低了南方聯軍的供給能力,也促成了其后期戰爭的失敗”,⑤Lisa Brady,“Environmental Histories,” in the Forum of “The Future of Civil War Era Studies,” The Journal of the Civil War Era, vol.2,no.1,Mar.,2012,p.8.安德魯·史密斯(Andrew F.Smith)甚至認為“饑餓是造成南方投降的主要原因”。⑥Andrew F.Smith, Starving the South:How the North Won the Civil War, New York,Ny: St.Martin's Press,2011,p.203.
當然,戰爭并未使所有南方地區的種植業衰敗。密西西比河封鎖阻隔了北方的煙草流入,南北軍隊在弗吉尼亞地區和北卡羅來納地區的長期戰事,客觀上為地區的煙草消費提供了市場。皮埃蒙特南部的香煙高品質聲譽和戰爭帶來的近乎壟斷的市場優勢,讓亮葉煙迅速在該地區崛起。亮葉煙的發展是內戰農業景觀衰敗普遍論中的例外,而其更巨大的影響是致使那里延續了兩個世紀之久的南方農村種植模式一去不返。如保羅·薩特(Pual S.Sutter)所言:“如果我們不仔細審視19 世紀的美國農業歷史,我們將無法真正了解內戰;同樣,如果我們缺乏對于內戰遺產的認知,我們就不會理解美國歷史上的農業發展軌跡。”⑦Pual S.Sutter,“Waving the Muddy Shirt,”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231.長期無節制的砍伐與耕種耗盡了貧瘠土地中僅有的肥力,亮葉煙雖曾一度讓這里富裕,但最后也讓這里成為“新南方的聲名狼藉之地”。①Drew A.Swanson,“War Is Hell,So Have a Chew: The Persistence of Agroenvironmental Ideas in the Civil War Piedmont,”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e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181.
(二)戰爭“參與者”和能量來源
內戰對非人類動物的影響與其對自然景觀的破壞一樣深刻。如賈珺所言:“無論是作為戰友、戰爭吉祥物、軍火庫中的彈藥,還是戰場本身的一部分,動物的命運都不可避免地與人類事務聯系在一起。”②賈珺:《英國信鴿在“一戰”中角色的轉換與形象變遷》,《世界歷史》2021 年第1 期。近年來內戰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對內戰的進程和影響因素方面又增加了新的解釋維度。安德魯·貝爾(Andrew Mcllwaine Bell)呼吁歷史學者重視戰爭中的蚊子:在戰爭還未打響時,“一群整裝待發的蚊子軍隊就開始等候身著藍色軍服的北方士兵了,它們的每一次叮咬都如同戰場上直面與身著灰色軍服的南方士兵交鋒一般致命”。③Andrew Mcllwaine Bell, Mosquito Soldiers:Yellow Fever,Malaria,and Cours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19.在北軍攻克南方駐守在密西西比河重要的駐點維克斯堡時,潮濕、溫暖的氣候,以及威廉姆斯(Thomas Williams)部隊試圖挖掘新的水道繞過維克斯堡而對土地和森林采取的破壞行動,都為蚊子的繁殖提供了良好條件,致使短短數日之內3200 人的部隊中有75%的士兵喪命。即便他后來的接替者戴維斯(Charles Davis)也遭遇了40%的部隊傷亡,最后海軍指揮官不得不宣布“推遲維克斯堡的一切行動,等待發燒(黃熱病、瘧疾)季節結束”。④Andrew Mcllwaine Bell, Mosquito Soldiers:Yellow Fever,Malaria,and Cours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p.58-60.在南方戰場上,士兵和蚊子的關系就是整個內戰中人與環境互動的直接體現。南方人為了打退沒有流行病學經驗的北方聯軍,他們甚至“把感染黃熱病的人的衣物郵寄到北方,試圖在那里引發疾病”。⑤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1.由此可見,當時在戰場上人們對這些“自然武器”的能動作用已有相當意識。
同樣,牲畜在戰爭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賈德金·布朗寧(Judkin Browning)和蒂莫西·西爾弗(Timothy Silver)認為,“軍隊依靠馬匹和騾子行進,士兵需食用牛和豬戰斗”,⑥Matthew Stith,“Review: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Civil War Book Review, vol.23,Iss.1,2021,pp.1-4.“馬匹、騾子和牛搬動了所有在葛底斯堡雇傭的補給車、火炮和救護車。馬背上的軍隊對雙方都是不可或缺的”。⑦Judkin Browning and Timothy Sil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20,p.103.牲畜在戰爭中充當著交通工具和能量來源,但大量牲畜的聚集也為動物傳染病的滋生提供了理想的溫床,一種在18 世紀末首次在北美發現的馬疽病在內戰的物質流動助推下迅速傳播。在1864 年1 月到1865 年4月之間,僅華盛頓旁的吉斯伯勒(Giesboro)的一個軍需庫即損失了17000 匹戰馬。⑧Erin Stewart Mauldin, Unredeem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ivil War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Cotton Sout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90.而戰前零散現于美國東北部的豬瘟,也因戰爭巨大的物質流通而大面積傳播開來。“1863 年11 月,總物資供應處的懷特少校報告說,由于豬瘟的肆虐,南方邦聯的培根供應即將耗盡,未來將無法補充”,進而釀成了如瓊·卡辛(Joan E.Cashin)在她的作品《戰爭原料:美國內戰中對人力和環境資源的爭奪》①Joan E.Cashin, War Stuff: The Struggle for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中所說的,士兵們把資源的獲得渠道轉向普通民眾。據統計,戰爭期間南方地區牲畜數量總體大幅度減少,平均損失近馬匹數量的20%、牛群數量的20%、豬的數量的30%。②Erin Stewart Mauldin, Unredeem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ivil War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Cotton Sout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84-98.作為肉類蛋白質、交通和生產工具,馬、牛、豬的大幅度減少不但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而且造成了以牲畜糞便改善土壤豐度的傳統農業方式走向終結。就內戰發生的故事而言,南北戰爭爆發讓美國人既成為自然毀滅的始作俑者,也成為自己的“生態難民”。這也促使美國人注意和反思動物與人這種始終相伴的時空關系。如蘇珊·南斯(Susan Nance)所說:“動物一直都在,世界的歷史中從未有過純粹的人類時刻。”③Susan Nance,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5,p.5.
(三)內戰與美國人的生態觀
長期以來,戰爭除了對物質景觀的變遷和動物群體造成影響之外,對人類的生態思想也產生了極大作用。凱瑟琳·梅耶(Kathryn S.Meier)認為,美國內戰是“美國環境思想發展的形成時刻”。④Kathryn S.Meier, Nature's Civil War: Common Soldi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1862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the North Carolina Press,2013,p.9.戰爭不但對士兵造成身體上的影響,而且會對士兵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影響。野外戰爭讓人們對環境與士兵健康之間的關系建立了新的認識,面對戰火焚燒和槍炮轟炸的毀滅景象,原本的“征服荒野”進步理論似乎也開始被打上問號。滿目的荒野殘垣讓士兵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們渴望令人愉悅的環境,為了讓自己的營地變得更有家園的味道,無論是聯邦軍還是南方叛軍都積極進入森林,并把自然元素帶回來。⑤Megan Kate Nelson, Ruin Nation: Destruc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p.130.這時士兵們開始通過種植鮮花和樹木,重新將自然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或者選擇“掉隊”⑥Kathryn S.Meier, Nature's Civil War: Common Soldi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1862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the North Carolina Press,2013,p.2.梅耶將私自偷偷短時間離開部隊、在自然中暫時尋找寬慰以緩解心理上的緊張的行為稱為“掉隊”。來完成自我的照顧。這些或許也揭示了為何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公園建設提議在戰后獲得如此多的美國人支持的原因。美麗景觀極大地作用于人們的思想,“幾乎沒有人不會因身臨其境于如此美好的景色而深深觸動”。⑦L.W.Greene, Yosemite: The Park and Its Resources, vol.1,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National Park Service,1987,p.56.在那里,“新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支持者看到了救贖;保存下來的自然可以治愈戰爭的創傷,并展示共和政府的持續活力”。⑧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2.
戰后的環境廢墟對人類的影響不僅僅是物理上的,它也改變了人們對荒野的定義。就像布萊恩·德雷克(Brian Allen Drake)所說:“戰爭引發的前所未有的破壞確保了這個時代關于自然文化觀念也與戰火密切聯系著。”⑨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2.戰爭帶來的環境毀滅讓美國人不再把森林砍伐視作一種進步,而是把景觀的破壞與人身體的損傷建立聯系,進而引導到環境保護和資源保護主義運動上來。以國家公園運動的發起為例:1864 年聯邦政府關于約塞米蒂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和1872 年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的運動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戰后的這種需求,它們與“美國由戰爭引起的醫療和心理需要上升相吻合”。①William Deverell,“Redemptive California?Re-thinking the post-Civil War,” Rethinking History, vol.11,no.1,Mar.,2007,pp.61-78;Adam W.Dean,“Nature Glory in the Midst of War: The Establishment of Yosemite State Park,” Civil War History, vol.56,Dec.,2010,pp.386-419.內戰這一影響美國環境思想和環境政治發展歷史的關鍵事件,不但促生了新的國家機器,也加速了美國環保意識的平民化、大眾化,讓人們認識到荒野(自然)并不是文明的對立面,帶有血腥和欲望的野蠻才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禮,讓人們認識到荒野與人類歷史發展之間的關系,認識到“保護荒野的最終意義是保留文明”。②羅德里克·納什:《荒野與美國思想》,侯文蕙、侯鈞譯,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94 頁。
總體來說,“戰爭不僅代表著人類社會和政治關系的崩潰,而且也代表著現有環境秩序的解體”。③Andrew Mcllwaine Bell, Mosquito Soldiers:Yellow Fever,Malaria,and Cours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7.經過二十來年的發展,內戰環境史研究主題涉及內戰影響范疇的諸多方面,讓人們對近代美國乃至當下美國人的生態思想和史學界的荒野認知都有了新的理解,同時也認識到了內戰引發生態破壞及其影響的嚴重性。但正如保羅·薩特批評“在戰爭環境史的研究中常有將戰爭的環境研究集中在傳統的軍事歷史主題上”④Pual S.Sutter,“Waving the Muddy Shirt,” 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226.的現象,當下的內戰環境史研究出現了一些新趨勢,諸如對戰場局部微小事件進行環境視角的解讀,追蹤內戰的長期性影響,以及對內戰進行大尺度的空間探討等。
三、內戰環境史研究的新趨向及其問題
近年來,內戰環境史研究在空間、時間和研究路徑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它一方面既在空間上走出原來囿于南北之間的敘述模式,開展“大內戰環境史”研究,把戰爭引發的環境變遷聯系到戰爭后方、西部乃至全球范圍,又在時間上把研究拓展到戰后長期的環境恢復問題,深入分析內戰留給現代美國人的歷史遺產;另一方面在研究路徑上傾向于從微觀切入,通過梳理細小的景觀變遷來論證內戰給整個環境帶來的影響。
(一)轉向“大內戰環境史”研究
受到環境史研究特有的宏大關懷,近年來內戰環境史研究不僅在國家、世界層面開展了探討,而且對內戰產生的環境影響進行了長時段分析。如2019 年德雷克(Brian A.Drake)在《戰爭的分水嶺:環境史與“大內戰”》中談到,這場19 世紀發生在美國的重大事件產生的影響像沖擊波一樣蔓延至戰場之外,不僅塑造了一個世紀或者更久的種族關系、經濟和選舉政治,而且對美國和更大尺度的空間產生了環境影響。⑤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p.238-239.那種對戰場、士兵經歷以及1861—1865 年區間的敘述顯然不符合當下全面研究內戰環境史的要求,特別是其研究風格,早在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的著作《自然的大都市》中就作出了示范。克羅農在回顧芝加哥的發展史時,曾談及這場戰爭造成的景觀和資源變遷與這座西部大都市崛起之間的密接關聯:“為保證150萬加入戰爭中的士兵超過5 億噸的腌制豬肉和培根消耗”,①威廉·克羅農:《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與大西部》,黃焰結、程香、王家銀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330 頁。芝加哥迅速成長為“豬肉的王國”。麗薩·布萊迪在分析內戰與環境的關系時也同樣肯定這種跨州際的聯系。她直言:“事實上,聯邦政府的勝利既取決于它對西部土地和資源的控制,也取決于它在戰場上的大戰略或實力。”②Lisa M.Brady,“Environmental War,” in Aaron Sheehan Dean,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p.249-267.中西部的大草地和平原提供充足的谷物和牛肉,明尼蘇達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充沛的森林資源補給,愛達荷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山區的豐富黃金、銅和白銀資源儲備,讓北方實現了對南方資源實力方面的絕對優勢。顯然,這場由南北之間的對抗產生的生態影響,已經輻射到更遠的美國西海岸地區。
正如斯文·貝克特(Sven Beuckert)所言:“弗吉尼亞農村地區的一場戰斗的余波震及貝拉爾和下埃及的小村莊,巴西農民對農作物的選擇取決于他對利物浦市場的判斷,而聯邦攻陷里士滿的消息傳到印度海岸后,孟買的房地產價格立刻崩潰。”③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徐軼杰、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年,第239 頁。謝爾曼將軍(William T.Sherman)的“向海洋進軍”(March to the Sea)的封鎖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內戰的全球生態影響轉向。莫爾丁形容其如同章魚張開了爪子一般,將一切卷入懷中,包括牲畜、作物、資源等,只留下了一個南方廢墟。受到內戰的影響,占據全球市場巨大份額的美國南部棉花產量銳減,極大地影響了全球紡織市場。英法為了維持其紡織業的持續發展,很快把目光投向了印度、埃及。而由此產生的影響是:短短數年之間,一個曾經的糧食出口國變成依靠糧食作物進口的國度。在“1863 年夏天,埃及幾乎所有的牛都死于疾病,一場糧食危機爆發,成千上萬的埃及農民喪生”。④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徐軼杰、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年,第286 頁。這無不印證了這場發生在北美大陸的國家內部戰爭的全球性影響。就如麥克尼爾(J.R.McNeill)所言:“在1789—2003 年之間,美國的軍事行動有著全球性的生態足跡。”⑤J.R.McNeill and David S.Painter,“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the U.S.Military,1789-2003,” in Charles E.Closmann,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31.
關于內戰環境史研究的時間維度,一直以來學者們往往把重點放在戰前和戰中。就如伍德(Michael E.Woods)所揭示的那樣,內戰環境史研究對戰前備戰和戰中戰事都有深入的關注,但是對戰后重建問題的關注稍有缺失。⑥Michael E.Woods,“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ivil War Era: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51,no.2,May,2017,pp.349-383.黑人奴隸解放、勞動力缺乏和牲畜的大幅度減少,造成了南方原有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匱乏,國際市場上高漲的棉花價格引發了棉花種植又一輪擴張,繼而進一步加深了戰后南方種植結構的變遷。如莫爾丁(Erin Stewart Mauldin)所說,“棉花帝國在開拓邊疆的道路上一往直前,而等待它的是環境帶來的終極束縛”,⑦Erin Stewart Mauldin, Unredeem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ivil War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Cotton Sout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40.當土地無力提供帝國膨脹亟需的營養之時,亦是棉花產業轉衰之時。內戰的生態遺產在之后的漫長歲月中逐漸顯露,并以人與環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體現出來。一般來講,戰后生態的持續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在新農業模式方面,戰后南方的密集型農業取代了傳統農業方式,農民原來的自給自足條件消失,南方的生態景觀進一步惡化;其二,棉花的大面積種植使內陸地區的農民進入到處于較低溫度狀態和較短生長季節的阿巴拉契亞山脈南部;其三,肥料適用于在較高海拔地區施用,如果向北流向棉花種植的傳統邊界,就會使土壤退化加劇,以致佐治亞州中部土壤因受棉花種植的侵蝕將需要長達一萬年才能恢復。①相關內容可參見Timothy Johnson,“Reconstruction the Soil:Emancipation and the Roots of Chemical-Dependent Agriculture in America,” 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p.204-205.也因為如此,“種植園主們贏得了‘農田殺手’的名聲”。②Donald E.Davis,Craig E.Colten,Megan Kate Nelson,Barbara L.Allen and Mikko Saikku, Southern United Stat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ABC-CLIO,2016,p.127.所以,就像德雷克(Brian A.Drake)所說的,局限在“戰時”研究的內戰環境史并不合理,“它應該超越戰爭時代,包括重建、‘鍍金時代’、‘進步時代’等甚至更遠的歷史”。③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39.
(二)開展微觀研究
“內戰好比一碗被大幅度攪動的生物湯汁。”④Brian Allen Drake,“Introduction: New Fields of Battle: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and the Civil War,” 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8.環境史學者受后現代及微觀史學的影響,開始觀察除主要是“食材”和“湯水”之外的其他輔料,著手在大畫卷的環境史研究中微觀取景、深挖細研。約翰·蘇拉瑞(John Soluri)和約翰·麥克尼爾(John R.Mc-Neill)對美國、洪都拉斯的香蕉葉病問題和大加勒比地區的蚊子傳染病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就是這方面的成功范例。⑤John Soluri, Banana Cultures:Agriculture,Consumption,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Honduras and the United State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5;John R.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bbean,162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他們通過這些代表過去的個體化歷史,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和確認它們各自所屬的歷史結構與范疇。⑥鄧京力:《微觀史學的理論視野》,《天津社會科學》2016 年第1 期。這種微觀的環境史研究范式,無疑對內戰環境史研究也產生了影響,并常常以兩種方式呈現:一是微觀個案研究,即通過小地區小事件小人物小生境的特點來反映內戰中人與環境之間的密切聯系,如皮埃蒙特南部地區因戰爭而迅速崛起的亮葉煙草及其引發的地區景觀變遷;二是以微觀有機體為線索,將其貫穿在宏大的時空背景中,來驗證微小有機體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歷史能動性,如安德魯·貝爾(Andrew M.Bell)利用蚊子的線索講述了在南北戰爭期間“那些由蚊子組成的南部沿海地區保護城墻,證明了有時要比南方叛軍的軍火防御屏障抵御北方聯邦更加有效”。⑦Andrew Mcllwaine Bell, Mosquito Soldiers:Yellow Fever,Malaria,and Cours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p.39.微觀視角的引入發現了總體性研究和普遍化之外的異元,亮葉煙草產業的興起就是內戰普遍性毀滅的例外,而由蚊子參與的戰爭更是形象地證明了微小有機體的歷史能動性。正如埃默里·托馬斯(Emory M.Thomas)在《奇怪的戰爭:內戰邊緣的故事》一書中所說的:“‘怪異’真是太棒了!處于戰爭的邊緣話題,往往確實是‘尖銳’的——是我們的研究似乎正在走向的前沿。”⑧Emory M.Thomas,“Foreword,” in Stephen Berry,ed., Weirding the War: Stories from the Civil War's Ragged Edge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1,p.xi.內戰史的微觀研究實則深化了歷史的整體解釋,以看似碎片化的具體研究還原戰爭的全景,進而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內戰的整個過程。
當然,環境史視角的引入讓老樹開新花,促生了“老戰場中的新戰斗”,讓人們從人與環境間的關系角度重新認識了內戰,但這一過程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內戰環境史研究過于關注和夸大環境及其作用,在論述中淡去了歷史中的人,即主要強調自然因素對內戰的決定性影響,如:認為極端的天氣造成了南方的物資短缺,進而影響到人力、動物和土地占有方面的損失,卻未考慮其組織和運輸方面的弱點;①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40.突出戰爭帶來的生態環境的災難,過于強調戰爭帶來的毀滅,進而忽視了南北戰爭所帶來的奴隸解放和國家進一步統一的進步意義。這種情形也容易造成薩特(Pual S.Sutter)所指出的困擾:環境史家過于堅持“自然重要”(以生態為中心的思考)的邏輯,或因為明顯的學派偏見,阻礙與內戰歷史學家的融合,不利于環境史學走進歷史研究主流。②Pual S.Sutter,“Waving the Muddy Shirt”in Brian Allen Drake,ed., The Blue,the Gray,and the Green: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5,p.227.第二,在歷史橫縱的跨域空間比較研究上有待突破。在南北戰爭爆發的同時,太平洋的彼岸太平天國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對于同樣歷時多年、對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南北戰爭”而言,自然環境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異同有著非凡的比較意義。從時間縱向來說,內戰前不久結束的美墨戰爭對于南方軍隊如何與自然相處并如何對其展開利用方面無疑會有著影響。麥克尼爾就提出,內戰期間士兵在荒野中的自我照顧應該考慮美墨戰爭的歷史經驗。③J.R.McNeill,“Review: Nature’s Civil War: Common Soldi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1862 Virginia,”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81,no.1,Feb.,2015,pp.201-202.內戰中環境利用問題存在多少繼承,這種對戰爭環境的研究也值得挖掘。第三,戰后廢墟的文化解讀弱化了戰爭物質影響的長期性。如凱瑟琳·梅耶(Kathryn Shively Meier)所言,在《廢墟的國度:破壞與美國內戰》中作者尼爾森高估了內戰廢墟的短暫性。④Kathryn Shively Meier,“Review: Ruin Nation: Destruc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8,no.1,Jan.,2013,pp.213-215.內戰給南方土地景觀、動物和所有美國人帶來的物質和思想文化上的傷害與震動是深刻久遠的,盡管毀滅的森林再次長出茂密的松樹,但是原有的生態結構已經改變。
綜合上述問題,未來的內戰環境史研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深入挖掘:一是在研究空間上從陸地拓展到海洋。例如,為了維持土地的肥力,盡快恢復棉花生產,戰后美國在太平洋和大加勒比海地區鳥糞島發掘上表現出了極大的積極性。據統計,美國根據《鳥糞島法案》(Guano Islands Act)前后對全球66 個島嶼宣稱擁有主權,其中9 個島嶼至今擁有主權。⑤如貝克島(Baker Island)、中途島(Midway Island)和納弗沙島(Navassa Island)等島嶼。這些島嶼的開發不但滿足了南方種棉區復興的需要,也成為美國生態足跡進一步全球化的標志,為其日后控制太平洋政治提供了中轉地。盡管這一過程充滿著領土爭端問題,⑥石曉文:《“鳥糞熱”與美國新生態帝國主義的崛起》,《歷史教學》2021 年第6 期。但正是這種“新生態帝國主義”讓美國得以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了資源掠奪。二是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注意多學科交叉,如與城市史相結合。尼爾森(Megan Kate Nelson)就曾注意到“聯邦軍隊在1861—1865 年間的主要戰役主要集中在攻占和取得南部的城市中心”,⑦Megan Kate Nelson, Ruin Nation: Destruc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p.10.軍事指揮者為了清除敵方的一切潛在供給,“故意摧毀自己的城市,防止它落入敵人手中”。①Megan Kate Nelson, Ruin Nation: Destruc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pp.13-14.南方叛軍放火燒毀了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鎮,產生了戰爭中的第一個廢墟城市。南北雙方對物資資源控制之慎重由此可見一斑。因此,這種對內戰環境史中城市景觀與資源的分析也不失為一種新思路。
四、結語
美國南北戰爭是發生在北美大陸的最大規模戰爭,它不但對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美國大陸的土地景觀也產生了長久性影響,甚至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敘事。正如布萊恩·艾倫·德雷克(Brian A.Drake)所言:“內戰是美國環境史的一個分水嶺。”②Brian A.Drake,“The Watershed of War: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Big Civil War’,” in Mark Hersey and Ted Steinberg,eds., A Field on Fir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19,p.239.戰爭的廢墟改變了人們過往對自然荒野的認知,也讓史家重新思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生物能動性。環境史的視角讓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微小的生物有機體也會在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中發揮作用。受到后現代主義、后人類主義的影響,內戰環境史研究更加重視非人類因素的歷史作用,從而豐富了歷史書寫的可能途徑,也讓人們看清了內戰背后的人與生態之間的交織。但環境史家在堅持“自然作用于歷史”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從生態角度解釋戰爭、環境與人之間關系的評價尺度。通過發現戰爭普遍破壞性中的特殊性,并不是對戰爭環境毀滅的敘述的消解,而是還原人類活動與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的另一個方面。北美大陸的景觀不只是人或自然在某一方的單獨作用下產生的,而是諸多合力之下的雜糅,且內戰所造成的這種深刻影響,在通過長時段分析后才能更清晰地發現它的歷史遺產價值。
環境的分析方法不僅為傳統的內戰史敘事增添了一絲“綠色”,更讓我們重新思考戰爭的本質及其與存在的物質現實和自然之間的變動關系。南部邦聯和聯邦政府所需要的龐大軍隊加速了人類與自然及其他非人類生物之間的互動,戰爭在對自然進行毀滅性利用的同時也遭受到了生態環境的反噬,自然的能動性反過來又直接影響了這些部隊執行他們從軍事指揮官那里得到的指示的能力。從環境史維度建構新的內戰史,為人們了解內戰的起因、過程和結果增添了一系列的跨學科方法,特別是如生物學、地質學、氣象學、有機化學和流行病學等學科視角的引入,不但增強了歷史解釋力、深化了歷史解釋深度,而且有助于彌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對于近年來內戰史研究中的“黑暗轉向”③即突出內戰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荒涼感,淡化內戰產生的某些進步意義。參見Michael E.Woods,“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ivil War Era: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51,no.2,May,2017,pp.349-383.也是一種有效的反思途徑。隨著未來內戰環境史研究的深入,或許更有助于我們揭開美國民眾現代環境保護意識出現的另一個源頭,為認識更真實的美國提供又一個新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