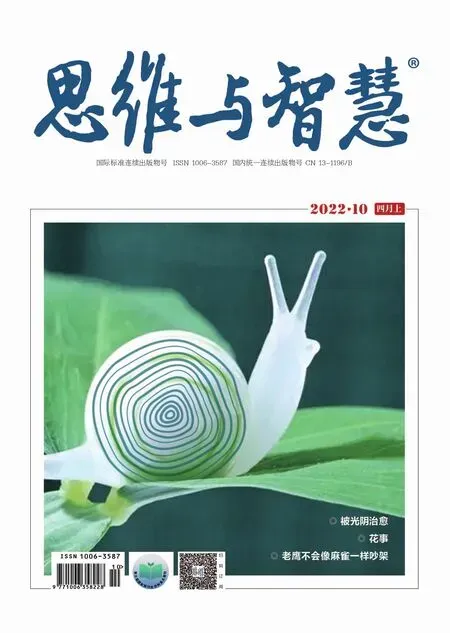花事
◎ 葉春雷

我以為這世間最浪漫的事,無過于秉燭賞花了。你看,蘇軾的那首《海棠》:
東風裊裊泛崇光,
香霧空蒙月轉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燒高燭照紅妝。
這首詩的詩眼,我覺得是那個“恐”字。這個字將詩人賞花時迫切的心情,寫得淋漓盡致。“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中國的文人,對生命的流逝,總有那么一點哀感。這哀感促使他們更自覺地去尋找身邊的美感,仿佛是,一天之中,找不到一點美的東西,這一天就虛度了。美,在某種程度上,是抵消生命哀感的一種有效方式。因為有美的存在,充實了生命,所以時間的流逝,也就不再顯得那么可怕了。這大約,就是蘇軾詩中的那個“恐”字,所傳達的真精神。
其實,古人這點生命的自覺,很可能是拜花之所賜。要不然,李白不會在那個浪漫的春夜,與眾兄弟一起,坐在桃李花叢中,秉燭賞花、飲宴了。在明晃晃的高燭照耀下,觥籌交錯的散亂人影,風中搖曳的裊裊花影,營造了多么神秘而詩意的一種氛圍。更不用說,那撲鼻而來的濃濃花香了。花之一生,是人之一生的一個縮影。對花的珍愛和欣賞,也就是對人生的珍愛和欣賞。要不然,活了一輩子,就像沒有活過。
李白對桃李花開的欣賞,帶有那樣一種轟轟烈烈的色彩,這源于李白張揚而顯得夸張的性格。夸張有時顯得虛張聲勢,但即使是虛張聲勢吧,卻帶有那么可愛的一種天真和執著,對生命的天真和執著。李白的一生,帶表演性,他就是喜歡被人看。被人看有什么不好,特別是,自己的人生,如此活色生香,恰若春夜盛放的桃李花。
春夜里盛放的桃李花,是李白人生的一個縮影。那般張揚,那般凌厲,那般富有氣場,那般先聲奪人。李白筆下的桃李花,因此像日本的櫻花一樣,有了一種暴烈的力道。這是生命的力道,在時間里刻下深深的刻痕。那些年輪一樣,刻在時間里的深深刻痕,成就了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人生傳奇。
相較于李白花事中遒勁的生命力的外溢,王維的花事中,傳達出的,卻是一種內斂的含蓄,一種消極的人生靜觀: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這首《辛夷塢》,與王維的生命氣質,真是太貼合了。張九齡罷相之后,朝政由李林甫把持,正直而怯懦的詩人再也看不到光明了,他的熱血開始變涼。然后是安史之亂,然后是被迫出任偽職,之后是撥亂反正,之后雖未遭清算,但畢竟人生有了污點,王維的熱血,徹底變冷。
《辛夷塢》展現的,就是這人生之“涼”。與李白的熱血僨張相反,王維的生命,也許一開始就帶點病態的色彩。這里有自憐,更有自戀。如果說李白筆下的桃李,其神韻近似日本暴烈的櫻花,暴烈地盛放,暴烈地凋零,那么王維筆下的芙蓉花,則近似西方那個美麗傳說中的水仙:一個自戀的男子的化身。
自然,王維筆下的木芙蓉,是一種林逋式的主動疏離,是一種保持靈魂自由的自覺。與李白張揚著生命活力的享樂主義人生觀不同,王維的人生觀更帶有一種禪悅的味道。自足、自立、自覺、自愈。我很欣賞這種心靈自愈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稀有的,是當代人最缺乏的。所以王維雖然有病態的色彩,但他的自愈能力,卻展現出生命宏闊的格局。
花事中的李白和王維,因此可以從人生導師的角度去理解:一個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是那樣熱情開朗,那樣野心勃勃,那樣生氣彌漫,隨時興趣盎然;一個是那樣內斂,從容,安靜,和諧,靈魂中長著厚厚的鎧甲,沒有什么能傷害到他,沒有什么能給他致命的打擊。人生靜與動的辯證法,在兩位詩人的花事中,看得很分明。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花是落了,但花魂是不會落的。花魂在哪兒?就在古人那些噴吐著花香的一首首詩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