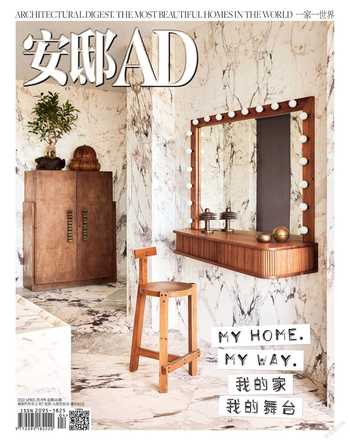缺陷之詩(shī)
陳桑雨

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家施勇,現(xiàn)工作、生活于上海。他是國(guó)內(nèi)首批從事觀念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工作室旁是一間協(xié)助藝術(shù)家完成大型作品制作的工廠,這讓他有了近水樓臺(tái)的便利條件。施勇身旁是一件裝置作品,他將“內(nèi)”字的筆畫(huà)拆解再重組,形成圍合結(jié)構(gòu)。

軟氈版上釘著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及布展的手稿。
藝術(shù)家施勇的工作室稍顯“擁擠”,手稿、模型、家具填滿了每一處角落。對(duì)比典型的藝術(shù)家工作室,這里的空間布置更近乎一間傳統(tǒng)的辦公室:書(shū)架整齊排列,其中妥帖安放著施勇在20世紀(jì)70~90年代購(gòu)入的書(shū)籍,涵蓋哲學(xué)、文學(xué),甚至漫畫(huà)。“買了那么多書(shū),我也不是全部看過(guò),但若干年后抽出一本,翻著翻著說(shuō)不定就來(lái)了靈感。”藝術(shù)家說(shuō),“哲學(xué)書(shū)的內(nèi)容可以說(shuō)讀起來(lái)常常一知半解,但讀起來(lái)能讓我莫名興奮——縱然一頭霧水,卻仿佛給了你全新的想象天地。”
這些老舊泛黃的各類書(shū)籍見(jiàn)證了施勇的觀念藝術(shù)啟蒙。“20世紀(jì)90年代初,‘85新潮美術(shù)運(yùn)動(dòng)平靜了下來(lái),一批新興藝術(shù)家想創(chuàng)作不同于前人的東西。我走近了觀念藝術(shù)的一支,讀德里達(dá)、福柯、羅蘭·巴特、海德格爾,欣賞德國(guó)藝術(shù)家博伊斯的創(chuàng)作……我們對(duì)視覺(jué)上的刺激已經(jīng)不太關(guān)心了,更關(guān)注與現(xiàn)實(shí)相關(guān)的話語(yǔ)表達(dá)。”在書(shū)架旁側(cè)的墻面上,一幅完成于 1991年的自畫(huà)像明確了施勇與架上創(chuàng)作的“訣別”。這幅具象繪畫(huà)從工作室里的一眾抽象作品中跳脫而出,在構(gòu)圖與色彩上有著契里柯的影子,一只纖細(xì)的手掌從底部揚(yáng)起。“你們看,我個(gè)人最滿意手的處理方法。”施勇玩笑道。自畫(huà)像完成后,他在畫(huà)框內(nèi)緣扎了一排鐵釘,標(biāo)志自己正式踏入觀念藝術(shù)的領(lǐng)地。

1.施勇工作室中的一幅自畫(huà)像從一眾抽象作品中跳脫而出。這幅完成于1991年的繪畫(huà)明確了他與架上創(chuàng)作的“訣別”。右側(cè)倚墻放著藝術(shù)家申凡的紙上油彩作品。

2.施勇于香格納畫(huà)廊個(gè)展“向內(nèi),直至消失”現(xiàn)場(chǎng)。空間中央的異形雕塑與展覽同名,投射出藝術(shù)家在后疫情時(shí)代的思考。后方墻上懸掛的裝置記錄了施勇抄寫(xiě)書(shū)籍的過(guò)程與結(jié)果。

3.展覽現(xiàn)場(chǎng),作品《內(nèi)向》是一件用熱軋鋼板制成的圓圈裝置,內(nèi)嵌的LED屏幕循環(huán)播放著48個(gè)宋體字的拆解與重組。
此后,在近30年的觀念藝術(shù)實(shí)踐中,他一直追求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實(shí)驗(yàn)性,突出表現(xiàn)關(guān)于文字、語(yǔ)詞、文本和觀念的思辨使用;他推崇簡(jiǎn)明的形式,而非繁冗;推崇內(nèi)容的可觸及性,而非無(wú)病呻吟。近年,施勇常常關(guān)注各種“缺陷”。在他看來(lái),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是全球化趨勢(shì)中的一個(gè)重大缺陷:“地球村”的概念暫時(shí)失效,基于這一觀察,施勇啟動(dòng)了創(chuàng)作:他將宋體字“全球化”的筆畫(huà)拆開(kāi)再進(jìn)行組合,形成圍合、封閉的圖像,作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狀況的提煉和隱喻。這件題為《內(nèi)向》的作品是關(guān)于圍合型字體在現(xiàn)場(chǎng)中的一次針對(duì)性呈現(xiàn):在香格納畫(huà)廊空間里,一個(gè)用熱軋鋼板鑄成的圓形裝置嵌套著場(chǎng)地中的承重柱,內(nèi)嵌的LED顯示屏上循環(huán)播放著48個(gè)宋體字的拆解與重組。巨大的異形雕塑《向內(nèi),直至消失》矗立于展廳中央:三個(gè)空心圓錐體在中心交匯于一個(gè)滅點(diǎn)。觀眾從任意圓錐體的末端向內(nèi)窺視,只見(jiàn)一團(tuán)漆黑;而站在多個(gè)圓錐體的盡頭,觀眾相互對(duì)話,雕塑的造型達(dá)成“傳聲筒”的效果,還擴(kuò)放出層層回音。這件與展覽同名的作品投射出施勇在后疫情時(shí)代的思考——圓錐體相交的滅點(diǎn)形若虛無(wú),卻扎實(shí)地存在——當(dāng)世界因疫情而區(qū)隔,人們只能邊摸索邊前行……
施勇透露,“跳躍式”的工作方法讓他有了喘息與調(diào)整的余地——施勇靈活切換藝術(shù)創(chuàng)作、畫(huà)廊工作與學(xué)校教職的場(chǎng)景。“有的藝術(shù)家可以‘打持久戰(zhàn),但我無(wú)法盯著某類作品就地打轉(zhuǎn);總是在一個(gè)地方打轉(zhuǎn)就可能被吞噬了。”為了打發(fā)時(shí)間,施勇開(kāi)始重讀工作室中的舊書(shū),并定下規(guī)則:通過(guò)抄寫(xiě)和擦除的方法進(jìn)行閱讀,以期化解焦慮。其中他抄寫(xiě)了《尤利西斯》的上卷,在速寫(xiě)本的同一張紙頁(yè)上,先用鉛筆抄寫(xiě),再用橡皮擦拭,工作不斷重復(fù),好似推石的西西弗斯。直至紙張破碎、剝落,施勇將殘片收集在玻璃罐子里,作為文字被記錄又抹去的“物證”。最終,抄寫(xiě)行為的過(guò)程與結(jié)果被打造成裝置《遺忘比記憶更久遠(yuǎn)——〈尤利西斯(上卷)〉》,并于個(gè)展中呈現(xiàn)。針對(duì)該系列作品的前綴名,施勇解釋道:“我不但沒(méi)能記住或理解書(shū)中內(nèi)容,機(jī)械的動(dòng)作反而加重了焦慮與不安……”目前,這項(xiàng)觀念創(chuàng)作還在繼續(xù),他也抄到了哲學(xué)家福柯關(guān)于藝術(shù)家馬格利特的“藝評(píng)”——《這不是一只煙斗》。抄寫(xiě)這本薄薄的小書(shū)時(shí),“可能是畫(huà)簿生產(chǎn)批次的緣故,紙張用起來(lái)特別不順手,鉛筆打滑、橡皮擦拭不凈,導(dǎo)致我的思路也‘打滑了。”雖然這本書(shū)不厚,但抄到后面施勇覺(jué)得“哲學(xué)家在自己的體系中層層推演,但站在藝術(shù)家馬格利特的角度,他創(chuàng)作時(shí)肯定不會(huì)考慮這些東西的。”
“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總是直覺(jué)性的,我也是這樣。首先有個(gè)大致構(gòu)思,隨后慢慢地深化、推進(jìn)。直覺(jué)能告訴我如何創(chuàng)作,但無(wú)法告訴我觀眾會(huì)如何解讀,可謂‘誠(chéng)惶誠(chéng)恐。”施勇頓了一下,繼續(xù)道,“藝術(shù)本身就有各種闡釋路徑,指引人們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一組書(shū)架從施勇以前的工作室搬來(lái),剛好嵌入一處內(nèi)凹空間。書(shū)架上擺滿了施勇在20世紀(jì)70~90年代購(gòu)入的書(shū)籍。書(shū)桌上擺放著作品模型與制作材料,后方墻上懸掛著施勇早年的觀念作品,是他在1994年夏季創(chuàng)作的《透明性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