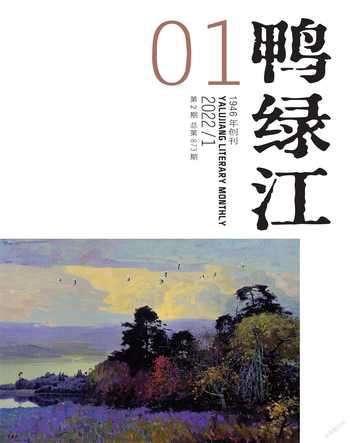阿婆
阿婆離開的時候,我還在宿舍里傻傻地等著阿婆康復。
老人住院后,抑制病情擴散的手段全用上了,起初醫院也下過病危通知,那晚,我連夜從北京輾轉回鄉,生怕見不到阿婆最后一面。
當我風塵仆仆地出現在阿婆病房外的時候,周遭是那么安靜,我以為自己來晚了,內心不由得一陣絞痛,眼淚止不住地往外冒。
該來的總會來的,我鼓起勇氣,踮著腳尖透過病房的小窗,匆匆朝里面瞥了一眼,母親正趴在床沿為阿婆活動手臂。阿婆還在!那一刻,我相信醫學是有奇跡的。
盡管已虛弱得口不能言,但阿婆還是很高興,嘴里不停地嘟囔著什么,多半還是問我什么時候畢業,要我好好上學、早點讓她抱上重孫之類的吧!畢竟每次見面阿婆都要問的。
阿婆離開的前一天,我還興沖沖地和阿婆通了視頻電話,趁著母親和舅母出去打飯的當口,我偷偷給阿婆看了妻子的照片。我向阿婆許愿,過年的時候一定要帶妻子回去看她。
那天,我接到父親匆匆打來的電話,母親在電話那頭已泣不成聲。我想再問點什么的時候,耳旁已傳來了嘟嘟的忙音。我的心忽地一下繃緊了,我突然意識到,在我的生命中,又有一個特別的、重要的人不見了。我不禁號啕大哭。
這不是阿婆第一次住院了,這也不是她第一次“回光返照”,但這似乎成了我內心醫學奇跡論的破滅日。一個對我來說頂頂重要的人,奇跡并沒有發生在她身上。
2007年,阿公的突然離世,一下子抽掉了阿婆的主心骨。平時精明強干的阿婆再沒有了往日的神采,身體康健的她第一次住院了。我們都嚇得不輕,真怕她跟著阿公一同去了另一個世界。
作為家里最大的閑人,我在阿婆的身邊陪伴了她近兩個月。八月底臨近開學,到了不得不離開阿婆的時候,我頭一遭向上天祈禱,祈禱我的阿婆能恢復健康。
許是老天爺被我的虔誠打動,外婆竟然逐漸恢復了健康。從那一刻到去世前,阿婆又陪伴了我們十年。時間一直在流逝,阿婆的世界卻沒有過多地改變:大中小學校的老師依舊被稱為先生,學堂之上還是大學堂……
每天醒來,阿婆總會讓母親和大姨將自己捯飭得干干凈凈,她還是那個爽氣的女主人。換我陪床的那幾天,阿婆大多數時間都不愿睜開眼睛。許是在強忍痛苦,許是對醫生在自己身上插管等行為表示不滿和厭棄。她從不希望別人特地來看她,她也不希望孩子們為了自己四處奔波,求醫問藥。阿公人生的最后時刻也如這般,整個人迅速消瘦下去,瘦骨嶙峋。生命艱難延續的背后,承載著太多不為人知的痛與苦。
阿婆要強了一輩子,無論何事都會給別人留下余地。人生的最后時刻,一生要強的她自然也希望體面地離去。
母親說,阿婆臨走前始終攥著我給她留下的一張照片,那是我和妻子在北京動物園的合影。外婆多次指了指照片上的我,比畫了一個既像是“V”又像是“2”的手勢,面帶微笑地離開了。
對于這個手勢,大姨有一番獨特的解讀。外婆曾和她說起,家里的孩子們只剩下我一個沒結婚的了。阿婆會把錢攢著,等我結婚的時候,她會給我大大的紅包。后來,大姨在整理遺物的時候,在阿婆的樟木箱子底層找到了一個大紅包,里面靜靜地躺著十九張一百元錢。
我好奇的是,為什么大姨那么肯定那個紅包是給我的。
“你知道的,你阿婆不會寫字的,那紅包的背面可是用阿拉伯數字寫著你的生日哩……”
生命的結局從一開始就是注定的,兒孫承歡膝下,阿婆定然度過了許多幸福的日子。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我們終將面對。也許阿婆在臨走前想過念出我的名字,提醒我不要忘記和她的約定,但她努力后發現,她已經無法掙扎著坐起,張開的喉腔始終發不出我姓名的音節。也許,她會在心里默念著我的名字,含笑離去,而我卻成了一個再沒有阿婆的孩子。
作者簡介:
封慰,江蘇泰興人,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碩士。曾于《中國考試》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作品散見于各大文學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