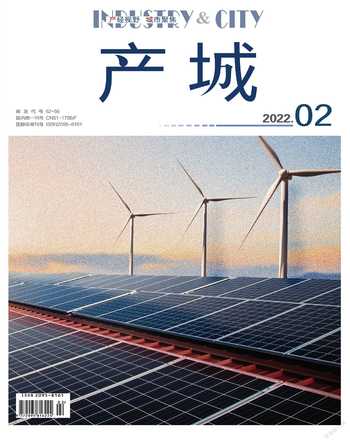“碳中和”對中國的戰略意義
第一,中國內部經濟轉型需要。
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重要過渡期,正在經歷從量增到質增的轉變,“既要金山銀山,也要青山綠水”。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都是以自身的廉價勞動力、環境破壞污染等為代價換取國際制造業產業鏈轉移,才成為“世界工廠”。現在,中國已完成資本積累與技術積累階段,下一步要求是整體工業體系升級,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層級中的位置,同時也祛除更多下游污染企業,重塑環境生態。
第二,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自成為“世界工廠”以來,中國也自然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為此飽受發達國家環保主義者詬病。2021年5月6日,美國智庫榮鼎咨詢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9年占全球的27%,超過發達國家的總和,遠超越排名第二的美國(11%)和排名第三的印度(6.6%)。
自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以來,在限制碳排放領域,雖然看似是發達國家群體因搶先自我設限,而并未給發展中國家設以明確減排目標,但實際上,以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越是優先控碳,留給發展中國家整體的碳排放份額就越小,相當于直接限制了這些國家(尚未開啟工業化進程或只是初級工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變相使得世界分工階層結構更加固化,讓發達國家永遠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性。所以,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積極參與“碳中和”行動,甚至以發達國家限碳標準要求自己,旨在參與新的國際規則制定,維護自身未來的發展權。
第三,中國能源轉型需要。
碳中和行動中歐洲幾乎是發達國家群體中積極性最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歐洲整體與中國的能源結構類似,都是貧油國,其石油天然氣資源高度依賴進口,所以亟需改變能源結構,早日擺脫對化石能源依賴。因此,歐盟對于新能源轉型的需求更甚于石油儲量豐沛的美國。這也是為什么歐洲對《巴黎氣候協定》極為執著而美國則搖擺不定。
中國在能源領域面臨的情境同歐洲十分類似,石油資源超過六成依賴進口,天然氣資源進口比例也不小,且相關物流通路的安全亦時有堪憂。中國自身的能源儲量和能源結構都以煤炭為主,而煤炭燃燒制造的二氧化碳污染又是碳中和的大敵。所以,中國亟需通過推進碳中和來重塑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核能以及光伏等新能源。
第四,“碳中和”帶動新領軍行業有望彎道超車。
碳中和將大量限制鐵路基建、鋼鐵、水泥、煤炭等傳統產業,同時催生新的產業,且中國有望在某些新領域彎道超車,獲得世界級的競爭機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產業就是新能源車。中國在傳統汽車領域一直總體落后于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但“碳中和”背景下的新能源車可能成為中國在新時代汽車領域“彎道超車”的典型案例。不過這一領域中歐將面臨新的競爭。據悉,歐洲正在成為全球電動汽車的先驅。根據麥肯錫管理咨詢公司最新發布的“電動汽車指數”,目前,歐洲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3%,略高于中國的41%,遠高于美國的10%。
第五,后美元時代的新貨幣錨?
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后,美元由于綁定黃金而一直扮演著國際貨幣的角色;“尼克松沖擊”之后,美元與OPEC綁定,從此憑借“石油美元”收取全球鑄幣稅。今時今日,自美國從阿富汗和中東逐漸撤出,世界迎來“后石油美元時代”,目前美國將美元與美債綁定,這顯然并非一個好的貨幣錨。
對于歐盟和中國來說,未來將歐元或人民幣推向國際化的基于窗口可能有兩個——“碳結算”與“數字主權貨幣”。現在看來,歐元很可能未來將錨定“碳結算”作為新的貨幣錨以推進歐元國際化;中國這方,數字人民幣已經施行,作為最大的碳排放國如果未來錨定“碳排放權國際結算”也是情理之中。
綜上,碳交易和碳國際結算可能成為未來歐元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貨幣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