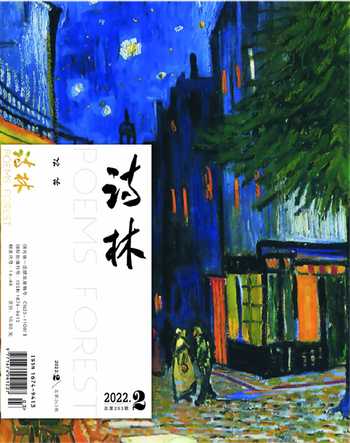陶易然的詩

把楊樹拼貼在枯萎的路邊
把汽車的尾氣拼貼在玻璃窗的岔路口
城市里最遙遠的定居是海浪
拼貼出蟄伏在沙土下的地毯
沒有玩具,沒有流著淚的書夾子
想獲得擁抱,像狗熊的窩
像毛衣粗糙的眼睛
貼在嬰兒失去羽毛的脊柱
基因工程、火箭彈、新法典
群居的路人閱讀日出的公告
每天都可以換一個棋盤
貼進叮當作響的黑色煤堆
開始拆解一只玩具
一個太陽需要一把鑰匙
在好的年成里,所有的收獲
都被月亮盯著。放一把火
在歲月的腰上燒
看瘋狂的孩子像春天跑向盛夏
一杯甜蜜的脂肪肝想要拆解
想要從零開始,從破殼的故鄉開始
拆解不是成年人的手和腳
不是堵在河溝里的紅色皮手套
也不是幸運彩票的白馬王子
只是路邊缺少花瓣的露水
缺少愛情的蛙鳴和豐滿的可組裝的
寂靜
點起蠟燭,童年在閃爍
鸚鵡的喉嚨擠出鋁網的銀
黑夜的翅膀飛向遠空
小溪的喉結高出塔身
搭建榆木的樓梯
氣管的迷途擁有一條手帕
讀著,白紙抱緊自己
回憶經卷、大樹、河流
唐詩的玉衣從魚腹傳來
美感流淌,捕捉女人的口器
月亮抵抗配音,把夜光杯摔碎
風在燃燒中蕩起秋千的蜂蜜
寒冷講話,墻親吻了光
你融化成為可觸碰的語言
樹葉給天空挖一個洞
挖出一個精致的墨點
手槍的管道發射陽光
雪山倒地,流出藍色的河流
一條排骨橫跨其上,螞蟻疾馳而過
老鼠需要一個洞
像風在油燈中點亮
覓食,吃掉的白骨慢慢堆積到天邊
往洞里灌水,紙張變滿變綠
倒掉熬煮的文字,在月亮之上
燙出一個洞
烏云一來,梅花就開
手拉手,搭著肩膀
手扶著腰,整理一下頭發
蒲公英的手,柔軟又輕盈
手是一面旗幟,把拉它上升的人
抱在流水的身體里
手推著車,拿口罩
手在尋找。另一只不潔的手
在嘴巴里。年輕的愛人
日與夜清澈的雙手,吹響
天上的木孔
在風中祈禱的綠手
無法合上。樹葉捧住陽光
親吻孩子的手,也親吻云朵
代替頭羊成為鈴鐺的手
搖搖晃晃,拍醒流水
一個詞
飛了起來,像小綠豆
落在碗里。是
沒有開出黃花的月亮
是潮汐,糾正海岸線的發音
自行車的臍帶運送甜蜜的銹跡
我們變成一個詞
落在紙上。游出筆尖的大海
沙粒表層的圖書館
更多的詞
小姑娘的白肚皮
轟隆隆響
詩者與論者,永遠是一對各自疏離而又彼此吸引的“緊張”關系。同時,論者的詩歌卻又決然不同于詩者的隨性寫作,會自覺納入到其詩學理論的譜系中,成為相互印證的獨特文本。
作為一名詩學研究者,陶易然的詩歌寫作似乎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抒情與敘事的兩大傳統,所謂的“日常”在其詩歌中也幾乎蹤影難覓。而抒情、敘事和日常性,這是目前詩歌界正在回歸和不斷踐行的熱詞,大量的事關庸常生活的“共情”寫作已經構成“大一統”審美的景觀。
陶易然的詩歌寫作在策略上“逆行”,直接扎根于詞語中。在時間的推演中,詞語恰恰是最可信賴的元基因,“詞語是微小的家宅”(加斯東·巴什拉),詞語是宿命的,但其變更與再生能力,使它全部參與到詩歌行動中。從詩歌的表面上看,他的寫作沒有地域,沒有現實、歷史或者時間的明顯標識,但是詞語本身所拆解和重構出了另一重現實,這個“新的現實”,或者說“發明的現實”,才是最真最可靠的此刻現實。
《拆解》一詩就是他代表性的一首。“開始拆解一只玩具/一個太陽需要一把鑰匙/在好的年成里,所有的收獲/都被月亮盯著”,“玩具”這個具體而又泛指的象征之物,對玩者有主體的塑造。在“玩”這個相互關照的動作中,兩者構成互文、互解的對應關系。“想要從零開始,從破殼的故鄉開始”,詩歌關注的原點是“故鄉”,故鄉無不是精神的原鄉。那個“瘋狂的孩子”造就童年的故鄉,也在重塑孩子自身,故鄉與童年,都處在生成中,也在拆解中,最終發現的是“可組裝的寂靜”。
陶易然就像一個對詞語反復探究、反復拆解樂此不疲的孩子,“與詞語獨處”的他在詩中若隱若現地布局了一個他者。他的視角并非主體的“我”,而是一個旁觀的第三人,拉開距離的審視,就像鏡中鏡,多維度的觀照才對得上這個同樣多層次復合的現實。
“樹葉給天空挖一個洞/挖出一個精致的墨點”,《洞》這首詩,起句就來個反思維,不是螞蟻們在挖洞,也不是樹在挖洞,而是樹葉朝著天空挖洞。這個“墨點”的暗物質,便具有了無限的意義。我們總是期望著狄蘭·托馬斯說的那樣,一首詩誕生了,世界就發生了某種變化。這個向上的“洞”和向下的“洞”,幽暗之處不可置疑地充當了我們挖掘、探究的詩學意義。“烏云一來,梅花就開”,我們奔向一個目標,但往往是奔向目標的反面。悖論,正是這個反諷主義時代的癥候。
——懷 金 詩人
陶易然這組詩作憑借修辭轉動之力,呈現出對閱讀解碼的隱藏以及一定程度的消解。正如前兩首詩題目所提煉出的逆向而行的命題,生命經驗被“拆解”,經“拼貼”“組裝”,即重組,進入修辭張力生成的超越日常經驗、物性、身體性的邏輯序列。詩人操控語詞,向讀者展開的經驗世界,如同隱匿圖塊的拼圖,打亂秩序的魔方。如果說其書寫是制造謎題的第一雙手,那么讀者調動語言感知力與自身經驗的閱讀甚至誤讀,便是解開謎題的第二雙手,是另一種整合、重組語言的力量。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中談及童年經驗與對世界的詩意理解間的關系時說道:“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中,誰不忘記自己的童年,他就是一個詩人。”《拼貼游戲》中的“游戲”“玩具”,《拆解》中的“玩具”“孩子”,《蠟燭》中的“童年”“手帕”,《洞》中的“洞”“老鼠”,《手》中的“孩子”,《響》中的“小綠豆”“小姑娘”等,被修辭分隔開的帶有某種童年印記的物象,似乎可以集束為光,在讀者閱讀視界交錯的繁枝間,推開一扇小窗,引入某種修辭干預下的童年視角,重組詩意的可能。“嬰兒的失去羽毛的脊柱”指向天使的失落,“無法合上”的“綠手”指向樹之祈禱的未完成,“藍色的河流”消解“雪山”,“月亮”“抵抗”“夜”,“沙粒表層的圖書館”抵抗借閱,“露水”“蛙鳴”的主體性存在被抽離。上述對物性及典型意義的消解,對抵抗的強化,去主體化的處理,恰恰生成了意義的離心力與修辭的向心力共同作用下的詩歌張力,成就了這組詩作“豐滿的可組裝的”詩意。
——納 蘭 青年評論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