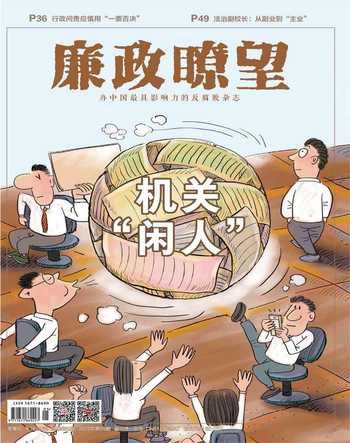向以鮮:呈現出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杜甫
曾勛
“千家注杜,萬家評杜”,對于杜甫這個我們十分熟悉的詩人,當下應該如何重構、重評?近日,四川大學教授、詩人向以鮮的新作《盛世的側影——杜甫評傳》出版,以詩解詩,讓讀者在賞析杜甫不朽“詩史”的同時,也可以從不同角度窺見一個獨特人物以及他所處時代的側影。
廉政瞭望?官察室專訪向以鮮,他向記者講述了寫作時的前前后后以及沒有在書中表達的想法。
您寫到杜甫入蜀后,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杜甫多次表達自己的寫作水平超過了西漢時期的成都文豪揚雄,又說自己的詩賦水平和另一名成都大文豪司馬相如相當,所以您認為,杜甫有一種抑揚雄而揚司馬相如的立場。在您看來,杜甫當時為何有這樣的心態?
:歷史上早有“揚馬”之稱,司馬相如是揚雄的前輩,揚雄的辭賦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司馬相如的影響。僅就文賦上的成就與貢獻而言,司馬相如顯然高于揚雄。唐代詩人中,最愛揚馬的就是李白和杜甫。李白說:“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杜甫也說:“悠然想揚馬,繼起名抃兀。”有意思的是,李杜二人對于揚馬的具體態度,又有著微妙的差異:李白認為自己的氣質和司馬相如更接近,常以相如自比,甚至認為自己少年時代就已經超越了這位前輩大師——“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夠狂了吧?
其實杜甫也很狂,他在《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一詩中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杜甫認為自己的賦寫得很好,好過了他的詩,好得可以和揚雄打個平手了。
李白杜甫兩人真有意思,各有各的偶像,都生出一種“滅掉”偶像的沖動。相比之下,杜甫的態度還是要稍微謹慎一些。杜甫后來到了成都,經過兩三年的營造,草堂已經像模像樣了,便寫下著名的《堂成》,尾聯是這樣寫的:“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顯然,杜甫還是很欣賞揚雄的。
杜甫雖然狂,還是要比李白謙遜一點,他喜歡揚雄,卻在詩文中“抑揚”,是不是表示我老杜其實是個謙虛的人,揚雄是比不上司馬相如,但我跟揚雄的文學水準差不多了,到揚雄這個級別已經夠意思了,有點“凡爾賽”的意思。
確實。杜甫的抑揚揚馬,并不是真的要貶低揚雄,而是一種個人風格上的選擇。為什么會舍馬而取揚呢?或許是因為杜甫覺得,在揚雄與司馬相如之間,自己的心靈與揚雄更接近一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后來認識了李白,杜甫覺得更不能把司馬相如掛在嘴邊了。這兒確實是有著杜甫自己的一份謙遜在。他知道李白那么喜歡司馬相如,李白又是大哥,總得禮讓幾分吧。
成都的遺跡很多,風景名勝也是數不勝數。這些與杜甫的詩歌美學兩者之間怎么樣相互影響的?
蜀中的山水和杜甫之前所經歷的山水既相連又完全不同,這種不同,讓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只屬于成都的杜甫。成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杜甫,杜甫也毫不吝嗇地贊美著成都,歌唱著成都——如同翠柳上的黃鸝,青天中的白鷺。因此,憑借杜甫的史詩之筆,我們看見了永不熄滅的“蜀人燈盞”西嶺雪山;看見了在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的對照中,魚兒在細雨里出沒,燕子在微風中快樂翻飛。
在成都,杜甫有了之前從未有過的心境來體察萬物,用杜甫的話說就是“細推物理”,詩人和成都的一山一水、一樹一石、一鳥一蟲之間達成了豐子愷所標舉的“同情”境界。我們現在游成都,看到夜晚的錦江,晴天看到西嶺雪山,春天看到草堂的花草,可能就會想到杜甫的詩句,這種歷史感和沉浸感,是無論花多少錢去做文宣廣告都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說,杜甫這名偉大的詩人,一千多年前就為成都代言,打免費廣告了。
杜甫來成都后,誕生了一種特殊的氣質“疏懶”。您在書中特意提到這種“疏懶”對杜甫詩學的影響,這樣的氣質恐怕也會影響杜甫的生活吧。
杜甫在別的地方從未找到過,只有到了成都后,詩人“疏懶”的神經才被喚醒。這種現象一定和成都平原及周圍山川的道家氣息緊密相關。杜甫本質上是一個典型的儒家詩人,他的人生取舍,他的詩歌風骨,均與儒家精神有著深刻的關聯。但是到了成都,或者說只有在成都的三四年間,杜甫顯示了由儒入道的氣象。
疏懶實際上是一種近乎隱居的狀態,一種有所選擇的放棄和沉迷。在這種接近于陶淵明的狀態中,杜甫很容易和峨眉老(東山隱者)這樣的人達成共識。唐代的峨眉山佛道共存,這個峨眉老就是一位來自峨眉的道士。

杜甫到底有多疏懶呢?最夸張的時候,他可以一個月不梳頭,似乎在刻意模仿像韓康那樣的隱士形跡。有時衣裳也懶得穿了,還給自己找了一個天真得可愛的借口:那些魚梁上的鸕鶿不是也很慵懶嗎,你看,它們舒展開寬大的翅膀,仿佛脫掉了衣裳,讓落日的光芒把每一根羽毛曬得又暖又亮。這種疏懶也必定和舒適的成都的文化與生活氣氛緊密相關。
在現代文學史上,不少詩人都寫過杜甫的傳記,人們說“千家注杜,萬家評杜”,您寫杜甫傳記時,對前輩寫的杜甫傳記有哪些取舍和突破?
確實,在整個寫作過程之中,承受著難以想象的壓力,這是我在寫作其他著述時從未有過的。在我的面前,橫亙著好多座大山,還有聞一多、劉文典、岑仲勉、汪靜之、李壽民、吉川幸次郎、宇文所安和葉嘉瑩等人的杜甫研究。其中有兩個人的杜甫研究較少被人注意:一個是湖畔詩人汪靜之的《李杜研究》,書中將李杜二人分置于“貴族”與“平民”兩個圈層來討論,開啟了后來郭沫若研究的基本范式;還有一個就是李壽民,他的另一個名字則更為人們所熟知,還珠樓主。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武俠小說名家李壽民的絕筆之作竟然是一冊七萬字的小說《杜甫傳》。1960年春天,躺在病床上的李壽民口述,由其秘書侯增作筆錄,斷斷續續歷時一年始完成初稿。
在大師林立的杜甫研究面前,我還得硬著頭皮寫下去,慢慢地,總算找到了一點兒自信心。隨著寫作的不斷深入,這種自信心越來越強烈,以至于讓我產生了幾分傲視的幻覺。回過頭來看,這些前輩大師的學問當然比我好,但不一定有我這么喜歡杜甫;就算有我這樣喜歡,他們也沒有我這樣幸運,因為我能站在他們的肩頭之上,我能從他們的杜甫研究中汲取精華和能量,從而淬煉出屬于我的杜甫之血與火。
至于說有什么突破,這個很難說。我想要給世人呈現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杜甫,我想要呈現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杜甫,而不是被格式化或標簽化的杜甫。不過,是否達成了這個目標,我說了不算,得讓讀者、讓時間來說話。
杜甫留給成都和四川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我們今天如何傳承這種人文精神?
愛。愛萬物,愛蒼生,愛人民,愛生命,愛一切可愛之物,杜甫正是這樣一個深愛著人間的詩人!我們要傳承的,要弘揚的,就是詩人發自內心深處的愛,同情與悲憫之心。
杜甫的苦難,很多時候并非來自個人生活的際遇之苦與難,而是一種士大夫的責任性苦難,源于深沉之愛的苦難。宋人黃庭堅在《老杜浣花溪圖引》一詩中寫道:“中原未得平安報,醉里眉攢萬國愁。”杜甫的憂愁和苦難,主要不是來自自身,而是來自中原和萬國。郭沫若在為成都杜甫草堂題寫的那副楹聯寫得好:“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這樣的大悲詩人,這樣的愛的精神,值得我們世世代代歌頌、薪傳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