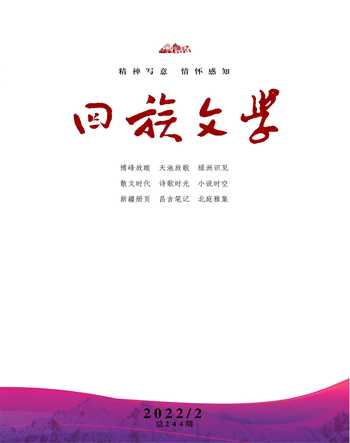詩歌創作中的感受力與想象力
周維強
詩人顧城在《學詩筆記(二)》一文中,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什么是詩?是什么樣特點使詩和其他藝術形式相區別?我想至少有兩個必須具備的因素:一個是美的感覺;一個是精煉的語言。只有美好的感覺和精煉的語言相結合時,詩才能出現。”“美的感覺”,我的理解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詩歌創作中的“感受力”。有主動的,也有被動的。主動地去發現詩意的因子和客觀規律,被動地承受來自外界的與心靈相契合的美妙感覺。只要能夠激發靈感,讓心動的感覺涌遍全身,詩意匯聚在腦海,“感覺越美,語言越精,二者結合得越和諧(矛盾,不平衡也能構成一種和諧),詩則越成為詩”。顧城甚至斷言:詩人,就是為美感和精煉的語言舉行婚禮的人。
感受力是原創力也是心靈萌動時的初始感覺。在詩歌創作中,擁有了感受力,才能有底氣駕馭那些經過篩選的字詞,才能讓字詞與心靈激蕩,繼而迸發出詩的豪情。“感受力”一詞,聽起來很玄,但是應用到詩歌創作中,卻是很常規的寫作技藝,它不僅折射了一個詩人處理文字的方式,用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的話說,還包括“對格律、節奏和文字肌理的把握”,“定義他對生命的態度”,“他對他自己的現實的態度”。對于一個有志于把詩歌創作作為終身事業的詩人來說,培養和發現自己的感受力,異常重要。絕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寫詩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寫著寫著,話說多了,美學的經驗就產生了,這個時候,美學經驗的加持,就會讓寫作者去尋找屬于自己獨特的聲音,獨特的感受,用詩人黃燦然的話說,“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聲音去表達你自己的感受”。
感受力有時候會存儲在少年時異稟的天賦中;有時候,人到暮年,依然心有所感,寫出令人拍手叫絕的好詩。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只要是心內流淌的自然的情感,有悲天憫人之情,有憐人愛人之意,有和萬物共融的悲戚之懷,都是感受力生發的源頭。我在微信公眾號上曾讀過一首《雪地上的羊》:“奶奶家大門口的雪地上/總是拴著一只羊/每天/我都跑去喂它些菜葉/有時它突然胖了/有時它突然瘦了/有時它突然高了/有時它突然矮了/有時它突然大了/有時它突然小了/其實它并不是同一只羊/只是我把它當成同一只羊來喂/而且我盡量不去看旁邊那個肉鋪/以減少內心的悲傷”。如果光看詩題,并無亮眼的字詞,甚至在詩歌的前半部分都沒能讀到讓人眼前一亮的詩句。好詩在結尾,最后三行畫龍點睛的詩句,讓我的內心充溢著感同身受的“內心的悲傷”。如果說“雪地上的羊”是一個美的感覺,那么這首詩的最后三行就是詩人悲憫的感受力的折射。如果我說,這首詩的作者只有11歲,你是不是會感到詫異呢?詩歌的作者叫姜馨賀,寫出這首詩時只有11歲,還是一個正在學校讀書的小學生。
我們再來讀這首《看云》:“船在河上行走/桅檣上/云在曬著衣裳//我在船頭看云/請問為何一動不動/云冷冷答曰:你不是也沒有動嗎?/蠢/我端起酒杯一飲而盡”。以擬人化的口吻,讓“云”和詩人產生了心靈上的美學互動,全詩讀完,頗有寒山拾得的偈語之境,動在靜中,靜在動處,又似乎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四句相唱和,寫出了那份空靈與空寂。詩歌的作者寫出這首詩時已經79歲,他就是被詩歌界譽為“詩魔”的洛夫。
那么感受力能否通過訓練和練習獲取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實,一首詩的誕生過程包含著思考和寫作兩個步驟。思考的過程可長可短,寫作的過程就很簡單,有時候一氣呵成,只需要三五分鐘就能夠寫出一首詩。思考的過程,是尋找詩歌感覺的過程,是讓感受力萌發產生詩思,從而讓意象通過語言呈現出文字美感的過程。從心理學上來講,感覺一般是指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時,人對事物個別屬性的反映。就詩歌的感受力來說,它是詩人對于藝術特性和詩歌特性的感性把握。
如何獲取感受力,我想那些長期從事詩歌創作的人,自有他們的密徑和方法。就我個人而言,獲取感受力一般有三個途徑:一是大量的閱讀。詩歌是文學皇冠上的明珠,創作詩歌注定要比其他題材更具有挑戰性,也更凝聚著創作者的深度思考和藝術探尋。詩人的閱讀應該更廣博也更駁雜。通過大量的閱讀,讓身心與詩歌保持一份靈與肉共融的感覺,達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境界。通過大量的閱讀,在詩歌創作過程中才能夠對分行時的情感、韻律和節奏有著真切的感覺。我向來主張詩人的閱讀應該是以開闊視野為前提的廣博涉獵,而不僅僅囿于詩歌類或者理論類的書籍。信息時代,我們擁有了各種可供閱讀的平臺和機會,而不再是過去單一的紙質媒介。甚至紙質媒介在經受著短視頻、音頻和電子信息平臺的沖擊下,被逼退至信息邊緣的窘境。詩歌類更是如此。這個時候,如何在信息遮蔽的時代篩選有效信息,且在良莠不齊的亂象中求真取舍,既考驗閱讀者的知識深度和廣度,又考驗閱讀者哲學思辨的寬度和概括力。詩歌的感受力來自于一種深扎泥土的根部營養吸收式的閱讀。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從古詩詞中尋找意境和感覺,又要從外國詩歌中感受現代詩學的經驗與思考方式。尤其是國外翻譯類的作品,讀者之間經常引發爭議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現代詩歌翻譯良莠不齊的版本,對此詩人木葉認為:“真正的好詩,經得起各種翻譯,詩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東西,無論怎么打碎,無論誤譯還是漏譯,最后詩的精魂仍在。”而古詩詞是老祖宗留下來的瑰寶,只要用心去品去悟,是能夠一次次尋找到美感的存在的。二是多欣賞和詩歌有著藝術連體感覺的影視、繪畫、音樂作品。蘇軾評價唐代詩人王維的創作:“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可見,藝術的形式是相通的。詩和畫如此,詩和音樂和影視和雕刻等等,更是如此。通過反復欣賞音樂作品、影視作品,就能夠激發形象思維和想象思維,繼而培養更為豐富更為美好的藝術感覺。三是用心去悟,回歸生活的疼痛處,感受生活的真善美,讓心靈濡染悲憫的氣息。所謂憤怒出詩人,同情出詩人,說到底,是生活給予詩人以重擔,讓詩人承擔起這份寫作的責任。那就是葆有對底層人民苦難的同情,對罪惡和不公鞭撻和痛斥,對美好與純凈給予贊美和歌頌。詩歌藝術的感覺,就來自這一次次自我的修行和凈化,來自于對心靈澄澈度的追逐和追求。像我們所熟知的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愛爾蘭詩人葉芝的《當你老了》、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側》等,盡管詩人寫作這些詩歌時,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處在困苦之中,但心中涌動的那份真情,那份對普世價值傳遞的愛和悲憫,依舊讓他們展望著生活的美好,繼而寫出交織著大愛與疼痛且讓人流淚的詩句。
感受力像一把鑰匙,只要能夠握住這把鑰匙,就能夠讓自己的內心變得平靜,繼而在茫茫詞海中尋找到那些震顫人心的字詞。我始終認為,詩人的敏銳感覺是柔軟的,是發現常人所不能發現的現象和片斷,是一種“凝視”。美國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對“凝視”有著詩意的詮釋:“寫詩的人會反復凝視一樣東西,他愿意耐心地去凝視一樣事物,凝視一個人,凝視一面風景,甚至凝視小小的甲蟲和蒼蠅,凝視它的生,凝視它的死。這樣的凝視狀態,對年輕寫作者應該很有啟發性。”我經常聽到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的作品進行批評時,會用上“感受力下降”這樣的批語,其實所謂的感受力下降,就是“凝視”的能量在下降,參透生死的境界在下降。詩人應該是看透生死的,應該是在生與死的天平上傳遞著能量守恒信息的人。他們似乎擁有了一種天賦,那就是能夠在自由思考的境界里,感知著生命的律動與平衡。顧城甚至說,詩的領域,像世界一樣廣大,像生命一樣奇異多彩,并不是一兩個術語所能概括的,它將超越一切既定的界限。
而想象力是感受力的一種延伸。詩歌創作中的想象,是催化劑更是助推劑。當一個人的人生經驗和生命體驗通過語言的形式轉化為詩歌時,想象力的作用,更像是讓字詞擁有了活性與活力。想象力是內在的動力。如同音樂的旋律,繪畫的色彩以及雕塑中的線條一樣重要。通過想象的融合,一切生命的體驗、文化的精髓和歷史的思考,都能夠在字詞中尋找到回歸的理由。詩歌作為一種藝術,一種文學形式,一種美學經驗的審美原則,想象力不僅不可或缺,而且,有著非同一般的穿透力和體驗感。
洛夫有一首詩,詩題為《信》,詩歌內容如下:“昨天收到一封信/打開信封發現只有一撮灰/撥開灰燼看到一張臉/果然是你,只有你/深知我很喜歡焚過的溫柔/以及鎖在石頭里的東西”。這首六行短詩,將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將“一撮灰”比喻成“焚過的溫柔”,以及對生命的透視,感知“鎖在石頭里的東西”,讀之心頭為之一顫。由“信”聯想到“一撮灰”和“一張臉”,再聯想到情感中的“溫柔”和“石頭”,兩相對比,讓“信”所包藏的信息量呈現出巨大的情感反差和生命觀感。
詩人余光中說,藝術創造有三個條件:要有知識;要有經驗;要有活潑的想象。所謂想象就是廣泛的同情,就是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余光中是從詩人的情感世界,從內心世界的本源出發。讓想象具有同情心,就能夠心有所想,情有所系,從而回歸到中國古典哲學的“心學”范疇。他接著又舉了一個例子,說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有一篇很長的論文,叫《詩辯》,就是為詩辯論。論文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科學綜萬物之意,而詩綜萬物之通”,科學要分門別類,要分析,而文學和藝術要綜合,要把不同的東西用想象力貫穿起來。可見,不論是在西方的詩學體系還是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想象力都是一條主線,唯有想象力,能像金色的絲線一樣,把詞語的珠子串聯在一起,繼而產生詩歌華美的光芒。
那么想象力是不是不需要知識儲備,只需要胡思亂想,讓思緒天馬行空地奔馳起來,而不加約束地任意思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理解的詩歌創作中的想象力,是從詩歌的靈感出發,當腦海中勾勒出一個“意象”,那么情感、語言,都在為“意象”的勃發做著準備,然后讓意象在想象力的推動下產生合情合理的聯想,宇宙萬物,包羅萬象,奇思妙想,異彩紛呈。在這里,詩歌的想象力,是個人情感的潛意識表達,是能夠讓字詞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立體到空間的一個組合過程。它能夠讓兩種毫不相干的事物產生關聯,在詞語爆破力組合的形式下產生美感,從而讓視覺、嗅覺等相互融合,融會貫通。
舉詩歌為例。張二棍的詩歌《故鄉》,只有十一行:“我說,我們一直溫習的這個詞,/是反季節的荊棘。你信了,你說,/離得最遠,就帶來最尖銳的疼/我說,試著把這個詞一筆一畫拆開/再重組一下,就是山西,就是代縣,/就是西段景村,就是滹沱河/你點了點頭,又拼命搖起來,搖得淚流滿面/你真的蘸了一點點啤酒,在這個小飯館/一遍遍,拆著,組著/一整個下午,我們把一張酒桌/涂抹得像一個進不去的迷宮”。這里的“我”是指代詩人自己,那么“你”指代誰呢,有可能是“我”的親人、朋友,也有可能是詩人自己,詩人在自說自話。這些都不重要,在“故鄉”兩個字面前,應該說,詩人都有著與生俱來的“還鄉”夙愿。海德格爾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張二棍沒有把這個古今中外的詩人寫得爛俗的意象,寫得更加爛俗,而是另辟蹊徑,讓想象力貼著意象起飛。離鄉,是“最尖銳的疼”,而思鄉,就是把“故鄉”這個詞“一筆一畫拆開/再重組一下”,就是“把一張酒桌/涂抹得像一個進不去的迷宮”,迷宮里有著離鄉的孤獨,有著思鄉的哀怨,有著一個游子對山西代縣西段景村滹沱河的深情回憶。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對于故鄉情感的復雜性感受。是詩人人生經驗和生命體驗的真實體現。在這首詩中,“故鄉”這個意象,有了鮮明的張二棍印記,他的想象力,是從生活的現實出發,讓虛與實、個人體驗和故鄉畫面交融在一起。于是,讀這首十一行的詩,我們并沒有疏離感,反而有著異常的親切。這種共同的生命體驗,很容易和讀者拉近距離。張二棍的故鄉,也有可能是絕大多數人的故鄉,而詩人的疼痛,也有可能是絕大多數人離鄉的疼痛。想象力在這首詩中,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同情心的體現,是一種樸素而美好的生命感覺。
當然,有的時候,詩人為了追求詩歌語言的陌生化,追求詩歌思考的新意,會讓想象力加速,運用各種寫作技巧和夸張的手法,讓想象力發揮作用。這個時候,我們在詞語上感受到的就是一種新奇,一種夸張,一種色彩斑斕的畫卷的美感。比如楊煉的《諾日朗》、昌耀的《劃呀,劃呀,父親們!——獻給新時期的船夫》等,而西部詩人中,對于想象力的運用,就更為廣泛。由于地域的特殊性,面對著荒灘、戈壁、巖畫和沙漠,強烈的視覺沖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的車隊、戰馬、古國和駝鈴。所以我在讀西部詩人的詩歌時,會情不自禁地誦讀起來。就是因為這個視覺沖擊力太過強大,讓詩人的想象力碰撞到了讀者的想象力。
比如葉舟的《懷想》:“那時候 月亮還樸素 像一塊/古老的銀子 不吭不響 靜待黃昏//那時候的野獸 還有牙齒 微小的/暴力 只用于守住疆土 豐衣足食//那時候 天空麇集了鳳凰和鯤鵬/讓書生們淚流不止 寫光了世上的紙//那時候的大地 只長一種香草/名曰君子 有的人入史 有的凋零//那時候 鐵馬秋風 河西一帶的/炊煙飽滿 仿如一匹廣闊的絲綢//那時候的漢家宮闕 少年劉徹/白衣勝雪 剛剛打開了一卷羊皮地圖//那時候 黃河安瀾 卻也白發三千/一匹伺伏的鯨魚 用脊梁拱起了祁連//那時候還有關公與秦瓊 亦有忠義/和然諾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跡//那時候 沒有磨石 刀子一直閃光/拳頭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馬//那時候的路不長 足夠走完一生/誰摸見了地平線 誰就在春天稱王”。正如詩題一樣,既是“懷想”,又是想象力策馬奔騰的體現。而亞楠的詩歌《巴音阿門》,雖然感情沉郁且敘述平緩,但是想象力依然有著詩人的自由與奔放:“從一座巖石上看到的/舊時光/和遙遠的馬蹄聲//就仿佛/看到一群馬延伸的畫面/在靜謐中。還會//看到塵土/白色雪峰環繞的土爾扈特/那些兒女們//從遠處歸來/草原盛大的場景,溪水還在/靜靜流淌//在每個草尖上停留/綠色山脊/和一群群陌生的牛羊//都沿著記憶漫游/很顯然,風/已經把多余的聲音//清除掉。只不過當鴻雁飛過/有人眼中就會噙滿/淚水”。相同的是,詩人葉舟和亞楠都把意象落在了西部常見的事物上,讓詩歌的想象依然有著現實的觀照和遵循。
感受力讓詩人保持著對這個世界童真般的體驗,而想象力讓詩人躍出自己的思維局限,開始延展自己的情緒和情感。其實,驗證一首詩的成色與底蘊,從語言上感受其境界,從內里感受其思想。品讀一首詩是否是好詩或者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其思想性和藝術性依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感受力襯托著思想性的嵌入,想象力則提升藝術性的品質。不論是初學者還是寫了多年的詩人,對詩歌保持敏銳的嗅覺,讓感受力不斷提升且不易消失,讓想象力秉持著孩子般的童心與純粹,這樣寫詩時才能夠讓字詞引出顫抖的聲音。有的時候,讀者讀詩,就是讀一種感覺,就是在感覺中靠近詩人的詩思,感受其內心的純凈,體悟其思想的深刻。而詩人那份對語言的忠誠,對詩歌的崇敬,通過感受力和想象力表現出來,就有了其他文體不具備的詩意與悠然。詩歌是文學皇冠上的明珠,詩人是打磨明珠的匠人或藝人,寫詩,就是在和心靈對話,就是讓修行的心靈得到安放,融為自然的幻境,繼而產生一種恒久,一種幸福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