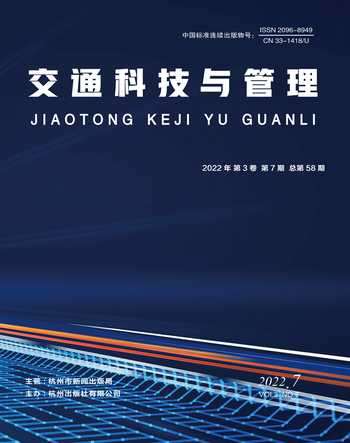卵石地層地鐵盾構隧道下穿河流段影響因素分析
陳龍





摘要 卵石地層地鐵盾構隧道下穿河流段易受到水力作用而產生復雜的圍巖應力場。以北京地鐵房山線北延工程1標段樊羊路—四環路區間盾構隧道下穿馬草河為工程背景,采用控制單一變量的手段,抽象簡化采用FLAC3D建立有限差分模型,對不同隧道埋深及水頭高度下的水土耦合進行數值計算。研究結果表明:地層整體豎向位移隨隧道埋深增大而增大,但對于水平位移影響較小;不同水頭高度時,地層豎向位移和水平位移與水頭高度呈正相關,并且隨水頭高度增大,盾構開挖影響范圍也隨之增大。
關鍵詞 卵石地層;盾構隧道;下穿河流;埋深;水頭高度;數值模擬
中圖分類號 U455.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8949(2022)07-0085-03
0 引言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口的大量聚集,城市地面交通發展空間受限,地下軌道交通發展如火如荼,許多研究人員對盾構地鐵修建進行了研究[1-3],攻克了諸多建設難題。閆莉等[4]以青島地鐵某隧道下穿河段工程為依托,提出了包含超前深孔注漿、地面復合錨桿樁及洞內小導管補償注漿等多種注漿加固措施的聯合控制方案。梁孝等[5]以杭州地鐵5號線盾構施工工程為背景,通過模糊綜合評價和BP(Back Propagation)神經網絡方法進行風險評價分析。沙原亭[6]結合某在建地鐵土壓平衡式盾構下穿河流及穿越橋梁樁基工程,總結出一套關于土壓平衡式盾構下穿河流及穿越樁基的施工技術。
綜上可知,目前盾構隧道下穿河流段研究仍然缺乏,特別在對于卵石地層等易受到水力侵蝕的地質環境中。因此該文以北京地鐵房山線北延工程1標段樊羊路—四環路區間盾構隧道下穿馬草河為工程背景,采用控制單一變量的手段,抽象簡化實際工程采用FLAC3D建立有限差分模型,對不同隧道埋深及水頭高度下的水土耦合進行數值計算,以期為類似工程提供借鑒。
1 工程概況
北京地鐵房山線北延工程1標段樊羊路—四環路區間出樊羊路站后,沿六圈路東行下穿Φ500燃氣管線及白盆窯住宅地塊至六圈路與規劃張新路交叉口,左右線分別以450 m、460 m半徑下穿馬草河后轉彎向北延伸,下穿采砂坑后以R=500 m半徑再次下穿馬草河,沿規劃張新路向北至四環路南側接入四環路站,在四環路站盾構吊出。區間在六圈路與規劃張新路路口側穿白盆窯規劃地塊東南角綠化部分,在馬草河東岸側穿空軍計量總站及巴莊子村部分民房(最小水平距離為1.93 m)。沿線地下管線有2.0×2.3 m暗挖單孔電力隧道(最小豎向距離為9 m)和DN2200在建上水管(最小豎向距離約9.77 m)。
區間隧道兩次下穿馬草河,分別于里程SK25+556.0~SK25+633.5、XK25+550.0~XK25+637.0范圍下穿馬草河,區間與馬草河豎向最小凈距約為15.42 m。區間下穿馬草河風險等級為一級。于里程SK26+243.1~SK26+426.8、XK26+215.4~XK26+365.9范圍下穿馬草河,區間與馬草河豎向最小凈距約為10.42 m。區間下穿馬草河風險等級為一級。隧道基本位于卵石6層,局部位于卵石5層,地下水位位于隧道底板以下5~15 m。隧道內各圍巖均勻性和穩定性較好。
2 水土耦合數值模型建立
2.1 模型建立
根據工程實際條件簡化及拉格朗日連續介質法,基于FLAC3D軟件,為了減小邊界條件約束帶來的模擬結果誤差,模型長度取隧道外徑的3~5倍,模型高度取隧道埋深的2~3倍。模型長×寬×高為60 m×60 m×42 m,如圖1所示。為了保證模擬流固耦合下隧道開挖的準確性,在模型前后左右及下邊界設置位移約束,并將模型的左右及下邊界設置不透水邊界。孔隙水壓力為靜水壓力且水壓力隨著深度變化而呈梯度變化,施工掌子面設置成透水邊界,管片內側設置零水壓力邊界,土體含水量為飽和含水量。
根據工程地質勘查資料,模型地層參數選取均與實際工程資料一致,地層土體采用理想彈塑性的3D實體單元來模擬,滿足 mohr-Coulo mb屈服準則。盾構隧道管片、盾殼、注漿體均視為彈性材料,盾殼及管片采用shell單元進行模擬,等代層采用3D實體單元進行模擬。管片厚度為0.35 m,采用C50混凝土,盾殼的單元剛度由鋼材的彈性模量及泊松比計算得出,厚度為20 cm。等代層厚度為20 cm。
模擬盾構開挖時,首先建立初始應力場及初始水壓力場,并將初始位移清零,然后將隧道按實際開挖的每段掘進長度將隧道部分劃分為同等長度。假設已開挖至第n步,首先,n階段的殺死土體單元,激活n階段的盾殼和土倉壓力,同步激活上一階段的管片襯砌,此外n-2階段的注漿壓力及等代層,盾構模擬過程如圖2所示。通過以上闡述的模型中操作以達到實際工程中的盾構開挖的效果。同時,重點研究地鐵盾構開挖從開始進入到盾構完成這個過程中,土體內孔隙水壓力的變化情況和地層位移情況,并對支護管片的變形及受力情況進行監測,從而保證盾構開挖過程的安全。
為明確考慮滲流作用下,在單一變量改變時,盾構開挖過程中地層變形規律及支護管片受力情況,設置測點位置如圖3所示,以模型盾構開挖方向20 m斷面為監測斷面,水平方向每2 m布置一個測點,共布置29個測點,以監測地表最終豎向沉降和水平位移;在同樣斷面隧道拱頂上方及拱底下方0.1 m處設置豎向位移測點,以監測拱頂及拱底隧道施工過程中位移沉降規律。
2.2 計算工況
根據實際工程中隧道上方覆土厚度和水頭高度,選擇隧道埋深15 m、20 m、25 m、30 m,水深2 m、4 m、6 m、8 m進行對比分析研究。具體研究工況組合如表1所示。在考慮水的作用時,對于水壓的模擬,采用有效應力法,例如河流水深2 m,其在模型上表面的孔隙壓為2×104 Pa,應力邊界為2×104 Pa。
3 關鍵影響因素分析
3.1 不同覆土厚度下盾構下穿地層位移分析
為更好地監測盾構開挖過程中地表沉降情況,在地表以中軸線為基準,盾構方向20 m處,每隔2 m布置一個地表沉降監測點,繪制出y方向20 m斷面處地表沉降值變化曲線(如圖4)。由圖4可以發現,隧道在開挖結束后,地表測線沉降整體呈“V”形分布,地表最大沉降出現在隧道拱頂上方,四種工況地表最大沉降值分別為6.78 mm、7.71 mm、8.78 mm和10.01 mm。離隧道中軸線越遠,地表沉降值也越小。此外,由圖4可知,隨著隧道埋深增大,水平方向上影響范圍也相應增大。受影響較大區域測點繪制出的曲線基本符合拋物線y=ax2,當隧道埋深為15 m時,距隧道中軸線為12 m處的地表沉降速率開始減小,基本開始穩定,沉降值為3.99 mm,a=0.03。當隧道埋深為20 m時,地表沉降速率在距隧道中軸線20 m處開始減小,并與20 m的測點沉降基本相同,最終沉降值為5.66 mm,a=0.02。而隧道埋深為25 m時,在據隧道中軸線26 m處向左右兩邊測點沉降值趨于穩定為7.18 mm,a=0.02。而隧道埋深為30 m時,距隧道中軸線28 m處的測點沉降值不再發生較大變化,最終沉降值為8.69 mm,a=0.01。由此可知,在卵石地層中,隨著隧道埋深增大,盾構開挖過程對于地表影響范圍也在增大,影響范圍增長速率在逐漸放緩。
3.2 不同水頭高度下盾構下穿地層位移分析
圖5為模型y方向20 m處,以距隧道中軸線水平方向測點地表沉降值繪制的單一斷面地表最終沉降規律對比圖。由圖5可知,地表沉降位移沿隧道中軸線對稱,并呈“V”形分布,并且四種工況的地表沉降發展趨勢基本相同。地表沉降峰值出現在隧道中心線上方,并且距離隧道越遠的地表沉降越小。此外,隨著水頭壓力的不斷增大,盡管遠離隧道中心線的地表各測點位移不再改變,但仍存在著一定的均勻沉降,并且盾構開挖影響范圍和沉降量也逐漸增大,2 m水頭高度地表沉降量為8.19 mm,4 m水頭高度地表沉降量為8.78 mm,6 m水頭高度地表沉降量為9.92 mm,8 m水頭高度地表沉降量為10.19 mm,分別增大了7.18%、13.00%和2.79%,即地表沉降量增加了0.59 mm、1.14 mm和0.28 mm。
4 結論
為了研究卵石地層盾構下穿河流段對于地層的影響規律,該文采用控制單一變量的手段,以實際工程地層及河流水深變化為參照,采用FLAC3D建立有限差分模型,進行了不同隧道埋深(15 m、20 m、25 m和30 m)及水頭高度(2 m、4 m、6 m和8 m)下的水土耦合數值計算,共計完成了8組數值試驗。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隧道上方不同覆土厚度影響因素方面:隨著隧道埋深增大,地表響應范圍相應增大,影響范圍增長速率有所減小,地層整體豎向位移隨之增大,但對于水平位移影響較小。
(2)不同水頭高度影響因素方面:地層豎向位移和水平位移與水頭高度呈正相關,并且隨水頭高度增大,盾構開挖影響范圍也隨之增大。單一斷面處,地表豎向位移曲線以隧道中軸線水平對稱,呈“V”分布。此外,水頭高度增大,地表沉降量增長速率也有所增大。
參考文獻
[1]孫燁, 劉明高, 陸平, 等. 盾構隧道橫向聯絡通道建設關鍵技術問題綜述[J]. 現代隧道技術, 2021(S1): 293-302.
[2]舒恒, 彭雨楊, 宋明, 等. 超大直徑盾構隧道穿越巖溶發育區地表注漿合理加固范圍[J]. 科學技術與工程, 2021(25): 10948-10955.
[3]殷凱, 吳盼盼, 胡云華. 軌道交通紅鋼城站建設十一路站區間盾構隧道下穿鐵路橋梁方案研究[J]. 工程技術研究, 2018(10): 42-43.
[4]閆莉, 張智慧, 朱興. 地鐵隧道下穿河流施工遇富水軟弱地層的控制技術[J]. 城市軌道交通研究, 2021(3): 138-141.
[5]梁孝, 漆泰岳, 陳鵬濤, 等. 下穿河流盾構隧道的風險評價體系研究[J]. 鐵道建筑, 2020(8): 64-68.
[6]沙原亭. 地鐵盾構下穿河流及橋梁樁基施工與監測技術[J]. 鐵道建筑技術, 2015(10): 16-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