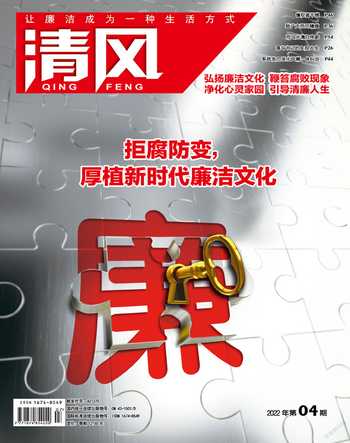慎權者不憒
張樹民

權力,是一種強制力量,往往職位越高,權力越大,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越強。所謂慎權,乃謹慎用權、嚴以用權之意;不憒者,頭腦清醒,不糊涂也。倘若權力掌握在以國家和黎庶為重的慎權者手里,則大有作為,利國益民;倘若權力掌握在利欲熏心的濫權者手里,則致公權私用,禍國殃民,同時也害了自己,禍及親人。因之,手握權柄者,只有慎權,方能保持頭腦清醒,不做糊涂事,秉公而廉潔,權為民所用,成為一個合格的公仆。
元代張養浩作《三事忠告》,提出省己、修身、戒貪,乃為政之要。廉以律身,忠以盡責,正以處事,慎以用權,能保其榮焉。反之,辱將近矣。南宋呂本中也于《官箴》開篇云:“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此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細品斯言,做到省己、修身、戒貪,就不會讓私欲沖昏頭腦,濫權之事就不會發生;做到清、慎、勤、忍,當為古往今來公認的好官。
慎,不僅將慎權囊括其間,恐怕還有慎獨、慎微、慎友、慎情之意,然慎權最為緊要。歷史上,深諳慎權不憒之理,重操守慎用權,公私分明的明白人并不鮮見。
《宋史》載,北宋仁宗朝,陳執中任宰相。他的女婿請求岳父給弄個官當當。豈料,陳執中回絕得十分干脆:“官,國也,非臥房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意思是官職是國家授予的,不是我臥房竹箱里的物件兒,怎么能你想要就送給你呢?陳執中位極人臣,位高權重,若想為女婿謀個一官半職,還不是手到擒來?甚至只使個眼色,就會有人主動給辦了。然而,陳執中用權極慎,決不肯公權私用。對女婿如此,對走其門路的其他人,更是拒之門外。一些人懷恨在心,不斷打小報告,痛陳陳執中凡事謹小慎微,呆板固執,處事過于死板,甚易誤事,不配為相。仁宗卻說,陳執中為相,深明慎權之益,恃權之害,頭腦清醒,從不縱權謀一己之私,考慮問題總是以國為重,既不瞞上,也不欺下,公器只為公用,朝中有誰能超過他這一點?陳執中一生慎權,即便有人忌恨,亦奈何不得他。至古稀之年而善終。
晚清曾國藩,執掌湘軍,朝廷倚重,權勢熏天。然而,曾國藩一生敬畏權力,“勤儉廉勞,修身律己”,慎權始終,用權如履薄冰,自感“時時有顛墜之虞”。曾國藩致書兄弟,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兄這等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他婉辭朝廷擢拔,奉勸兄弟辭官,以“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財,多財終為患害”為齊家理念,“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曾國藩之所以手握重權而戰戰兢兢,就是因為他頭腦清醒,深知汲取權力若火,善用則利國利民,濫用則引火燒身的慘痛教訓。曾國藩很清楚,當官與發財乃兩條平行的道路,克己修身、重操守之人,決不可使之交叉。一旦交叉,公權勢必成為謀私的利器,導致權力失控、脫軌,直至覆滅,濫權的和珅就是前車之鑒。一生守矩慎權的曾國藩,成為晚清的頂梁柱,不僅善終,身后還被追贈“太傅”,獲“文正”謚號,更有圣人之譽。
關于慎權之道,《名賢集》云:“官至一品,萬法依條……常懷克己心,法度要謹守。”當然,慎權,決不是不作為不擔當,而是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公正廉潔,不偏私,不貪財,不貪色,不枉不縱;在職權邊際內,處處以黎庶的向往為用權的指南。若此,就會凝聚民心,絕不會憒憒然,墮入深淵尚飄飄欲仙,禍已臨身尚不自知。
無數事實反復證明,握有公權者,不慎則憒,憒而濫權,濫權乃殃。無論歷史上手握重權的奸佞,亦無論當今被打的“老虎”、被拍的“蒼蠅”,無不與濫權而腐有關。因此,只要如曾國藩般時時自警、自省,律己奉公,矯正“三觀”,做到慎權并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