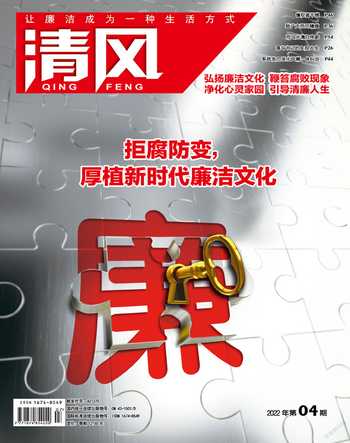唐太宗補過慎刑
沈淦

隋末唐初有一位張蘊古,老家相州洹水(今河南安陽一帶),他幼時便聰慧異常,博覽群書,還寫得一手好文章。張蘊古記憶力超群,看過的碑文能過目不忘,棋局被打亂后能一子不差地復盤,“背碑覆局”這個成語即由此而來。張蘊古書讀得好,而且對朝廷政治得失有很深刻的見解,“尤曉時務”。
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后不久,已經入仕的張蘊古上了一道名為《大寶箴》的奏疏,勸誡唐太宗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愛惜民力,不要貪圖享樂;開門納諫,虛心聽取大臣意見,不要自以為是、拒諫飾非;要豁達大度,“安彼反側”,使用人才不計前嫌、不拘一格,要安撫好曾經的對立面。
張蘊古這道奏疏不但文辭好,道理更是講得透,對于剛經過玄武門之變兄弟鬩墻亟須穩定朝局收攬人心的唐太宗來說,不啻一服良藥。唐太宗大悅,賞賜張蘊古束帛以示鼓勵,并將張蘊古提拔為大理丞,分管涉及尚書省六部官員和徒刑以上案件的審理。
張蘊古任職大理丞后, 相州出了個名叫李好德的人,因患有瘋癲病,發作時就胡言亂語,竟說出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話,被抓捕起來。張蘊古查明后上奏唐太宗:“李好德瘋癲病的癥狀很明顯,按照法律不應治罪。”太宗一聽有理,同意寬宥他。但在旨意下達之前,張蘊古竟偷偷地將處理情況告訴李好德,還在監獄里與他一起下棋。
負責舉劾非法行為的侍御史權萬紀發現后,就向太宗揭發了這件事;權萬紀還查明,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張蘊古老家在相州,他為李好德講情,有徇私之嫌。太宗聽后勃然大怒,感到被欺騙辜負了,當即傳旨將張蘊古押赴市曹,斬首示眾。
事過不久,唐太宗十分懊悔,張蘊古是個賢臣,案未查明而且罪不至死。于是太宗對宰相房玄齡等說:“張蘊古身為執法官員,卻泄漏朝廷機密,還與囚犯下棋,罪行是很嚴重的。但根據法律,不至于死刑。朕當時盛怒,就讓處死他,你們居然也不勸諫,一句話都不說,有關部門也未審核一下再上奏一本,就將他殺掉了,豈有這樣的道理?”房玄齡等都很慚愧,低著頭,默默無言。
于是,唐太宗傳下詔令:“從今以后,凡是犯有死罪的,即使朕傳令立刻處決,主管部門也不得執行,一定要經過反復審核,復奏五次后,才準依法施行。”唐代的“五復奏”制度,就是從張蘊古冤案后開始實施的。
后來,唐太宗還不放心,又傳詔要求:“從今以后,由門下省負責復審罪案。有的囚犯根據法令應判死刑,但在情理上能夠憐憫的,應該錄寫清楚后一一上奏。”唐朝時門下省與中書省同掌機要,并負責審查詔令,簽署奏章,有封駁詔令之權。
這個故事記載于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刑法》,當代人寫當代事,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對此亦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在封建極權社會,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于皇帝來說,殺一個有罪的官員也許算不上大事。而唐太宗因為盛怒之下殺了有罪卻不至死的張蘊古而深深自責,這在其時其境,算是難能可貴的;更可貴的是,他并不只停留在自責之中,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臣下及時進諫,匡正己失;制定“五復奏”制度;罪當處死,情有可原者,再重新審議……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再發生冤案。唐太宗廣開言路、虛心納諫的精神及重視法制、恤刑慎殺的措施,是使國家繁榮昌盛、形成“貞觀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畢竟是專制帝王,其冤殺張蘊古一事固不足取;然而,他補過慎刑的精神和一系列措施,顯然是值得當今執法、司法者借鑒的。13394B73-CB2C-4322-A0A1-5D8D25E4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