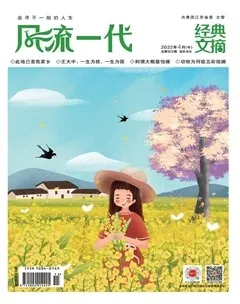動腦筋其實是在休息
袁越
成年人的大腦重量只占人體總重量的2%,卻消耗了20%的能量。可見,動腦筋是很費勁的。
人們都喜歡把計算機叫作電腦,但是,如果從能量消耗的角度講,這個比喻是不準確的。電腦關機的時候不耗電,人腦在休息的時候卻仍然要消耗能量。于是,又有人把人腦比作汽車發動機,平時休息時就像汽車怠速,耗油量較少,動腦筋的時候就像行駛途中,油門肯定得一直踩著才行,耗油量立刻就上去了。
這個比喻聽上去很正確,至少直覺上如此。美國《身心醫學》雜志曾經招募了14名大學生做過一個心理測驗,讓他們分別進行三種活動:坐下休息,給一篇文章寫讀后感,做一個與記憶力有關的小測驗。半小時后讓他們去吃自助餐,結果發現,學生們在動腦筋后的飯量明顯見漲,平均算下來,寫完讀后感后吃下去的熱量比休息后多了203卡路里,做完小測驗后更是多吃了253卡路里!
問題是:學生們動腦筋時到底多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的能量呢?
為了回答類似問題,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人做過試驗。1953年,一位名叫路易斯·索科洛夫的美國醫生在一位大學生志愿者的頸靜脈里插入一根針管,隨時監測他的大腦耗氧量,以此來間接測量這位大學生在休息和動腦筋時的能量消耗。出乎索科洛夫意料的是,這位大學生在閉眼休息和做數學題時的大腦耗氧量沒有任何差異。
索科洛夫認為自己的試驗精度不夠,因此沒有繼續做下去,這個試驗結果也因此而被埋沒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科學家們掌握了更加精密的測量方法,重新開始研究大腦的能量消耗,得出的數據和索科洛夫的相同。從總體上看,動腦筋并沒有多消耗能量。
但是,如果具體到大腦的不同部位,差別就顯出來了。有一種技術名叫“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成像技術”,可以對大腦進行三維立體掃描。掃描前先給志愿者服用一種帶有微量放射性的葡萄糖,然后用PET跟蹤葡萄糖分子的走向。眾所周知,葡萄糖是能量分子,葡萄糖分子聚集在哪里,就說明哪里的神經細胞正在拼命工作呢。
美國華盛頓大學神經生理學家馬科斯·雷克利試圖利用PET技術研究人腦的哪部分與語言有關,可是,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人在休息的時候,人腦中的某些部位異常活躍,可一旦他開始動腦筋,這部分就突然“冷”了下來,葡萄糖不再在這里聚集了。
和索科洛夫一樣,雷克利當初也認為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是背景噪音。但是,雷克利的同事戈登·舒爾曼不這么想。他把134名志愿者的PET數據綜合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這個奇怪的部位在每個人那里都是一樣的,都位于大腦皮質的中軸線上,從前額一直延伸到后腦。兩人于2001年聯名發表了這個試驗結果,并把這部分奇怪的腦組織命名為大腦的“默認網絡”,意思是說,平時這部分大腦一直是活躍的,除非人開始動腦筋了,它才會給其他部分讓路。
兩人還發現,這個“默認網絡”甚至比大腦的其他部位更加耗能,單位體積的能耗比其他部位高30%左右。
這個發現在神經科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這就等于說,我們的大腦深處一直存在一套神秘的系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偷偷干著某種神秘的勾當。科學家們急切地想知道這套系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們對照了以前的研究,發現這套系統的位置大約相當于大腦內側前額葉皮層,這部分腦組織和人的自我認知密切相關,如果內側前額葉皮層受到損害,人會忘記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很多事情。曾經有一位中風的病人,內側前額葉皮層被損壞了,醒來后她報告說自己仿佛繼承了一個空空蕩蕩的大腦,記憶中曾經有過的那些漫無目的的意識流現在都消失了。那些細碎的小思想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每一個正常人的頭腦里不斷地飄過,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罷了。
不過,人類有時也會意識到這些意識流的存在,人類還給它們起了個好聽的名字——白日夢。科學家認為,人的白日夢其實是非常有用的。我們做白日夢的過程,就是在把我們每時每刻的經歷整理出來,把不必要的信息扔掉,把有用的信息存檔備用。這項工程是如此浩大,以至于大腦必須每時每刻不停地工作,直到你需要集中精力分析一件事了,才會暫停一下,把寶貴的葡萄糖省下來留給負責進行邏輯分析的那部分神經組織。
關于這個“默認網絡”的研究是當前神經生理學的熱點之一,科學家們相信這個神秘的網絡將有助于解開人類的記憶之謎,甚至會最終揭開潛意識的面紗。不過,在科學界有定論之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別把動腦筋這件事太當回事了。要知道,你在動腦筋的時候,大腦其實是在休息呢。千萬別因此而多吃,否則你會越想越胖。
(六月的雨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命八卦:行走在人體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