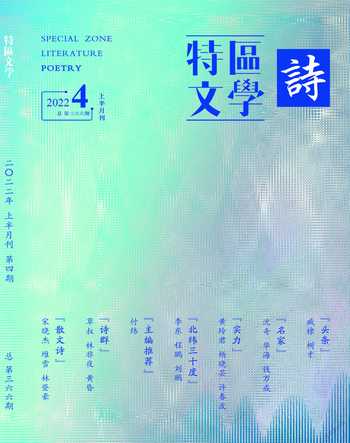生命中的鹽
施施然成名于組詩《走在民國的街道上》。“民國”是中國現(xiàn)代的開端,也是民主、自由、平等、女性解放等概念逐漸進(jìn)入國民心中的開始,可以說那是一個(gè)既新又舊、亦中亦西的時(shí)代。但詩中的“民國”并非完全是歷史上的物理的具體,公元的某個(gè)片段,它更多是詩人賦予想象與理想的一個(gè)精神的烏托邦虛構(gòu),是詩人的精神原鄉(xiāng)。那是古典與現(xiàn)代相融匯、講求精神質(zhì)量與文人風(fēng)骨的世界。
詩歌理論家謝冕與詩人、詩評家西川評價(jià)施施然的詩歌是“先鋒與古典并重”;詩人于堅(jiān)說施施然“率真、豐富而傲視”;南開大學(xué)羅振亞認(rèn)為施施然是一個(gè)寫作態(tài)度嚴(yán)肅“以性靈為詩歌招魂”的詩人,的確這和詩人唯美主義寫作理想符合;詩評家苗雨時(shí)先生認(rèn)為:施施然的詩不僅有“精神輪回的穿越書寫”也有“靈肉通達(dá)的生命修辭”,施施然的詩歌讓她從理想虛構(gòu)回到了生存現(xiàn)場;著名作家李浩說“施施然為自己的繆斯建立了個(gè)人‘面部表情’”,這是在褒獎詩人的文本風(fēng)格,認(rèn)可了詩人作品的個(gè)人化特征。人到中年,一個(gè)充滿激情的人天性中不可摧毀的東西會越來越多,施施然詩集《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讓詩人從懷舊的理想主義者,向現(xiàn)實(shí)步步靠近,詩人用懷疑的視角重新打量這個(gè)世界,臧否生活,但依然葆有對未來浪漫的信任。詩人自由、性靈、超越,以一顆古典柔軟之心,穿越而今當(dāng)下,開始從“私人客廳”走向“生活廣場”,把女性意識切入現(xiàn)代性的生存境遇,詩與思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痛。施施然自信文本是唯一的競爭力,她高調(diào)只讓文本說話的矜持而嚴(yán)謹(jǐn)?shù)膭?chuàng)作態(tài)度。
繼承中的轉(zhuǎn)型
詩人的詩歌定位說到底無論是“心靈寫作”還是“文化寫作”,基礎(chǔ)是“生命寫作”,是面對的詩現(xiàn)實(shí)和現(xiàn)實(shí)中噬心的精神主體,深入到生命現(xiàn)場,是發(fā)自內(nèi)心,并遵循內(nèi)心,發(fā)現(xiàn)“無限的詩意”。詩人用想象和虛構(gòu)完成了詩歌的“共時(shí)性”與“歷時(shí)性”的折疊,意境厚重、漸抵大氣。我以為詩歌不論抒情還是敘事都需要詩人對感覺的辨認(rèn),對語言詩性的融萃。詩歌的背后是什么?一首詩的結(jié)構(gòu)、語言等技術(shù)層面的東西,決定我們判斷詩歌高下的,恐怕更多的還是詩歌本身傳遞出來的獨(dú)立思想及境界。思想即是一首詩的“志”,也是一個(gè)詩人的擔(dān)當(dāng)。施施然說,“詩是我對世界的觀察,也是我活在這世界上的證據(jù)”。詩之心像、語象、物象都是秘密個(gè)人的情感因素。詩歌的敘事中,或多或少地隱藏著詩人自傳的片段。如《窗前的柿子樹》《黃昏從夢里退去》,詩人夢幻婉約,兒女情長,總是情懷。“身后/有人喚我乳名,無疑/是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我輕快地/應(yīng)一聲,庭院里的草就綠了。漫山遍野的杜鵑,就開了/我在奇妙的明亮里奔跑。周身/染了鮮紅的花蕊……/一張張臉向身后退去。退回到我的童貞—/母親,端坐在堂屋的中央”(《黃昏從夢里退去》),詩人堅(jiān)持思辨與反省同步的視角與立場,在母愛、情愛、自然、生命本質(zhì)、時(shí)間體驗(yàn)、歷史人物事件中凝眸與思考人性,隱現(xiàn)出些許的宗教情懷。
詩歌的內(nèi)驅(qū)力。詩人寫詩實(shí)在是一種自我修行。不論是書寫愛情、親情、歷史等情懷的抒發(fā),到對客觀世界中某種本質(zhì)性事物的發(fā)現(xiàn)與探索,以及后來世界各地旅行時(shí)的行吟與記錄,都是“知與行”力直抵知行合一。詩人曾只身西藏、新疆云南等一些偏遠(yuǎn)的有著宗教意味的地方,體感、眼觀、思考,游弋在現(xiàn)實(shí)與夢幻。在這里我看見某種“天涯孤旅”孤獨(dú)求敗,道成肉身。詩歌成為心靈縫合術(shù),詩人在萬物間的互動的行走中完成自我審視,發(fā)現(xiàn)日常中的詩性,呈現(xiàn)詩性的日常,復(fù)位生活天性之崇高。詩人用身體的真實(shí)改寫語言的表情。謝有順說,“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作家的根本處境”。施施然將廣闊的夢想藉借詩歌輸送表達(dá)。
在塔爾寺詩人看見“朝圣者從四面八方涌入如同/太陽蜂鳴的光線傾瀉……轉(zhuǎn)經(jīng)筒不息,轉(zhuǎn)去現(xiàn)世的苦難/磕等身長頭,脫下肉身的罪//在塔爾寺,我用手機(jī)拍下這一切/我呼吸急促/像小時(shí)候在夢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塔爾寺》)。介紹這首詩,因?yàn)樗査率且惶幾诮淌サ兀恳粋€(gè)去過的詩人都寫它,寫它的純潔和自己的迷茫。每個(gè)人都在朝圣的路上,尋找回家的路。詩人的純潔來自詩和經(jīng)歷,來自《半生記》的“清澈”和《想起90年代》中的“童貞還在體內(nèi)”的堅(jiān)守。詩人悲傷人生的盡頭是死亡;悲傷父母離開,悲傷不能阻止粗糲的霧霾進(jìn)入親人的肺腑……詩人保持傾聽的姿態(tài)和沉默的拒絕。詩人懷疑,詩人批判。詩人遭遇的,揮之不去的是一個(gè)浪漫主義者無奈的“紅與黑”的現(xiàn)實(shí)夢魘。“她眸子明亮,穿著泡泡紗的裙子/三只蝴蝶繞過她向森林的邊際飛去/她走走,停停。身后/一只毛皮斑斕的巨獸在噴吐光怪陸離之火//它像夜晚一樣躡手躡腳/不動聲色,卻/在無底的黑暗中,突然露出尖牙”,詩人的這個(gè)《現(xiàn)實(shí)》是一個(gè)童話?還是一個(gè)寓言?《現(xiàn)實(shí)》帶著魘性,還原了詩人潛意識中的某種恐懼與不安。詩人的警覺、焦慮和憂患。“一切都亂了,世界/仿佛被注射了過量的激素。”(《飲茶記》)。人格張裂在“因?yàn)閻?我們學(xué)會了微笑/和哭泣。”(《我們都是卑微的神靈》)。如今,寫下《批判記》《先鋒記》的詩人有了更高的站位和視野,她正努力告訴我們?nèi)绾嗡伎疾庞辛α俊T凇断蠕h記》詩人無情地否定了現(xiàn)在詩歌集體性“媚俗”和所謂先鋒性的“透過陰道向外看”。詩人坦言:潛心寫作,堅(jiān)守內(nèi)心,才是一個(gè)詩人的本分。“因?yàn)樘弁矗鸥杏X到生命的存在”(《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才是真正的在場言說。詩人的敘事能力不僅僅來自記憶和經(jīng)驗(yàn),也和詩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與想象力有關(guān)。詩人對世界的感知方式天真、隱忍、敏感、脆弱、尖銳,這些來源于自我本身骨子里的天性,也與成長過程中的經(jīng)驗(yàn)沉淀有關(guān),她用一個(gè)豐富和堅(jiān)硬的內(nèi)核努力地表達(dá)著個(gè)人的難以窮盡的復(fù)雜性。是的,“唯有黑暗使肉體中的靈魂溢出”(《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
不得不說的女性意識
歌德說,“永恒之女性,引我等向上。”女人對性別的回避其實(shí)是在自我冒犯。考察對女性寫作,讀詩,我們不是在尋找一個(gè)女人,而是正在完美一個(gè)靈魂。有人說,生而為女人,一切在自然而然中生成。女性身體天然著與生俱來的身份語境。而欣賞青年女詩人康雪詩句:“是嬰兒,以非凡的耐心慢慢教會了一個(gè)人成為母親”。
女人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詩歌比男性詩歌更細(xì)膩、更溫潤、更清靈、更芬芳,也更幽秘,細(xì)節(jié)上的魅力更加迷人。2017年開始,施施然在努力打造一個(gè)女詩人編、女詩人選、選女詩人、展現(xiàn)中國當(dāng)代最優(yōu)秀女詩人年度創(chuàng)作成果的平臺,開始思考女性和女性寫作等問題。施施然坦誠自己首先是個(gè)“真實(shí)的女人”,然后才是一個(gè)“寫詩的女人”,不知詩人是否意識到,是詩歌讓詩人成為一個(gè)關(guān)注女性和女權(quán)的人。施施然積極面對和思考的是,女人、女性、自己三者之間復(fù)雜的私人性和社會性關(guān)系。揭去世人眼里的“塵埃”。寫詩,寫“那些雞/從孵出來就晝夜被燈照著,不讓睡,除了吃/就是下蛋,一輩子沒有見過公雞……” 而今當(dāng)下的轟轟烈烈是一個(gè)逐漸認(rèn)清自己和喚醒這個(gè)世界的過程,它需要靈魂的在場和參與,更需要確認(rèn)我、我在的肉身和具體。
詩人的女性意識來自祖母、母親、西單表妹。詩人的詩歌啟蒙昆曲、京戲、越劇……杜麗娘、崔鶯鶯、祝英臺……婉轉(zhuǎn)、含蓄、孝廉、高貴……美輪美奐的傳統(tǒng)戲曲所無私地賦予詩人啟蒙和啟示,它為詩人獨(dú)立的、誠實(shí)有靈魂的詩歌注入了大量的活性元素。活在真實(shí)中審美中,拒絕媚俗和從眾,精神質(zhì)地智性而磊落。女性寫作,追求獨(dú)立、自由、尊嚴(yán)。“女人為之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逐漸形成的。”這里不得不提及《西單表妹》,表妹命運(yùn)詭譎,表妹有未經(jīng)稀釋的痛苦。“表妹是妖精的表妹/表妹是高挑兒的表妹/表妹是初中畢業(yè)/管“橙子”叫“凳子”/(你膽敢指出其中的錯(cuò)誤/她便拿白眼球瞪你)的表妹//從16歲開始,美,就將表妹/遮蔽,成了她唯一的外衣—/在修車鋪王鰥夫的眼中/美女都是裸體的。西城區(qū)的胡同/曾蕩起一個(gè)時(shí)代的性欲//人們其實(shí)并不了解/二十世紀(jì)末/一個(gè)紋身、穿鼻環(huán)的街頭少女/正如袈裟不了解僧侶/何時(shí)入定。野花不了解香水// 表妹的故事終止于一場意外/在昌平,為了避開馬路上踢足球的/兒童,她和一輛卡車迎面相遇/死的時(shí)候還是處女。”表妹人性俊美善良,活得性情,活著自己。詩人對西單表妹的肯定是一種自我投影或折射,也有鏡像的真實(shí)。《西單表妹》悲劇、自由、空靈。
詩言志的問題是每個(gè)詩人都無法繞開的神話。在我和大我,個(gè)體與集體之間其實(shí)并不存在絕對的鴻溝,一個(gè)人的復(fù)雜就像某些人說的“魯迅就是林語堂”。姥姥說:“只有登上千仞高峰,才會聽到雄虎的吼聲”(《殤》)。這里暗示性一種根性的觀念,“雄虎”而不是泛指的“虎”,這是骨頭里的,血?dú)馕拿},沿著這條意脈追索,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敬亭山作畫》《在黃埔軍校舊址》詩人建造了個(gè)人男女完美的世界,這里預(yù)示詩人的一種蛻變后訇然開闊。在散發(fā)著李白式雄性荷爾蒙的敬亭山上,詩人有“自由/將高于一切藝術(shù)”的精神真相。《在黃埔軍校舊址》有詩人自我異質(zhì)的生命真相。
詩歌的情感形式就是生命情勢,詩人言及身體覺醒中的個(gè)體覺醒生動而感人。是本能欲望也是人生理想。是才子佳人,也是兒女英雄。當(dāng)佇立在一幀黃埔一期的大合照前詩人有兩種眼光兩種身份的切換,“作為女人/我仰視他們/如仰視力量和父權(quán)/腦海中有一雙手/正飛快地將我?guī)щx雪白桌布金黃香檳的餐廳/推倒在繡著紫色大麗花的/席夢思上”,詩如果僅僅如此,就凋萎于平面化了,恰是這性別的翻轉(zhuǎn),讓詩有了“兩顆心臟”。詩人寫“作為男人/我視他們?yōu)樾值埽笥眩蛿橙耍?我祈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個(gè)/在炮火與血肉的沸騰中/和歷史一道/冷卻成永恒的黑白色”(《在黃埔軍校舊址》)。在黃埔軍校的舊址上,施施然有一張生動的臉。施施然有伍爾夫、杜拉斯、伊蕾、翟永明之外的另一種復(fù)雜,給人的感覺或蕭紅的才情與果敢,或丁玲激情與鐵血,或張愛玲的孤傲和癡迷……此刻、當(dāng)下,施施然是桀驁不馴的“新女性”,是那個(gè)現(xiàn)實(shí)中寫下《飲酒記》的人。《飲酒記》中你可以看見“詩者持也”的人格骨力和精神操守。施施然有聽過雄虎咆哮的姥姥,有一生“青衣”的母親,是百無禁忌的西單表妹復(fù)雜的“精神集合體”。有詩《飲酒記》為證:
他們叫她“騷貨”。仿佛她/是杭州西湖邊成蔭的垂柳。/她淡淡地笑起來:“與你們/匍匐在地面的叫囂相比,我拘謹(jǐn)如村婦。/高貴似女王。”/的確,整個(gè)世界都在被人類誤讀/這,又算得了什么。想到/當(dāng)他們讀到這行詩,必將更加狂躁地蹦跳/她禁不住又笑起來。她順手將手中的/葡萄酒,換成威士忌。哦,這感覺/多么奇妙,仿佛身體里/有某種慢,被奇特地置換出來。/她沿著同伴的手指,望向落地窗外/金黃的圓月像時(shí)間寫下的詩,在今夜/同時(shí)印上億萬仰慕者的雙瞳。/她端起玻璃杯,將琥珀色的液體一飲而盡/她像圓月一樣清醒。但世界東倒西歪/仿佛大地在搖晃。
王之峰,河北省黃驊市關(guān)家堡人,生于1964年,1985年開始詩歌寫作,曾在《星星》《詩選刊》《綠風(fēng)》《詩潮》《回族文學(xué)》《滿族文學(xué)》《大地文學(xué)》等期刊發(fā)表詩歌和詩歌評論。出版詩集《王之峰的詩》、詩歌評論集《鹽的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