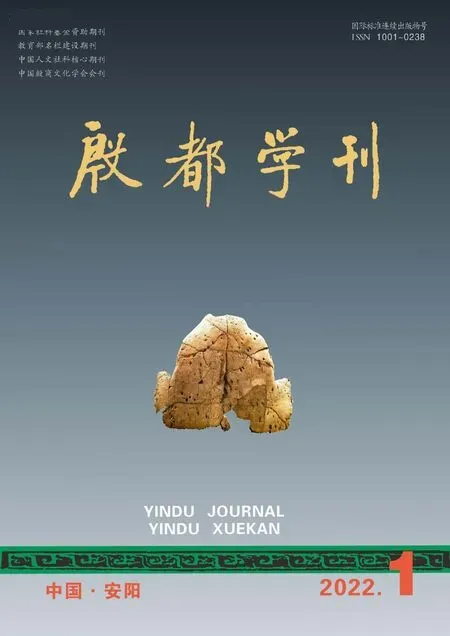卜辭“攸侯”都鄙之規劃與商王朝的“體國經野”
王旭東
(清華大學 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北京 100084)
被古文經師奉為“致太平之跡”的《周禮》一書,開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所謂“體國經野”,鄭玄注:“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孫詒讓解釋說:“次乃分國野疆域,使內外別異也。”(1)(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第13頁。概言之,即在“國”“野”兩大范圍內劃分地域空間,設置不同類型的居民組織。商周時期是否實行過“國野制”或類似制度,學界還存在較大爭議,(2)如趙伯雄先生認為西周時代不存在作為政治區劃的“國野制度”,一邦之內只存在大邑和小邑的差別,參氏著《周代國家形態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00頁。但商周王朝為鞏固、強化統治,在直轄及服屬區域內,對各類聚落的分布進行規劃與調整,這種行為不妨也借用古書的講法,稱之為“體國經野”。
關于西周王朝如何劃分治理自己的國土,近年來學者已由簡單的“王畿-封國”模式,深入到政治地理架構、王畿的行政區域及基層聚落形態、諸侯國與王朝的互動等問題上,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3)見朱鳳瀚:《關于西周封國君主稱謂的幾點認識》,收入《兩周封國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2-285頁;李峰著:《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胡曉軍、許景昭、侯昱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陳絜:《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收入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6-167頁;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相較而言,殷商史領域內相關問題尚存繼續考索的空間。宏觀上,商王朝的統治疆域被歸納為“王畿-四土-四至”三個層次,(4)宋鎮豪:《論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27頁。但其中許多史實尚未明晰,如所謂“王畿”有多大范圍,如何管理?“王畿”外的都鄙邑落商王怎樣管控?“殷邊侯田”性質當作何理解?本文擬選取晚商“多侯”之一的“攸侯”為例,以其所轄鄙邑的變化為中心,談一下“體國經野”在商王朝東土具體是怎樣進行的。
一、攸地在東土經營中的戰略地位
商王己巳日自弁地出發趕往攸地,至遲癸酉日已抵達,盤桓三到四天后,啟程前往舊地,最晚辛巳日到達。此“舊”地一般認為即無名組卜辭中的“夷方邑舊”,曾經是人方集團的重要聚落。(5)李學勤:《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約一個月后,商王的隊伍回到攸地:

表一 帝辛十祀十一月至十二月日譜

表二 帝辛十一祀正月至二月日譜

正因為戰略位置如此重要,至遲在武丁時,攸地已經設侯,并一直延續到殷代末年。帝辛十祀“征人方”時,“攸侯喜”是配合商人作戰巡狩的主要力量(《合》36482,黃)。朱鳳瀚先生認為,“商王朝的‘侯’應該有更強的、較為單純的邊域軍事職官性質”,同時“擁有自己的屬地以安置其家族,其屬地與其軍事防衛區域范圍應是大體相同的”,(10)朱鳳瀚:《殷墟卜辭中“侯”的身份補證——兼論“侯”、“伯”之異同》,收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第4頁。換言之,“侯”在其領地內兼有“軍事職官”和“封君族長”兩種身份,故“攸”地既是商王朝的邊域防區,也是“攸侯”個人的領地。值得注意的是,為適應東土局勢的變化發展,商人統治者對“攸”地聚落布局作過一番精心規劃,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問題。
二、“在爿牧”與“在義田”:從私邑到公邑
目前所見殷代前期的攸侯,有賓組卜辭中的“攸侯唐”(《合》3330(11)《合》3330即《龜》2.13.18,拓本不全,右側無字部分被裁剪,完整拓本及照片見《東大》B.0559b。有學者將《東大》559b釋作“弜侯”,不確。),及歷組卜辭中的“攸侯由”,后者屬歷組“父丁類”字體,時代可能稍晚于“攸侯唐”。關于“攸侯唐”,除其名號外我們別無所知,而“攸侯由”的相關資料卻彌足珍貴:
戊戌貞:右牧于爿攸侯由鄙。
中牧于義攸侯由鄙。 (《合》32982,歷)

然而卜辭顯示,商王卻將“右牧”“中牧”派遣到了攸侯的私邑之內。甲骨文中的“牧”本職大概與畜牧有關,(13)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第162頁。攸侯邊鄙的“爿”“義”等地,也許水草豐美,宜于放牧,今已不能詳考;不過僅據《合》32982一條卜辭,我們尚難判斷,“右牧”“中牧”是臨時受命到“爿”“義”活動,還是長期駐扎于此。在晚期無名組、黃組卜辭中,又出現了重要線索“在爿牧”:
弜悔。吉。
弜執。
辛亥卜在攸貞:大左族有擒。
不擒。 (《合》36492+36969+《懷》1901,黃)

另一處“中牧”所去的攸侯鄙邑義,并未自此常設“牧”職,而是變為“田”官的駐地:
“在義田”應即設置在“義”地的田官,他向商王貢納抓獲的羌人,用為祭祀的人牲。(18)獲羌之事契文習見,貢納羌人作為人牲者更是遍布商王朝四土,陳絜先生告知,所謂“羌”可能是身份標識而非具體國族。故絕不可將“執羌”者一律目為西土貴族。義地緣何未設“牧”而置“田”,個中詳情今天已難知曉,但從“在義田”能夠捕獲羌人看,他也同“在爿牧”一樣,擁有獨立武裝,是王朝對外擴張的助力。無名組卜辭《合》27979云“戍叀義行用”,所謂“義行”就是來自義地的行伍,(19)寒峰:《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制數則》,收入胡厚宣主編《甲骨探史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401頁;羅琨:《商代戰爭與軍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418頁。平時大概即由“在義田”統轄。
商王將“田”“牧”等職官設置在攸侯領地內,其戰略意圖應在于控制交通要道,部署武裝拓殖,提高作戰指揮效率。無論“爿”“義”二地在名義上是否交付給商王,它們事實上都已由攸侯的私邑轉變為重兵駐守的“公邑”。“田”“牧”原本不是當地的族長,純粹因商王的任命而統治其轄地,在此過程中,殷代國家直接管控的疆域有所擴大,集權趨勢也得到增強。類似情形后世并不少見,如西漢景、武削藩時,為避免諸侯王聯絡胡、越,割其國邊邑而置直轄郡縣,所謂“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敘》),(20)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頁。與商人割取攸侯鄙邑而設“田”“牧”,可謂異曲同工。
三、“攸侯喜鄙永”:從族邑到私邑
盡管相繼失去了屬邑“爿”與“義”,但在晚商末年,攸侯仍保有相當大的勢力范圍,例如卜辭記載有“攸侯喜鄙永”:
癸卯卜黃貞:王旬亡咎,在正月,王來征人方,在攸侯喜鄙永。(《合》36484,黃)
賓組卜辭中有一位常見的貞人稱為“永”。除占卜以外,他也曾領受別的任務:

(3)貞:冓眔永獲鹿。王占曰:獲。允獲。
丙午[卜]殻貞:冓眔永不其獲鹿(《合》1076正、反,賓)
(4)丁丑卜爭貞:來乙酉眢(21)“眢”舊或以為是祭祀動詞,近陳劍先生釋作“兼”,沈培先生推測是“瞇”之初文,通作“彌”,何景成先生釋作“盾”,讀為“循”,各有創見,雖然目前還難以達成一致,但從相關辭例看,該字看成一個副詞或更可信。各家意見可參看何景成:《試釋甲骨文的“盾”字——甲骨文所謂“眢”字新釋》,陳光宇、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0頁。用永來羌自元……(《合》239,賓)

廩辛、康丁之世,永族命運迎來巨大轉折。首先是族長被任命為“戍”官(23)甲骨文中“戍某”之“某”為族氏名,參見朱鳳瀚:《再讀殷墟卜辭中的“眾”》,收入《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第20-28頁。:
戍永于義立(位),有[截]。(《屯》4197,無名)
“于義位”大概是指在義地方向布陣迎敵,這個“義”當即前文討論的“攸侯由”鄙邑,此時很可能已經置“田”,而“戍永”雖任職為“戍”,仍在守衛自己的領地。但不久后永族就徹底為商王所控制:
辛巳卜:王其奠元眔永,皆在盂奠,王弗[悔]。洋。大吉。(《屯》1092,無名)

表面上看,攸侯占據永地后,擴大了自己的勢力范圍,似乎與商王朝鞏固統治的目的背道而馳,實際上,過去“永”雖為商人臣屬,但仍保有自己的領地,經此一番調整,原本獨立的“永”族轉變為攸侯私屬之“永”邑,而商王可借助攸侯控制萊蕪地區,謀求邊域的整體穩定。從這個角度看,“攸侯喜鄙永”與設置“牧”“田”的爿地、義地一樣,都可視為商王朝的政治疆域,只不過在管理方式上有直接或間接的區別。
最后附帶說一下,與“永”一起遷徙的“元”,可能也曾是“多侯”之一:
戊寅卜貞:令甫比二侯及眔元,王省,于之若。(《合》7242,賓)
“元”與另一位“及”并稱“二侯”,曾受令與“甫”配合。然而元侯似未能在商王朝的擴張中發揮有效作用,故最終難免顛沛流離的命運。其舊居元地在乙辛時代被辟為田獵點,按《英》2562記載,商王去元地田獵時駐蹕在攸,暗示元可能也被納入攸侯的勢力范圍。
結語
綜上所述,在商代晚期,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政治勢力,犬牙交錯地分布在萊蕪以東的“攸”地周邊:
第一類是相對獨立的族邑,如武丁晚期的永。國家對這些強宗大族的控制并不十分牢固,時叛時服者亦不在少數。臣服的族邑固然也為殷代國家的一部分,但至少在形式上,其領地不受商王直接管轄,不妨看作商王朝“服屬”區域。
第二類是擔任王朝官職的“諸侯”,如攸侯。按照傳統認知,商代的“侯”也是獨立性較強的外服封君,但從攸侯的實例看,商王可按照宏觀戰略布局增減其邊鄙屬邑,調整其領地范圍,顯然殷代國家對“侯”的掌控更為嚴密,其統治區域可視為殷代國家“間接管理”的政治疆域。
第三類則是直屬于商王的外服職官,如在爿牧、在義田。“田”“牧”等職最初或為墾田放牧而設,但在殷代晚期基本演變為軍事長官,扼守各處戰略要地,為商人拓殖提供武力保障,其轄境可看作殷代國家“直接管理”的政區之雛形。
就晚商攸地周邊的形勢變化而言,永族族邑(第一類)被并入攸侯領地(第二類)之中,攸侯鄙邑爿、義(第二類)又被規劃為“田”“牧”職官的轄地(第三類),總的趨勢是“服屬”區域向“間接控制”或“直接管理”的政治疆域轉化(參圖一),具體手段包括遷徙舊族、設立新官、軍事管制等等。為拓展勢力范圍,商王朝在東進前線萊蕪地區屯兵戍衛,設“侯”置“田”,殷代國家的“集中”傾向也因此大大增強。攸侯鄙邑的調整應非個案,在其他戰略要地或邊域防區,類似變化恐怕也會發生,這無疑是商王朝“體國經野”的一項重要內容,商王的統治藉此得到鞏固,國家政權日益成熟,甚至誕生了地方行政的萌芽。

武丁晚期攸地周邊政治地理局勢示意 乙辛時期攸地周邊政治地理局勢示意
當然,我們對殷代國家的成熟度也不宜評價過高。一方面,直到殷末,在商王朝統治區域內仍有眾多族邑錯雜分布,東土邊域“體國經野”的布局不能代表商人的全部國土,如春秋時楚國,在北方邊境很早建立起具備地方行政性質的縣制,但內部的“封君制”卻也同時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直轄的政治區域并不能穩定存在,按周初文獻敘述,商人所置“田”、“衛”等職官,基本已演變為與“侯”性質相同的、承擔軍事職能的外服封君,(28)如“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尚書·酒誥》)、“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尚書·召誥》)、“惟殷邊侯、田”(大盂鼎,《集成》2837)、“舍四方令,諸侯:侯、田、男”(令方彝,《集成》9901)等。所謂國家直轄的“政區”,易為個人之封疆。盡管商王朝“體國經野”的種種措施,展現出殷代國家走向統一、集權、行政化的趨向,但理想與現實還相距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