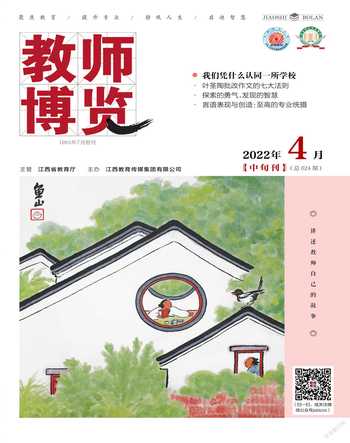誰的青春 不迷茫
陳忠

一、理解每一種痛苦
秋高氣爽的季節,校園桂花分外香。
幾個女生闖進我的工作室,焦急地說:“我們寢室有個女生絕食兩天了,誰勸都沒用。陳老師,您幫幫忙!”“她愿意與我交談嗎?”我沉穩地問。她們用目光交流后,留下一句“我們想想辦法”,便匆匆離去。
半個小時后,四個男生幫忙把一個女生抬來了,后面跟著之前那幾個焦灼不安的女生。我先請這個女生坐下,再謝謝四個男生,并請他們離開——談女孩子的事,他們在場不方便,其他女生或坐或站不必回避。那絕食的女生趴在桌子上,一言不發,一動不動。“喝水嗎?”我問。她慢慢晃了一下頭。“生病了?”她仍不出聲。“心事能說給陳老師聽聽嗎?”她依舊一動不動。
我只好把目光移向她的室友。一個稍胖的女生會意地說:“她與一個男生談戀愛,談了很長一陣子。最近對方提出分手,鐘情的她氣得不行,想去找男生說清楚。對方或是躲著不見,或是見面便吵,太傷她的心了。她已經兩天不吃不喝,就躺在床上哭,現在連走路、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真急死人。”原來是一個女孩墜入情網難以自拔的故事。
已經兩天不吃不喝怎么行?先得解決餓肚子的問題,這是當務之急。時值中秋節后,我打開桌子上的餅干盒,里面有月餅,請她吃,還倒了一杯水。她不做回應。“吃陳老師的東西沒關系。”我說。她趴著不動。“陳老師喂給你吃。”我拿出月餅,用小刀切開,把一小塊往她嘴里送。她拒絕張嘴。“你聽過我的課,是我的學生。老師請你吃,你不賞臉,我在同學們面前多沒面子。”室友也趕緊相勸:“你別傷了師生情,千萬別讓陳老師也難受得不吃不喝流眼淚啊。”另一個室友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說:“給陳老師一個面子,吃一口吧。”或許是盛情難卻,或許是饑餓難耐,她終于張開嘴,吃了兩個小月餅,又喝了幾口水。然后,她堅決不再吃,我也不勉強她。不過她原本蒼白疲倦的面孔,略顯出一絲精神。她聲音很微弱,慢慢細說著心中的隱痛——
兩年前,他們在返校的火車上相識,因為是校友,又剛好同路,所以談得很投機。學校不算大,食堂吃飯、教學樓上課、校園散步,低頭不見抬頭見,接觸多了,他們就有了感情。他個頭高,卻比她低一個年級,學習成績過得去,人挺仗義,長得也帥氣。有陣子,他生病,她幫他洗衣服、買藥送飯。他家在農村,經濟較拮據,兩人在外面吃飯都是她付錢。她真情待他,他卻甩了她,還說沒理由。“愛他一兩年,大家都知道了。如今他一下子拋棄我,我沒有心理準備,接受不了,我死給他看!我是認真的。真氣人,我恨不得殺了他這個沒良心的家伙!”她越說越氣,怨氣被宣泄出來,聲音也大了一些。
“你家里還有誰?”我問她。“有爸爸、媽媽、哥哥,還有一個奶奶。”“如果你真自殺了,他們會怎樣?”她靜靜地聽著,過了一陣子才回答:“從小是奶奶把我帶大的,奶奶最疼我。如果我死了,她也活不了。”說到這里,她的眼眶里有淚花在涌動。“你是一個聰明且漂亮的女孩,又善解人意,犯得著為一個‘負心郎去死嗎?你的死能感動他嗎?你都死了,即使他被感動又有何意義?他決心放棄你,你還用死向他證明什么?”一連串的問號,是想喚醒她的理智,把她從糊涂的“情潭”中拉上岸來。她的淚花漸漸收起,臉上多了一絲自責的神情。
“你現在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問。她沒有遲疑地回答:“好人呀!”“你如果真的把他殺死了,是好人還是壞人?”她輕輕地說:“壞人。”“你為什么放著好人不做,去做壞人?一個不懂得愛、不尊重愛、不珍惜愛的男人,值得你為他自殺嗎?值得你去殺他嗎?”她不作聲,心里肯定在想這些問題。我想她會找到答案的。
“你戀愛過嗎?”“沒有。”“這是你的初戀?”她點一下頭。我繼續問:“初戀的‘初字什么意思?”“初,就是第一。”我點頭肯定她的回答,又問:“那初戀呢?”“初戀是第一次戀愛。”我邊點頭邊問:“有初戀,第一次戀愛,這意味著什么?”她想了想,接著說:“有再戀呀!”我笑著說:“很對,真聰明。中國的語言文字博大精深,古人早就認識到這事,造字組詞時便考慮到了男女戀愛的過程及變化,有早戀、初戀、再戀、單戀、失戀、苦戀、多戀等等詞的出現,多豐富呀。如果大家都是一次戀愛就成功,還造‘初戀這個詞干什么?只要造個‘死戀的詞就夠了,男女一戀到死,白頭偕老,多好。初戀,就意味著可能失敗,第一次失敗了,不要緊,第二次已經在等著呢。你知道初戀為什么容易失敗嗎?”“不知道。”“道理很簡單,大家都缺乏經歷與經驗,都不懂得怎么去戀愛,都在盲目地戀呀愛呀,對戀愛的復雜性、變化性、后果等等,缺乏認識與準備。你知道什么是戀愛嗎?”她開始搖搖頭,然后加上一句“戀愛就是彼此喜歡”。“是的,戀愛就是彼此喜愛、互相愛慕的行為表現。戀愛是一個過程,一個彼此相識、相交、相愛的過程。通過認識、了解、考察、考驗,越談越近相互牽手,或者越談越遠彼此分手。所以,戀愛應該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或者牽手,或者分手。其實,牽手也正常,分手也正常;牽手了也可以分手,分了手也可以再牽手。我們要以一顆平常心來應對初戀,應對戀愛。說到底,戀愛就是選擇愛人,選對了人幸福一陣子或一輩子,選錯了人痛苦一陣子或一輩子。你說對嗎?”
她和室友聽得津津有味,有的睜大眼睛看著我,有的豎著耳朵用心聽,她也顯得自然多了。當今社會,許多家長與老師只一味要求孩子好好讀書考大學,對孩子成長中的許多問題避而不談,甚至做出硬性禁止的規定。他們忘了孩子也是“人”,不以人為本,不重視人性、人品、人格、人情的教育,屈從于“應試教育”,把孩子變成考試的工具和賺錢的手段。孩子被異化了,還強詞奪理說:“沒有辦法,全社會都這樣。”多么可怕又危險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來,我倆握個手。”她同意了。我握著她的手說:“不會再干傻事了吧?”她有點激動地回答:“放心吧,陳老師。謝謝您!”“不對,首先謝謝你自己,是你戰勝了自我。”然后,我與其他女生也一一握手,夸獎她們的熱情與善良,叮囑她們請她下館子,吃一碗熱乎乎的面條,放點辣椒開胃。她站了起來,在室友的陪伴下,自己走出工作室。我把她們送出大門,再次握手道別,說:“需要老師幫助時,歡迎再來。”她朝我彎腰鞠躬,轉身離去了。
這個女生會走出初戀受挫的陰影嗎?我惦記著。她真的找回自我、自尊、自信與自愛了嗎?我期待著。
二、聽見每一個求助
“咚、咚、咚”,伴隨著敲門聲,工作室走進一位中年婦女,她問:“你是陳教授嗎?我是慕名而來求助的。”我請她坐下,并遞給她一杯茶。“謝謝。”她喝了一口茶,開始講述,“我和老公都是紡織工人,沒讀多少書。前些年,工廠改制,我們都下崗了,只得打工謀生。我們生了個女兒,很乖,讀書一直不用我們管。如今她讀初三了,長得比我還高,像個大姑娘。”講到這里,她停下來,連喝了兩口茶,然后話鋒一轉,就數落女兒:“可是突然不曉得哪根神經搭錯了,都快一年了,女兒把我視為仇人,不理我,不叫我,不跟我說話。我弄飯給她吃,買衣服給她穿,掙錢給她花,對她一百個好,可她怎么成了無情無義的白眼狼?”說到傷心處,這位一臉愁云的媽媽哭了。我遞上紙巾,任其宣泄,沒有插嘴。
待她稍微平靜后,我問:“女兒何時來例假的?”母親一愣,說:“小學六年級。”“母女關系一直緊張嗎?”“不。”“怎么突然變了?”“我弄不明白。”“你和她爸爸沒有和女兒溝通嗎?”“死丫頭什么都不說。”“青春期的女孩最敏感、脆弱、多變。她不叫你、不與你說話,一定有她的理由。關鍵要找到那個心結。”媽媽點頭認同,立馬求助我,想叫女兒來談談。“她愿意來嗎?”媽媽搖搖頭:“我和她爸肯定叫不動。”想了想,我給她一個建議,請班主任動員女兒來。母親認為這個方法可行,決定試試。
星期天上午,女兒跟在媽媽后面走進了工作室。我請母女倆坐下,然后沏好兩杯茶。“歡迎你。”我向女生伸出右手。女生不習慣,停頓片刻,還是與我握手了。“挺面善、挺漂亮的青春女孩嘛。”“謝謝。”聽到夸獎,她略顯羞澀。“你媽媽前幾天來找我,說快一年了,你不叫她,不與她說話。你知道嗎?媽媽心里難受呀!那天在我這里痛哭了一場。”女生臉蛋依舊陰沉,兩顆眼珠快速轉動了一下。“你愿意同陳老師聊聊嗎?”她沒有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女兒不叫媽、不與媽說話,我想,一定是有理由的。”這句話,讓女生感興趣了——她的眼神告訴了我。“我倆聊聊,媽媽可以旁聽嗎?”她慢慢晃了晃腦袋。媽媽看見了,起身說:“好,我出去。”并隨手把門關上了。
媽媽走了,女生似乎有一種輕松感、安全感。“快一年了,你不叫媽媽,不與媽媽交談,卻每天在家里吃住,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出門不見進門見,你心里也一定很不好受,是嗎?”一句理解的話,打開了女生的心門,無聲的淚珠成串地往下掉。我指了指桌面的紙巾。待她平靜后,我接著問:“你愿意把不理媽媽、不叫媽媽的緣由,說給陳老師聽聽嗎?”她用紙巾擦擦眼淚和鼻涕,喝了一口茶,終于開口說話了——
從小,爸爸媽媽很疼我。長大后,我逐漸懂事,知道他們下崗謀生不容易,便更用心讀書。盡管他們很忙,文化程度不高,難以陪我學習,但我不怪他們,做女兒的也總會感恩父母。初一開始,我很快發育,一下變成了大姑娘。從這時候開始,媽媽喜歡嘮叨,總說男孩子很壞,要我遠離他們,當心吃虧上當、受到傷害。說一兩次就算了,老掛在嘴上煩不煩?一年前的某天下午,放學早,有位同組的男生向我借書,便一道來我家。拿了書,他就坐在我房間里閑聊。他很幽默善談,平日閱讀廣泛,是個渾身有故事的帥小伙,大家都喜歡他。正當我倆有說有笑時,媽媽下班回家了,看見男生坐在我床邊,立馬拉長了臉,大聲問我:“怎么這么早回來了?”男生見狀,起身拿書就走,我送他到大門外。當我返回房間時,看見媽媽正翻被子和床單反復查看。開始我沒有反應過來,問她“在找什么”。她沒作聲,卻找得很仔細。我突然臉紅了,天吶,母親怎么能這么做?!她分明在找毛發!在找血印!“你把女兒當成什么人了?!”我的尊嚴被侮辱了!我怒火三丈高,立刻叫她走,然后關門痛哭,晚飯也不想吃。自此之后,我不愿同她說話,也懶得叫她。為什么她不認錯?為什么她不向我賠禮道歉?一想到她翻被子、床單的場景,我沒法跨過那道心坎!太傷我的心了!第二天去學校,那個男生看見我,說:“你媽媽怎么那么兇?”陳老師,你叫我怎么做人?
原來是這么一回事,我理解青春期女孩的情緒變化。“你想化解母女矛盾、改善母女關系嗎?”我問。她一直望著我,遲遲不吭聲,也許內心正在糾結,進行思想斗爭。喝了一口水后,她緩緩地點點頭。這是我期待的結果:“去,把媽媽請進來。”她起身出去,一會兒,媽媽跟在女兒后面走進了工作室。此時,我從桌上的書堆里,找出賈容韜的《改變孩子先改變自己——好爸爸賈容韜教子手記》,對媽媽說:“孩子的問題常常不是孩子的問題。父母是孩子的天然老師。別看孩子天天在我們身邊,父母真的懂孩子嗎?未必。”我又把孫云曉、李文道的《拯救女孩》擺在她們面前,建議她們買來好好讀讀,看看女孩的生理特點、心理特點、行為特點、情感特點。“長大真的不容易呀!人們常說女大十八變,啥時候變?怎么變?”媽媽和女兒都沒有回答。我再拿出第三本書,杜啟龍的《陪孩子度過青春期:父母送給青春期孩子的成長禮物》。青春期是孩子人生一個“暴風驟雨”的階段,很多身心健康問題都始于此。我們常贊美青春美好,殊不知,青春陽光下可能隱藏著青春迷茫、青春疼痛、青春不知所措。所以,父母需要關注,需要學習,需要陪伴。
做好這些鋪墊后,我便把女兒剛剛說的那些話,原原本本復述給媽媽聽。媽媽一臉疑惑,這是事兒嗎?“當年孩子她外婆不就是這樣教我的嗎?我錯了?”媽媽自言自語。我微笑地問:“你小時候在哪里?”“在農村長大。”“孩子外婆讀過書沒有?”“沒有,文盲一個。我也才小學畢業。”“現在時代不同了,生活不同了,觀念不同了,你承傳鄉下媽媽的話,在城里長大的女兒不愿聽。你按照當年你媽媽的思維做出的事,如今新時代的女兒特別反感。真是好壞一句話,好壞一件事,源于‘代溝呀。”聽話聽音,機靈的媽媽立刻轉身面對女兒,像自言自語,又像認錯自責:“沒想到,我好心做事竟傷害了女兒。我錯了,女兒。”我立即抓住時機對女生說:“不容易,媽媽認錯了,道歉了。來,站起來,跟媽媽握握手,再抱抱。”當母女握手擁抱時,兩人都哭了。女兒抱著媽媽的肩膀邊哭邊說:“媽媽,我也不好。”母女一年來的矛盾終于化解了。
臨走之前,媽媽把手機給女兒,說:“把那三本書拍下來,好網購。我們都要多讀讀書。”
(作者單位:九江學院)
(插圖:譚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