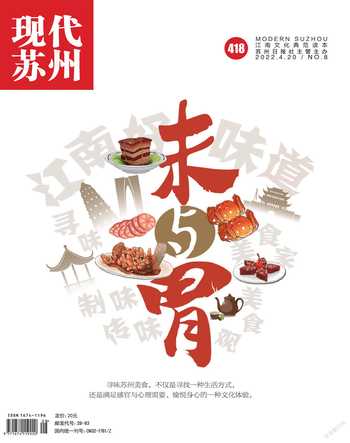費新我的書法外交
文 費之雄 詹小嫻

早在上世紀50年代,畫家費新我就經常參與接待來蘇的外國文化人士。前后會見過蘇聯、匈牙利、德國、巴西、瑞典、芬蘭、澳大利亞、印尼、日本等許多國家和地區著名的藝術家和社團。有的和他們都有筆墨交誼,有的還保持通信聯系,互寄參考資料。其中因為與日本兩位書家通信,“文革”中受到了審查。
經過了右手病廢,換用左手,“十年磨一劍”的臨書實踐,富有獨特個性的“新我左筆”書法逐漸形成。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那凝重奔放、縱橫捭闔、參以畫意、富有氣勢的書法作品越來越為世人所承認和追摹。他的作品也由此走出國門。
1972年中日關系開始解凍,專門對日發行的《人民中國》雜志來蘇辦筆會。費新我應邀寫了毛主席詩詞《十六字令·山》,刊登后引得好評。郭沫若先生見后大為贊賞,稱其:字里行間有山石突兀之態,群山起伏奔騰之勢,寫出了詞意。這幅字的發表,是費新我多年來藝術實踐、藝術見解的大釋放,標志著他的書法上了新臺階,開始走向國際藝壇。
1978年秋,剛剛復出的鄧小平訪問日本,費新我擬寫了“相鄰一帶水,友誼萬年春”的語句表示祝賀。《人民日報》于10月23日以顯著位置刊登了“新我左筆”的原件照片和文字:鄧副主席赴日訪問,中日雙方即將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謹書聯句,祝愿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費新我。報紙還加了一個小注:著名書法家費新我用左手寫的。
報紙發表的當天,費先生正在家鄉湖州雙林鎮,向書法愛好者作講座,他高興地說:好,這件事辦好,辛苦了《人民日報》領導邵華澤同志,他曾特來蘇州商量安排。這件事意義重大,我應該做好。從此,費新我獲得了一個“書法外交家”的美稱。一股左筆旋風首在東瀛刮起。
1982年1月21日起,由北京榮寶齋組織的《費新我書法展》先后在日本東京、大阪舉行。230件作品兩地各一半展出,盡管是一個人的單純的書法藝術展覽,但并不覺得單調,卻是豐富多彩,洋洋大觀。雖然是天寒地凍,但人氣十足,歷時10天,盛況空前。引起了日本書畫名人和社會朝野的轟動和贊賞。
在東京西武百貨店展覽大廳,大門一打開,迎面即見的是“新我左筆”四條屏六尺對開的通景:《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使觀者眼睛為之一亮。原詩是唐代大詩人杜甫描寫舞劍者的高超藝術,稱吳地書法家張旭見此景,得其神,而草書長進的故事。費先生將輕重、徐疾、節奏、韻律、力度等種種舞蹈和太極的因素融入書中,體現出雄健剛勁的動勢和瀏漓頓挫的節奏,使作品氣韻生動,神采飛揚。人們連連叫好,被日本書道協會會長村上三島先生捷足先登,掛上了他的認購紅條。所有作品隨后均被掛單。年屆八十的費老,由于群情激奮,竟在展覽大廳中現場揮寫起來。

曾到我國交流書法,與費老相識的全日本著名書法家青山杉雨、梅舒適、飯島太久磨等都恭逢盛會。《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朝日電視臺》等首席媒體爭相報道,稱他是“墨中之仙”“異峰突起、一新耳目”“是筆耕心織的使者”“不僅是一位藝術家,而且是一位哲學家、一位有志之士”。
在大阪展出時,費老又應請作了書法講座,講了書法與太極的關系。他有數十年太極拳、劍的功夫,因之邊講邊演,氣沉丹田,一手未止,二手又起,連綿不斷,內勁不絕,一派神韻。聽得日本朋友連連稱:中國的太極拳是活動的書法,書法是凝固的太極。
改革開放伊始,榮寶齋組織的這次訪日展覽有特殊的使命。主要是投石問路,為打開中國在日本的書畫藝術市場。有了費新我個展首次順利進軍日本,接著,范曾、鄭乃珧、啟功、黃苗子等著名書畫家個人作品展也相繼成功舉辦,被稱是為中國書畫走向世界作出了篳路藍縷的貢獻。
在東京,費老還與多年通信的老友,九十高齡的老書家伊藤東海第一次相見,百感交集。“文革”中因此關系受到批判,被沒收了老書家書贈的杜牧“張好好詩”五條一堂屏。先生說:好得我還在。便當即揮毫:“迎君不知疲”五個大字,表達了一位老友的心意。
離大阪不遠的池田市與蘇州市締結友好城市不久,費老受市政府外辦委托,當起了友好大使。他專程前往拜會了池田市政府,又由副市長陪同,到了擔任池田市與蘇州市友好協會會長的小山藤兵衛家做客,小山夫人親自下廚,用精美的日膳招待貴賓。以后他夫婦倆每來蘇聽鐘聲,雙方總要相聚。
在日期間,費老還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千里書道會會長重森翠溪,原是位民間書家,會員中絕大多數是女委員、家庭主婦。他很仰慕費老,常將費老作品展示后給大家講評。首次見面后多次來蘇交流,費老也在與他通信中除書寫些作品外,還提出些許灼見,供參考。因此雙方十分投緣,相約兩年會面一次。重森77歲喜壽時收到了費老寫的《友情墨緣與年俱增》記敘歷年交往的長卷。遽料,費老在1992年去世。重森踐約,仍于1994年攜子女及會員九人來蘇掃墓。1998年在他米壽(88歲)書展時,還將歷年來費老贈與他們的十余幅作品一道展出并編輯入冊。
費老的獨特書藝,引得日本行家都想一睹為快。有一年,一個日本代表團來華,他正在南京,請作現場示范。為時短暫,人員眾多,這時,似乎是商量好的,只見前排年青觀者一一蹲下,以下腭擱臺邊,第二排迅速將頭插在前排者兩肩之間,如此三排、四排(如我們習慣拍集體照狀),只幾分鐘內不事聲張卻已排疊整齊。雖暫受委屈,卻確保人人看得清楚,只有領隊和翻譯可以自由走動,費老見后大為震驚,只見四周幾百只眼睛齊刷刷注目以待!他即飽蘸濃墨,凝神靜氣,酣暢淋漓地揮寫起來。——這一生動場景,是他歸蘇后告訴三子之雄的。
1980年10月,正值美國總統競選高潮,卡特來到紐約唐人街銀宮酒樓,對亞裔、華裔發表演講,表示對華人和中國的友好。他展示了一幅華人送他的落款“新我左筆”的行書立軸,全場頓起一片掌聲。照片登在《華僑日報》上,在美國畫壇極富影響的美籍畫家程及先生將此報剪下寄給了費老。
程及先生是費老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白鵝畫校的同學,無錫人,比費小5歲,過從甚密。自程去美后失去聯系,1972年程及夫婦回國省親觀光,在獅子林看到六幅風格獨特的行書,大加贊賞。當他得知這就是思念已久的老同學時,喜出望外,兩人終重逢言歡。
為抒發對祖國家鄉的情懷,程及創作了一幀巨幅長卷《春到江南圖》,請費老題字。費老除為此圖寫了“引首”幾個大字外,也滿懷激情在卷尾用整張六尺宣紙題寫了王維桃源行古詩,為其錦上添花。此畫與書,交相輝映,在美國展出后轟動了整個畫壇,受到美國藝術家的高評。于是,程先生邀請老同學訪美。
1984年春暖花開時節,年逾八十的費老只身飛赴美國。在美35天,會見老朋友,交流技藝,領略大都市風光,參觀畫展和眾多的博物館,又一次大開了眼界。他徜徉在藝術殿堂里,心中激起對藝術求新求變的浪花。

在美的50余位華裔華僑于紐約著名的東方畫廊聯合舉行歡迎費新我訪美茶會。會上旅美畫家媒體副刊主編朱光晨、程及等人對其書作給予高度評價,說他的書法作品猶如繪畫一樣有節奏、有旋律、有感情,其筆力流暢豪放而富有力量,其章法優美而極富畫意。“他的書法作品在中國既受藝術家贊賞,又受廣大群眾喜愛”“費新我的書法可以說是風行全中國”“他的書風在中國獨樹一幟”。
費新我向大家介紹了自己的藝術生涯,他的講話語言生動,見解精辟,寓于風趣,到會人士都表示得益殊深。會后即席揮毫。他在鋪好的紙上濡墨點了濃淡、大小、粗細數十點,接著一一加線成文。原來是神采動人的“點點滴滴墨,區區菲菲心”十個字。接著,他說:我用翰墨表達我的區區之心。這是到美國后受到啟發,才有此創意的,贏得在場藝術家的嘖嘖稱贊。
美國《華僑日報》《星島日報》《華語快報》《中報》等均作了詳細的追蹤報道。他并為一些華僑和有關協會、中國駐美機構、中國民航等單位留下許多墨跡。
回國后,他向各方人士大談感想,說這次訪美擴大了眼界,深感自己的書法還可以求新求變。也看到了我國的藝術品在國際上享有的盛譽,我們在藝術上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東搬西湊是沒有出息的。程及先生有一方印:我用我法,就是指在傳統的基礎上,要創出自己的路子。
1991年炎威未退,88歲高齡的費老應新加坡書法協會邀請,由原河南省書協主席,中國書協名譽主席張海先生陪同飛赴獅城,舉辦“費新我八八書展”。
此行受到了新加坡政府、藝術總會、文化學術協會、人民協會等的隆遇。有“世界書法大使”譽稱的陳聲桂主席是費的老朋友,他親自接待,全程陪同,給予最高禮遇。三家華文日報一齊發文報道,二家電視臺連續報道三次,引得人們爭相前來觀展。
第二天一早,書協秘書長告知:在內部預展中費老的作品已被認購38件,余下的9件作品肯定一開幕即定。費老的作品大受歡迎,平時的展覽當場只能售出一兩件。
費老白天參觀、拜訪、講學,晚上接待來訪者,一直處在興奮之中,晚上客人走后,還要在燈下記錄一天的行程(這是他幾十年來的習慣)。或許是天熱加勞累,他在睡前洗澡時一下摔倒了,疼得滿頭大汗,當夜請來醫生治療。第二天原定有講座,主辦方想取消,但他堅決不同意。只得由張海攙扶著,每講一段坐下休息一會,就這樣堅持完成了兩小時的演講。
當地高僧廣洽法師,是與畫家豐子愷同為弘一法師李叔同的高足,上世紀50年代豐先生曾代廣洽向費老請過一幅弘一法師的造像。因之,法師幾次來華都拜會過費老。這次費老一到就想去拜訪,但據報載,法師已住院多日。回國前費老執意要去一趟法師府上。一按門鈴,弟子告知巧在昨日出院,兩位老人終又相見,惜法師已說不多話,告退時依依不舍。
按照文化部的規定,費新我的展品不能出售,必須帶回。有人建議可當即寫些補進去,海關和有關方都不知道,既可獲得滿堂喝彩的好名聲,還有一筆可觀的收入。可費老覺得不妥。展覽一結束,除贈送主辦單位及有關部門數件之外,其余全部交由海關帶回。事后,在陳聲桂先生向江蘇省國畫院的致謝報告中提到:費老此行訪問十二分成功及備受推評,為國民外交作出極為重大的貢獻,本會謹此致予萬二分的謝意。至于費老人品清高,淡薄名利,尤其使本會同人受益良多。
訪問結束,在機場告別時,主人真誠邀請費老明年再來,他說:我的一方印是“人書未老”,當然還會來的。引得送行友人一陣惜別而又歡快的笑聲。
費新我的不少書作還被作為國家、政府各有關方面的禮品、贈品飛向世界各地,引起世人矚目。
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柏偉能,是北歐研究中國書畫的知名學者,他見到費老書法后情有獨鐘,曾三次來蘇州探訪,并不遺余力地向西方藝術家推介費新我書法。
1986年他第二次來時帶著瑞典電視臺攝影師,專訪時,費老滔滔不絕地講起了他的藝術和家庭,并欣然命筆,揮灑自如…… 又為柏偉能寫了“筆酣墨暢”四字,那大刀闊斧又游刃有余的書寫風度,以及手舞足蹈地解釋其中含意,都被一一錄進了鏡頭。
在柏偉能專著中,稱他收藏有一件出自費老手筆的杜甫絕句,“這件生機勃勃的作品集中體現了‘費體’的獨特風格,它優美淳厚、蘊藉含蓄,變化中求統一,對比中見和諧,結構上十分完美,一筆一畫,都包含著特定的視覺特征,處處呈現出對立統一的完善境界……欣賞費老的作品,能使人充分認識到書法線條的重要性,也就更加明白了書法為什么在中國成為最受歡迎的藝術。”據他分析:以左手艱澀、難駕馭而形成 “拙”的效果,竟然與法蘭西藝術中十分重要的美學概念Gaucherie(不善交際的,粗魯拙樸的)不謀而合,他以為費老對拙的追求,比其他人更為自覺和執著。最后還說: “八十年代是中國藝術史上一個充滿創造的時期,作為這個時期的書壇巨擘,費新我將同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杰出的藝術家一樣,被永遠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