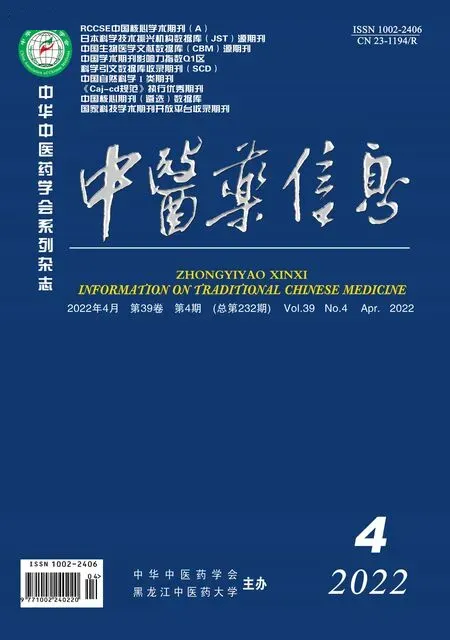呼吸訓練聯合咽三針對卒中早期吞咽障礙患者頦下肌群肌電活動的影響
宋琦,喬鑫,馮秋菊?
(1.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2. 中國人民解放軍93220部隊,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6)
卒中(stroke)又稱中風,多因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和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引起腦部動脈狹窄、閉塞或破裂,進而導致腦部血液循環突發性障礙。該病可能導致患者發生一次性或永久性腦功能障礙,并伴有其他功能障礙,如肢體偏癱、吞咽功能障礙等。調查顯示,隨著醫療技術的相對提升,卒中患者死亡風險大大降低,但其發病率和病死率仍舊呈現上升趨勢,且發病率隨年齡的增長有增加風險。近年來隨著年輕人生活作息和身心狀態的變化,卒中患者基數年齡在不斷降低,導致其成為一項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在經濟和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卒中患者預后效果偏低,復發率也相對較高,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生活負擔[1-3]。在其多種并發癥中,吞咽障礙是一種口腔、咽喉、食管等器官結構和(或)功能受損,導致患者進食異常的過程,不僅影響患者通過食物攝取營養物質,還會對患者正常生活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對卒中伴吞咽障礙的患者進行康復研究,在其吞咽功能發生障礙早期進行呼吸訓練聯合咽三針治療,探究此種方法對吞咽障礙的改善效果,以期為卒中康復治療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9年10月—2021年5月本院收治的109例卒中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抽簽法將109 例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55 例)和對照組(54 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病程、舒張壓、收縮壓和WST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本研究取得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2020-K037。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s)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s)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χ2/t值P值例數55 54性別(男/女)25/30 32/22 2.081 0.149年齡(歲)49.17±5.91 47.33±8.29 1.336 0.184體質量指數(kg/m2)18.05±0.17 18.10±0.21 1.367 1.640病程(d)12.94±9.51 15.62±7.40 0.174 0.104舒張壓(mm Hg)76.19±12.46 80.34±10.28 1.895 0.061收縮壓(mm Hg)119.08±7.52 121.50±6.91 1.749 0.083 WST評分(分)Ⅲ13 21 3.303 0.138Ⅳ22 15Ⅴ20 18
1.2 診斷標準
符合《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試行)》[4]對卒中的診斷標準,患者表現為肢體軟弱、偏身麻木、舌歪語謇、氣短乏力、心悸自汗、舌質暗淡、苔薄白或白膩、脈細緩或細澀。
符合《中國各類主要腦血管病診斷要點2019》[5]對腦卒中的診斷標準,患者表現為一側臉部、手臂或腿部突然感到無力,猝然昏撲、不省人事,并經過影像學檢查診斷為腦卒中。
符合《中國吞咽障礙評估與治療專家共識(2017年版)》[6]對吞咽障礙的診斷標準,患者表現為吞咽費力費時、食物滯留口腔內、流涎、進餐時嗆咳和呼吸短促,并經過吞咽造影確診為卒中后吞咽障礙。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上述診斷標準;②洼田飲水試驗(water swallow test,WST)Ⅲ~Ⅴ級的患者[7];③面頸部肌肉出現運動障礙的患者;④患者知情同意。
1.4 排除標準
①吞咽障礙既往史或口腔咽喉疾病史的患者;②面頸部肌肉萎縮史的患者;③精神疾病或研究期間意識不清、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④心、肺、肝、腎等組織器官功能障礙、惡性腫瘤、嚴重免疫疾病的患者。
1.5 剔除或脫落標準
①未能及時參與檢查或治療依從性差的患者;②研究期間發生其他腦血管疾病、二次卒中或去世的患者;③研究期間同為其他研究工作病例樣本的患者。
1.6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進行常規康復治療。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J20171021,規格:100 mg × 30 s,用于抗血小板凝集),1 次/d,第1 天嚼碎服用300 mg/次,第2 天及以后降至100 mg/次(整片服用);口服硫酸氫氯吡格雷片(賽諾菲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J20180029,規格:75 mg×28 s,用于抗血栓形成),75 mg/次,1 次/d;靜脈滴注馬來酸桂哌齊特(北京四環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20125,規格:2 mL∶80 mg,用于改善腦部微循環),2 mL/次,溶于500 mL 10%葡萄糖中,滴速100 mL/h,1 次/d。所有藥物持續治療4周。
對照組進行呼吸訓練(腹式呼吸、縮唇樣呼吸和主動循環呼吸訓練)。腹式呼吸訓練方式[8]:患者取坐位,緩慢呼吸,用鼻吸氣并吸住腹部,用口呼氣并收縮腹部肌肉,上提膈肌,每分鐘完成12~20 個呼吸,持續10 min 為1 組;縮唇樣呼吸訓練方式:患者用鼻深吸氣,將嘴縮成魚嘴狀呼氣,呼氣過程緩慢,約為吸氣時間2倍,持續10 min為1組;主動循環呼吸訓練方式:需要患者進行深呼吸并完成胸廓擴張運動,尤其是呼氣時需保持呵氣動作1~2 s,持續10 min為1組。每項訓練3組/d,5 d/周,共持續4周。
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進行咽三針治療。主穴選擇咽三針,即患者廉泉穴、廉泉穴左右旁開1.2 寸和下0.5 寸3 個穴位,配穴根據患者實際情況,有語言障礙者選擇通里穴,有流涎者選擇地倉穴和承漿穴,有偏癱者選擇曲池穴、外關穴、后溪穴、足三里、豐隆穴和俠溪穴,對選擇穴位進行常規消毒,使用華佗牌一次性使用無菌平柄針(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蘇械注準20162200970,型號:0.35 mm×40 mm),采用平補平瀉手法,對主穴向舌根部斜向上方向針刺,進針深度約為25~30 mm,刺激中等,快速捻轉10~15下,緩緩退出不留針,配穴采用常規針刺,留針30 min。所有所選穴位針刺完畢為1次,針灸治療1次/d,5 d/周,共持續4周。
1.7 觀察指標
1.7.1 標準吞咽功能評估量表
在治療前、治療2 周和4 周后,采用標準吞咽功能評估量表(standard swallowing function evaluation scale,SSA)對兩組患者分別進行吞咽功能檢測,共三步。第一步對患者進行初步評價,包括對現有意識、對頭、肢體和唇控制等方面評估,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別讓患者飲3次5 mL水和1次60 mL,對患者咽水時狀態進行評估,共18 項評估內容,第1、2 項采用4 級評分法將每項設置為1~4 分,第5、6、8、13、17、18 項采用3 級評分法將每項設置為1~3 分,其他10 項采用2 級評分法將每項設置為1~2 分,共18~46 分,得分越低患者吞咽障礙恢復越好。
1.7.2 表面肌電
在治療前、治療2 周和4 周后,使用加拿大Thought Technology 公司開發的H4A2L8 型號的表面肌電儀以及Biograph Infiniti Software 表面肌電圖分析軟件,對患者的表面肌電信號進行采集和分析,對其吞咽過程中頦下肌群(頦舌骨肌、二腹肌前腹和下頜舌骨肌)表面肌電圖(surface electromyography,sEMG)信號進行檢測,使用delsys 全無線表面肌電測試系統對數據進行處理。檢查前,檢查者啟動儀器開始預熱,并為患者進行檢查演示,待其理解后開始進行檢查;檢查時,患者取坐位,保持面部放松狀態,檢查者對頦下肌群部位皮膚進行消毒和去油污,將電極貼至所測肌群表面部位,記錄患者飲約5 mL 溫開水時吞咽動作的sEMG 信號最大振幅(最大肌電值)、平均振幅(平均肌電值)和吞咽時限(吞咽動作開始到結束的時間),測量3次后取平均值[7]。
1.7.3 不良反應
統計兩組患者在治療期間發生的不良反應情況,主要為睡眠質量、呼吸道反應和皮膚反應。如失眠、身體發熱、針灸部位皮膚紅腫瘙癢、發生醫院獲得性吸入性肺炎、支氣管痙攣等。
不良反應率(%)=不良反應例數/總例數×100%
1.8 臨床療效判定標準
治療4 周后,采用WST 對患者治療后吞咽障礙治療效果進行評估,評估時患者取坐位,飲30 mL 溫開水,根據患者臨床表現和等級劃分(Ⅰ級:1 次性將水咽下,且不嗆咳;Ⅱ級:需要2次或以上才能將水咽下,且不嗆咳;Ⅲ級:1 次性將水咽下,但有嗆咳;Ⅳ級:需要2 次或以上才能將水咽下,但有嗆咳;Ⅴ級:始終不能將水咽下頻繁嗆咳)將患者分為有效(吞咽障礙消失,且WST 試驗評級為Ⅰ)、顯效(吞咽障礙明顯改善,且WST 試驗評級為Ⅱ)和無效(吞咽障礙無明顯改變,且WST試驗評級仍保持在Ⅲ級及以上)。
總有效率(%)=(有效例數+顯效例數)/總例數×100%
1.9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1.0 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或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檢驗,不滿足球形檢驗使用Greenhouse-Geisser進行校正;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92.73%)高于對照組(81.48%),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患者吞咽障礙改善情況比較
治療前,兩組SSA 評分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2周和4周后,觀察組SSA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兩組SSA 評分在治療2 周和4 周后均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 1 640.472,P<0.05),觀察組SSA評分與對照組在治療前、治療2周和4周后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82.680,P<0.05),時間和干預因素存在交互作用(F= 23.063,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SSA評分比較(±s,分)

表3 兩組患者SSA評分比較(±s,分)
注:與治療前相比,*P <0.05;與治療2周后相比,#P <0.05。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值P值例數55 54治療前39.43±3.21 39.78±3.46 0.551 0.583治療2周后24.91±1.70*29.59±1.46*15.351 0.000治療4周后20.51±1.38*#22.24±1.96*#5.328 0.000
2.3 兩組患者頦下肌群肌電活動情況比較
治療前,兩組最大振幅和平均振幅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2 周和4 周后,觀察組最大振幅和平均振幅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兩組最大振幅和平均振幅在治療2周和4周后均上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分別為(F= 843.147,P<0.05)和(F=106.983,P<0.05)],觀察組最大振幅和平均振幅與對照組在治療前、治療2周和4周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分別為(F= 249.386,P<0.05)和(F= 57.508,P<0.05)],時間和干預因素存在交互作用[(F=73.356,P<0.05)和(F= 12.995,P<0.05)]。治療前,兩組吞咽時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2 周和4 周后,觀察組吞咽時限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吞咽時限在治療2 周和4 周后均下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 1746.613,P<0.05),觀察組吞咽時限與對照組在治療前、治療2周和4周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210.883,P<0.05),時間和干預因素存在交互作用(F=77.419,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頦下肌群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表4 兩組患者頦下肌群肌電活動情況比較(±s)
注:與治療前相比,*P <0.05;與治療2周后相比,#P <0.05。
?
2.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情況比較
觀察組不良反應率(18.18%)和對照組(20.37%)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中醫學認為,經絡和腧穴與人體特定部位存在著一定聯系,使用針刺療法可以調整營衛氣血和調和氣血,從而能有效防治疾病。腧穴位于體表,常作為針法治療的刺激點與反應點,鄭曉珊等[9]指出,舌針刺激舌體相關穴位能幫助舌體局部通暢氣血,從而恢復舌體功能。廉泉穴是任脈、陰維脈交會穴,位于人體的頸部,覃亮等[10]發現,針刺該穴可利咽活絡,幫助麻痹遲鈍的舌體運動相關神經運動纖維產生興奮,恢復舌咽部恢復隨意運動,從而增加卒中患者恢復吞咽功能的幾率。研究發現,對廉泉穴及周圍穴位進行刺激,即咽三針,對治療吞咽障礙也具有較好的治療效果[11]。周文姬等[12]采用吞咽造影技術對咽三針治療吞咽障礙進行評價,發現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得到明顯改善,推測廉泉穴具有治療吞咽困難的作用,且針灸治療成本較低,可減輕卒中患者經濟負擔。此外,在治療卒中后吞咽障礙時,廉泉穴還可與其他穴位配伍,謝巒等[13]指出與舌頸部的腧穴配伍能增加吞咽功能的恢復速度,與肢體遠端腧穴配伍還有對全身起到協調陰陽、調神導氣的效果。因此,咽三針和配穴配伍能有效改善吞咽障礙患者臨床癥狀。
GUTIERREZ等[14]指出,阿韋利斯綜合征、杰克遜綜合征和維拉特綜合征等吞咽有障礙的綜合征可能與舌咽神經(glossopharyngeal nerve)、舌下神經(hypoglossal nerve)和迷走神經(vagus nerve)等神經有關,認為此類神經功能異常可能是導致患者表現出吞咽障礙的原因之一。舌咽神經屬于第9對腦神經,主要控制莖突咽肌和腮腺體,部分味蕾和收集來自耳部后部的感覺;舌下神經是由軀體運動纖維組成,可支配舌肌運動。黃小麗[15]等指出,對廉泉穴進行刺激,能刺激舌根深部的舌咽神經和舌下神經,從而刺激吞咽神經核,促進卒中后吞咽障礙患者恢復舌體上運動神經元功能,增強舌體的運動能力。迷走神經與舌咽神經并行,為第10 對腦神經,是腦神經中最長,分布最廣的一對神經,其最主要的分支為喉上神經和喉返神經,當雙側喉上神經損傷時,可能引起吞咽障礙[16]。另一方面,卒中患者因腦細胞供血不足,導致神經功能異常,可能降低機體肌群活性,如增加肌群肌電活動的閾值,需要比正常狀態下更大的電刺激才能做出反射,或電信號在傳導過程中因神經損傷而傳遞異常,而肌群活力降低是此類現象的表現形式之一[17]。吞咽障礙患者因舌咽神經、舌下神經或迷走神經異常,可能出現頦下肌群活動性低的情況。本研究檢測治療前卒中后吞咽患者頦下肌群表面肌電活動,發現活動水平較低,但觀察組隨著針灸治療的進行,活動性逐漸升高,推測針灸可能通過對舌咽神經、舌下神經和迷走神經的刺激,從而激活吞咽相關肌群。劉勇等[18]指出,強化呼吸訓練也能幫助卒中患者增強呼吸相關肌和吞咽相關肌群的協調收縮,幫助促進舌體有效上抬,并能吞咽壓力增加,減少了食物殘留。此外,黃小麗等[15]指出對廉泉穴及相關配穴進行刺激,可直接對中斷舌咽神經和迷走神經的異常吞咽反射弧,通過活血化瘀和通氣導氣的方式,對這些反射弧進行重塑,從而改善卒中患者腦細胞血氧供給不足的現象,致使神經細胞再生,增加肌群活動性,恢復吞咽功能。因此,可認為咽三針能通過幫助神經功能恢復從而間接改善吞咽障礙和頦下肌群活動性。但對于肌群深層活動如何被針灸治療影響,本研究使用的sEMG并不能觀察到[19],因此,進一步將通過實驗室動物幫助了解針灸對卒中后吞咽障礙者深層肌群的影響。
綜上所述,卒中后發生吞咽障礙的患者在早期進行呼吸訓練和咽三針治療,能有效改善吞咽障礙,并增強頦下肌群肌電活動水平,縮短吞咽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