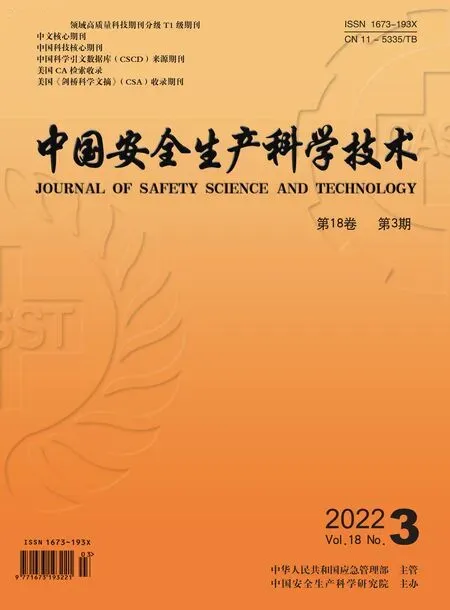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的U型影響
——一個雙調節模型*
程戀軍,姜曉藝
(1.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公共管理與法學院,遼寧 阜新 123000;2.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葫蘆島 125105)
0 引言
如何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以降低人員傷亡和經濟財產損失,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據統計,2020年全國生產安全事故數與死亡人數較2019年分別下降15.5%和8.3%[1],安全形勢總體趨于平穩,但當前我國安全生產正處于“爬坡過坎期”,風險因素的增加仍預示著安全事故可能不時發生。因此,如何有效減少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仍是亟需解決的問題。研究表明,員工的不安全行為是導致生產安全事故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2],減少員工的不安全行為,對有效降低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辱虐管理等帶有負面特征的領導行為在安全管理領域得到了快速發展,諸多研究也證實了辱虐管理在安全領域的負面作用。例如,王丹[3]以306名礦工為研究對象,第1次驗證了辱虐管理與礦工不安全行為之間的正向關系。盡管辱虐管理在安全領域的負面作用已經得到廣泛共識,但根據Lee等[4]的研究發現,辱虐管理并不總是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適度的辱虐管理會提高員工的創造力。而在安全領域,現有研究主要關注了辱虐管理對其結果變量的線性影響,而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曲線作用。因此,辱虐管理與員工的不安全行為之間是否也存在一種非線性關系,即適度的辱虐管理是否會減少員工的不安全行為,使二者之間呈現U型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
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正念與領導-成員交換作為調節變量,應用層次回歸方法實證研究辱虐管理與員工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以及正念、領導-成員交換在二者之間的調節作用,旨在深化對辱虐管理的認知,為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提供新思路。
1 文獻述評與研究假設
1.1 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
辱虐管理是指下屬所感知到的主管的持續性敵意行為(包括言語與非言語行為),但不包括身體接觸[5]。其定義包含以下3層含義:首先,辱虐管理是指下屬對領導行為的主觀評價,即不同個體特質和價值觀的員工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對同一辱虐行為會有不同的評價[6],換言之,不同下屬在同一管理行為是否屬于辱虐管理的認知上存在差異;其次,辱虐管理是一種持續性的行為[6],若領導因為家庭糾紛等特殊原因產生負面情緒,在工作中對下屬進行辱虐,其因并非領導持續表現出的行為,因而不屬于辱虐管理的范疇;最后,辱虐管理是指領導發出行為的本身,而并非做出此行為的意義或目標。
不安全行為是指在工作場所中曾經引發過安全事故或可能引發安全事故的行為。相關研究表明,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3]。但是,本文認為辱虐管理與員工不安全行為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U型的曲線關系。一方面,破壞性領導理論指出,破壞性的領導行為并非總是會帶來消極的結果,在某些特定環境下也可能產生積極效應。另一方面,激活理論指出,員工在適度的激活水平下能夠優化自身資源,進而增強工作投入,提高績效[7]。相反,過低或過高的激活水平均不利于員工達到最佳工作狀態。Harris等[8]認為,辱虐管理是工作場所中重要的激活源之一。因此,基于激活理論,認為適度的辱虐管理會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具體而言,作為工作場所中重要的激活源,適度的辱虐管理有利于員工優化心理狀態與個體資源,提高工作熱情與工作投入,使員工在工作中能夠按照安全規程進行風險操作,并保持工作專注度以積極面對工作中產生的突發情況,進而有效避免心智游移與無理由試錯等危險狀態與行為,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但當辱虐管理水平較低時,員工所受到的激活水平也相對較低,進而無法有效激發個體資源與工作積極性,使員工無法擁有良好的心理狀態與足夠的資源去面對安全風險與突發事件,進而導致員工產生慣性解決的依賴,不利于安全行為的產生。而當辱虐管理水平較高時,會嚴重影響員工的認知與情緒調整能力,造成個體安全感下降,使員工認為領導并不認可自身在工作中的努力付出及改變,進而減少有利于安全工作的行為并恢復到原有慣性工作的依賴,增加了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綜上,提出假設:
H1: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有U型影響。即適度的辱虐管理會降低員工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
1.2 正念的調節作用
在管理學領域,正念是指一種對當前內外部刺激的高度專注和坦然接納,其既可以表示個體的心理狀態,又可表示為一種積極的個體特質[9]。Martinko等[10]認為,個體特質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個體對相同的領導行為有不同的感知。而正念作為一種與自我調節密切相關的個體特質,可以對個體行為進行有效調節,極大地減少因內外部刺激而產生的消極后果[11]。基于此,認為正念會調節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
首先,資源保存理論指出,資源越充足的個體越不容易遭受損失資源的攻擊,且更容易獲得資源。而正念作為一種積極的人格特質,其水平差異會影響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高正念水平的員工擁有更多的個體資源來面對外部壓力與刺激源帶來的干擾,在面對適度的辱虐管理時,能夠擁有充足的資源與良好的心態去面對領導的辱虐行為,積極分析領導辱虐行為中對自身的不滿與批評,并及時改正自身的工作缺陷。因此,高水平正念的員工往往會將適度的辱虐管理視為領導對自身的提醒與鞭策,認為領導對自身“高標準、嚴要求”,有利于自身工作水平的提高,進而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而當辱虐管理水平超過其自身資源的承受極限時,其資源平衡會被打破,導致員工必須分配資源以應對領導過度的辱虐行為,進而不利于安全工作的進行。相反,低水平正念的員工沒有足夠的資源以面對外界壓力與刺激,更容易遭受資源損失的威脅。因此,在面對領導辱虐管理時,低水平正念的員工為避免資源的過度消耗,往往會采用沉默、回避等方法應對領導的辱虐行為以避免陷入資源“損失螺旋”,進而抑制工作中的資源投入,提高了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
其次,正念強調專注于當下,減少對當前工作無關的思考,并同時強調對內外部刺激進行無批判的接納[12]。具體而言,高正念水平的員工能夠專注于當下的工作任務,提高工作時的專注度,減少外部刺激對工作的干擾與分散。因此,在適度水平的辱虐管理下,高正念的員工能夠更加坦然地接受領導的辱虐行為,而不會將注意力轉移到領導為何對自己進行辱虐的原因上,這有助于員工在辱虐管理與自身感受間建立更大的緩沖空間,進而有足夠的資源與精力完成工作,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而根據“過猶不及”效應[13],當領導的辱虐行為超過員工個體資源與心理狀態所承受的范圍時,其負面作用會超過積極效應,導致員工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增加。相反,低水平正念的員工并不會將注意力專注于當下,且不會坦然接納領導的辱虐行為。因此,在面對領導的辱虐管理時,其個體資源與心理狀態受到沖擊,進而無法將注意力專注于工作之中,導致在工作時分散工作專注度,提高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綜上,提出假設:
CSS縮寫性質屬于一種專用的性質名,其可以完全替代多個相關性質進行集合。例如,頂部間隙、右側間隙、左側間隙、底部間隙的性質的縮寫都可用間隙性質(padding property)來表示。
H2:正念調節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只在高正念水平下存在。
1.3 領導-成員交換的調節作用
領導-成員交換是指由于資源與時間的有限性,領導對不同下屬投入的資源與時間不同,進而發展出不同的關系質量[14]。已有研究表明,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質量會對員工的態度及行為產生影響[15]。社會交換理論指出,當員工能夠感知領導對自身的鼓勵、關心與欣賞時,往往會給予組織更多的積極回饋。員工通過高質量的領導-成員交換,可獲得更多支持與鼓勵、增進溝通并減少誤解,進而改變工作態度與行為;而在低質量的領導-成員交換情形下,員工會盡量避免與領導進行溝通,并將與領導溝通視為一種負擔[16]。
具體來說,擁有高質量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員工會與領導進行更多的交流與溝通,并會得到更多來自領導的支持與鼓勵。因此,作為交換,在面對適度的辱虐管理時,擁有高質量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員工更愿意相信領導的辱虐管理是對自身行為問題的糾正與鞭策,進而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上級領導的辱虐管理,努力分析遭受辱虐管理的原因,改正自身缺陷,進而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而根據“過猶不及”效應[13],當辱虐管理水平超過自身承受極限時,員工會分散自身資源以應對過度的辱虐管理,進而無法擁有更多的資源去糾正自身工作存在的不足,使辱虐管理帶來的消極效應超過積極效應,提高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相反,低質量的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員工與領導間的溝通和交流不足,得不到足夠的鼓勵與支持。因此,作為交換,在面對領導的辱虐管理時,員工并不會將領導的辱虐管理視作對自身的糾正與鞭策,而是將其視為領導對自身工作的否定與不認可,使員工將自身資源與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應對領導的辱虐管理上來而減少了安全工作投入,進而加深了辱虐管理的負向效應。綜上,提出假設:
H3:領導-成員交換調節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只在高質量領導-成員交換關系下存在。
研究的理論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假設模型Fig.1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研究以高危行業企業員工作為調查對象。高危行業是指危險系數較高,事故發生率較高,財產損失規模大,且事故發生后短時間內無法恢復的行業。由于其生產作業的特殊性,極易對參加生產過程的員工造成傷害。因此,相關企業更需要注重員工工作中不安全行為的產生,以促進生產安全。采用現場發放—回收與網絡在線填寫2種方式對遼寧、河北2省11家高危行業企業進行問卷調研。現場發放—回收方式在遼寧省6家高危行業企業進行,在征得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同意的情況下,利用午休時間在每家企業隨機抽取30名員工進行問卷填寫;網絡在線填寫方式在河北省5家高危行業企業進行;在征得人力資源部門同意后,通過隨機抽樣方式在每家企業隨機抽取30名員工進行填寫。
調研過程歷時2個月,共發放問卷330份,回收296份,回收率為89.7%。剔除掉不完整、無效問卷后,共得到有效樣本242份,有效回收率為73.3%。樣本特征方面,性別以男性為主,占比90.5%;年齡以26~35歲為主,占比36.4%;受教育程度以大專為主,占比34.3%;職位以普通員工為主,占比85.1%;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占比63.2%。
2.2 量表選擇
2.2.1 辱虐管理量表
采用Harris等[17]修訂的辱虐管理測量量表。量表共包含“我的主管經常對我保持沉默”等6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法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員工所遭受的辱虐管理程度越高。
采用Brown等[9]開發的正念量表。量表共包含“我可能正在經歷某種情緒,但直到一段時間后才意識到它”等15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法計分。由于該量表為反向量表,因此,回收問卷后將各題項進行反向計分并納入研究,分數越高,表明員工正念越強。
2.2.3 領導-成員交換量表
采用Graen等[14]編制的領導-成員交換量表。量表共包含“我的領導會認識到我的潛力”等7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法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員工的領導-成員交換關系質量越高。
2.2.4 不安全行為量表
采用Garcia等[18]開發的量表,其中18~25題為不安全行為量表。量表共包含“我沒有關于安全工作的信息”等8個題項。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法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員工在工作中產生不安全行為的幾率越高。
3 數據檢驗與分析
3.1 區分效度與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應用Amos24.0對辱虐管理、正念、領導-成員交換、不安全行為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見表1。其中,四因子模型適配指標(χ2/df=1.735,TLI=0.953,CFI=0.956,SRMR=0.049,RMSEA=0.055)均顯著優于其他備選模型,表明本文研究中的4個變量屬于不同的構念,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良好,適合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Table 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由于研究各變量均屬于個體層面變量,采用自我報告法進行問卷收據,可能出現共同方法偏差問題。因此,采用不可測量潛在方法因子效應控制法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由表2可知,加入公共因子(CMV)后,CMV模型擬合指數較假設四因子模型并未得到顯著改善(Δχ2/df=0.373,ΔTLI=0.024,ΔCFI=0.024,ΔSRMR=0.023,ΔRMSEA=0.016),因此,本文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適合進行下一步研究。
3.2 相關性分析
應用SPSS25.0對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2。結果表明,辱虐管理與領導-成員交換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r=-0.283,顯著性概率值p<0.01),結果初步驗證了研究假設,適合進行下一步分析。

表2 相關性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3.3 假設檢驗
3.3.1 主效應檢驗
檢驗假設H1提出的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的U型影響。為減少模型中非線性關系帶來的多重共線性影響,研究將辱虐管理與辱虐管理的平方項預先進行均值中心化處理,層次回歸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模型2與模型3在控制了5項控制變量后,發現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為正(b=0.584,P<0.001);辱虐管理的平方項對員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也為正(b=0.214,P<0.001),說明辱虐管理與員工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存在,假設H1成立。

表3 層次回歸結果Table 3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3.3.2 調節效應檢驗
檢驗假設H2提出的正念在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同樣,為避免非線性關系帶來的多重共線性影響,研究將正念與兩交互項預先進行均值中心化處理,層次回歸結果見表3中模型4、模型5、模型6。由模型6可知,正念與辱虐管理平方項的交互項對不安全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b=0.123,P<0.01),說明正念在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存在,假設H2成立。
同理,應用上述方法檢驗假設H3,結果見表3中模型7、模型8、模型9。由模型9可知,領導-成員交換與辱虐管理平方項的交互項對不安全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b=0.114,P<0.05),說明領導-成員交換調節了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U型關系,假設H3成立。
為更好地展示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以及正念和領導-成員交換的調節作用,利用回歸系數,繪制不同辱虐管理水平下不安全行為的變化,以及不同正念水平與不同領導-成員交換水平下,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關系的變化,如圖2~4所示。由圖2可知,當辱虐管理水平較低時,隨著辱虐管理水平的提高,員工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逐漸降低;而當辱虐管理水平較高時,隨著辱虐管理水平的提高,員工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幾率迅速上升。當辱虐管理水平達到均值(3.612)時,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的影響達到最低,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1。由圖3所知,低正念水平下,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幾乎呈正向的直線關系;而在高正念水平下,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便呈現U型關系,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2。由圖4可知,低質量領導-成員交換關系下,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幾乎呈正向的直線關系;而在高質量領導-成員交換關系下,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呈現明顯的U型關系,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3。

圖2 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的U型關系Fig.2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management and unsafe behavior

圖3 正念對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的調節作用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abusive management and unsafe behavior

圖4 領導-成員交換對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的調節作用Fig.4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on abusive management and unsafe behavior
4 討論
4.1 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
研究證實,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有U型影響(b=0.214,P<0.001),適度的辱虐管理會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研究結果回應了相關學者對管理學中復雜變量曲線關系研究的呼喚,并進一步探究了辱虐管理等破壞性領導行為可能存在的積極影響。鄭伯塤[19]認為華人組織領導行為往往蘊含了“立威”成分,上級可能出于確立自身權威,避免破壞群體和諧、導致下屬競爭等因素的考慮,表現出專權作風、貶損下屬能力等辱虐管理行為,這種“立威”成分往往指向任務而非個體攻擊,有利于降低個體不安全行為;Rodwell等[20]也認為辱虐管理會包含指向任務、指向個體和獨立3種成分。而隨著辱虐程度的增加,個體消極情緒體驗會進一步增強,對辱虐管理的感知也會由指向任務逐漸轉為指向個體被攻擊,從而導致了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的U型關系。因此,組織應重視高集體主義背景下經常存在的辱虐管理行為,通過定期培訓、日常監管等方式提高實施辱虐管理領導的控制力,使其在工作中能夠有效把握自身辱虐行為的“度”,充分發揮辱虐管理的積極作用,避免過低或過高的辱虐管理水平,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4.2 正念的調節作用
研究證實,正念調節了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為更準確理解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的差異化作用機制澄清了邊界,并進一步豐富了正念作為邊界條件的適用范圍。在實踐中,組織除了應把控好各層次領導辱虐管理的程度之外,還應著重關注員工的正念水平。組織應通過正念減壓法等正念訓練提高員工的正念水平。此外,還應通過組織培訓、領導鼓勵等方式讓員工意識到正念的重要性,進而使員工自身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進行自我正念訓練,提高正念水平,以更好地發揮辱虐管理的積極作用,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4.3 領導-成員交換的調節作用
研究證實,領導-成員交換調節了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進一步理清了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存在U型影響的差異化機理,豐富了二者之間關系的邊界作用條件。因此,組織應促使管理者給予下屬更多的支持與鼓勵,定期與下屬進行溝通與交流,并將領導-成員交換關系建設能力作為管理者考核的一部分,進而提高上下級關系的質量,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5 結論
1)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有U型影響。適度的辱虐管理能夠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過低或過高的辱虐管理均不利于安全工作。
2)正念與領導-成員交換均調節了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之間的U型關系。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的U型作用只有在高正念或高領導-成員交換水平下存在。
3)研究結論為如何減少員工不安全行為的發生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本文僅考慮辱虐管理與不安全行為的整體概念,尚未對其具體類型進行深入討論。因此,在未來研究中可針對不同類型的辱虐管理對應不同類型的不安全行為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明晰辱虐管理對不安全行為的作用機制,以期更好地減少不安全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