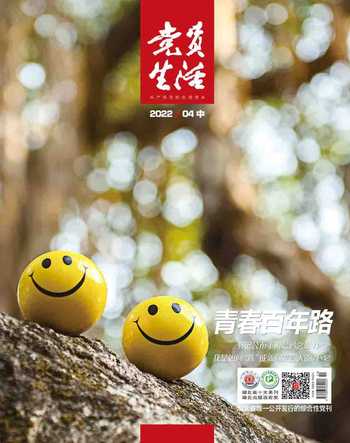譯書為何是件“苦差事”
陳雪


2022年年初,一個“天才兒子”的故事刷屏了——身心多難的金曉宇通過自學,十年翻譯了22本書。通過媒體報道,于困苦中自強的譯者金曉宇終于被看見、被聆聽,甚至被稱為“天才翻譯家”。但現實情況是,金曉宇至今仍難以靠譯書稿酬謀生。他自述:“翻譯的稿費很低,一千字五六十塊錢。這些年家里的開銷主要是靠我爸媽的退休工資。”
職業譯者低稿酬、學術翻譯“無工分”——這是當代圖書翻譯的基本現狀。
80元/千字的譯書“票友”
2021年3月,某出版機構招募譯者,明確標明翻譯稿酬為80元/千字,隨后有人給原作者寫信“投訴”,指責中國出版方“壓榨譯者”。出版機構編輯隨后在社交媒體上喊冤:80元/千字雖然不高,比起其他工作的報酬可以說很低,“但請考慮下國內這類圖書的實際收益”“我們目前已經收到26份此書的試譯稿”。
譯者和出版方雙雙叫苦不迭,起碼指出了一個事實:千字五十至百余元的譯書稿酬是業內多年來的普遍標準。按此標準計算:一本10萬字的書,80元/千字的翻譯費,稿酬稅前8000元,網友調侃“扣稅后只夠買臺手機”。其實大多數譯者每天基本上只能譯兩三千字,一本10萬字的書起碼耗時一個多月。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長董風云一語道出了譯書群體的基本面貌:國內就算是“天花板”級的譯者,也很難用譯書這件事來養活自己,“目前譯者的主力軍還是業余愛好者、‘票友’”。
商務印書館編輯李婷婷分析,翻譯稿費一般來說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原因有很多,圖書的利潤不高是主要原因。據了解,一本印數只有3000冊的圖書,收回成本已經很難,譯稿費自然也在成本范圍內。另一個原因則是譯者的可替代性越來越高,隨著機器翻譯技術的進步和人們語言能力的提高,很多通俗讀物、實用性文件翻譯均可用機器替代或輔助。多種因素導致了譯書很難走上職業化道路。
董風云介紹,目前出版領域翻譯稿酬計算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按字數一次性支付稿酬,一本書大致幾萬元;另一種是版稅制度,與銷量緊密相關,通常在6%~10%不等。但以大多數人文社科書的銷量,市場回報甚至不及一次性稿酬高。
2021年10月,《百年孤獨》中文版(南海出版公司版)銷量累計破1000萬冊,可謂現象級暢銷書。據了解,該書譯者北京大學副教授范曄當初簽訂的也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說,后續銷量如何與譯者無關。范曄透露:“據我所知,現在能拿版稅的譯者很少。”
一份難計回報的“良心活”
具有較高門檻的學術及嚴肅文學翻譯是另一個議題。
2021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聶敏里及其團隊耗時十年翻譯出版了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這套書共8冊300余萬字,實現了國內幾代學者的夙愿,受到了學界一致好評,并入選了《中華讀書報》“2021年度不容錯過的20種歷史好書”。在外界看來,這項翻譯活動可謂“功德圓滿”,但由于譯著不受重視,十年譯書均不計入學者工作量。
聶敏里說,譯著在職稱評審、科研獎勵、工作量考核等方面都不被計算。所以,翻譯基本上是一個“良心活”,譯者憑著自己的學術責任感來做,所追求的是知識傳播推動社會進步的效果,但所獲得的只是學術界的口碑。
“用愛發電”“費力不討好”“良心活”“為他人作嫁衣”……在學術界,翻譯成果不受重視漸成“不足為外人道”的老話題。于是,學術翻譯出現了“平行宇宙”:一面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等為代表的譯介行為被文化界高度認可;另一面,回報較少的學術翻譯越來越純化為一種學術和文化上的公益行為、利他行為,同時還要接受讀者對翻譯質量的質疑。
“你鼓勵年輕人來做文學翻譯,是一個非常不負責的行為。”范曄清楚地記得一位友人對他說的這句話,所指正是譯書這種“苦差事”的困境。然而,就連范曄自己也無法拒絕文學翻譯對自己的“召喚”。去年,他耗時七八年翻譯的《三只憂傷的老虎》正式出版,這部小說被譽為拉美的《尤利西斯》。范曄說這次翻譯對自己來說是“一次空前挑戰”,書中有很多古巴特色的西班牙語,結構復雜、文體豐富。范曄說:“最初想得很簡單,就是看到一些好的東西特別想跟人分享。”
讓譯者不再“隱身”
北京大學翻譯學者章文認為,雖然譯著在某種意義上是模仿,但不應該遮蔽翻譯行為中巨大的創造性。事實上,所有的學術成果都是對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創造的結合,都植根于前人已經織就的巨大互文性網絡,在這一點上,翻譯與寫作并無本質區別。
我國歷史上曾出現三次翻譯高潮,譯者一直是文化的“擺渡人”,經歷了從“舌人”“通事”到今天“翻譯家”的地位變遷,并在嚴復、梁啟超、魯迅等一代代學人思想家的理論及實踐中得到確認。梁啟超曾言“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為中國革命引進了理論指南,翻譯的價值無須贅言。章文認為,“翻譯低于原著”是過于簡單粗暴的價值判斷,需“一事一議”,具體評估特定譯作的價值。
為了讓人們看見譯者群體、認識嚴肅翻譯,讓譯者不再“隱身”,學者們普遍認為,設立一些資助、獎勵是目前比較現實可行的方法。去年,圖書品牌甲骨文和單向街公益基金會聯合發起了“雅努斯翻譯資助計劃”,希望資助在文學和學術領域有突出貢獻和公共影響力的杰出譯者和青年譯者。范曄認為:“這樣的獎項在精神上的鼓勵意義更大一些,可以體現出對翻譯價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