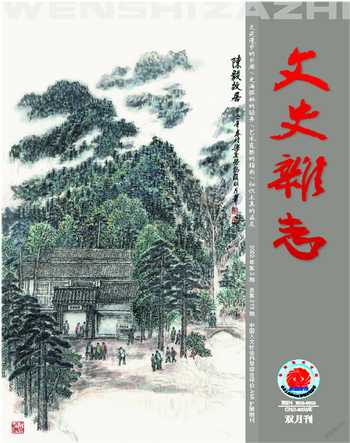他者視角下的國共經濟博弈探析
許關喜



摘 要:哈里遜·福爾曼《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因其客觀、詳實記錄了中共在陜甘寧邊區根據地開辟和發展以及政權建設、民主建設等相關史料而被關注、征引;但通過學術梳理,仍感有被忽略之處。其實《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涉及有關國共經濟博弈的相關史料,已經說明了國共經濟博弈演進過程中的實質與內在邏輯。
關鍵詞:他者視角;延安時期;國共經濟博弈;內循環;常態
一、研究現狀
哈里遜·福爾曼(1898—1978,又譯哈里森·福爾曼、哈里森·福曼),美籍作家、新聞記者,1930年曾以航空公司代表身份首訪中國。全民族抗戰初期,他訪問過賀龍等中共高級將領,后供職于《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時報》《泰晤士報》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等多家傳媒機構。
在中國人民全民族抗戰的關鍵時刻,蔣氏當局在與日本侵略者的“政治默契”下“聯手”對延安形成的雙重“封鎖”,與陜甘寧政權力量的逐步壯大所造就的“錯位”格局,引發了以哈里遜·福爾曼為首的一眾國際媒體人對中共濃厚的興趣。[1]
1944年2月,哈里遜·福爾曼同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岡瑟·斯坦因等10名外國記者一道聯名上書蔣氏當局,再次表達赴延安采訪的正當訴求。“在多方的壓力下,國民黨終于同意了外國記者的延安之行,但采取了新的措施來限制記者團的組成。”[2]自1944年5月17日起,哈里遜·福爾曼、趙超構等一行21人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名義赴西北等地開展了為期六個月的實地考察。[3]此次訪延之行參觀團成員成果頗豐,《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別名《北行漫記》)一書即出自哈里遜·福爾曼紀實報道。該書共分為“邊區”(二十二章)、“前線”(七章)兩部,涉及陜甘寧、晉綏、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開辟和發展以及政權建設、民主建設等相關史料。
通過學術梳理,當前學界關注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以人物與通訊報道研究為切入視角,對哈里遜·福爾曼在華的新聞活動進行“全景式”敘事與回顧;二是以國共輿論博弈為視角,將哈里遜·福爾曼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核心成員“主動介入”國共雙方輿論“宣傳與反宣傳”的活動進行論述。就前人研究成果來看,仍有值得深入探析之處。一是對能與《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起到互相印證的《哈里遜·福爾曼的攝影集》紀實圖片資料(哈里遜·福爾曼訪延期間拍攝)研究不足;二是“日本人民解放聯盟”一章中記載了該聯盟抗戰期間日籍人士在華反戰最為詳盡的史料,亦為相關研究留下新視角。故本文以他者視角為切入點,對國共在抗戰后期經濟領域的博弈作進一步探析。
二、《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
他者視角下的國共經濟博弈
(一)國統區“克難坡”式經濟實踐
在蔣氏的“精心”籌劃下,哈里遜·福爾曼一行人自作別首站西安后,即轉道繞行至抗日戰爭第二戰區總部、山西戰時省城——克難坡。此舉表面在言中共及其所轄第18集團軍隸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節制,實則是欲借閻錫山在克難坡的“革命競賽”來“沖淡中外記者對邊區的印象”[4]。閻錫山作為民國“派系”政治中的重要構成,明面上“遵從”蔣氏為“共主”,暗下卻在“保晉”的“生存邏輯”下積極謀求在蔣氏與中共之間達到某種平衡。中外媒體到訪于閻氏而言確實是強化“新經濟制度”和“兵農合作制”外宣的絕佳時機。同蔣氏及其當局多數官員逢“共”必反的做派不同,隔岸觀“共”的閻氏能夠客觀看待并積極效仿中共的某些優點。為使中共不能“煽惑”群眾,他提出了諸如“改進自身行政工作”“健全民眾組織,改善民眾生活”等舉措,以期同中共“革命競賽”。閻氏遂自臨時省城克難坡發起面向全省的“新經濟制度”和“兵農合作制”。
1.家長式的“新經濟制度”
1944年5月26日至31日,哈里遜·福爾曼所在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到訪克難坡,先后參觀克難坡電燈廠、平價購銷處等地。[5]在隨后召開的座談會以及公宴上,閻數次闡述“新經濟制度”理念及其實踐路徑。
閻認為當時社會經濟制度下“勞動的非產生性”和“分配的非勞動性”構成了群體和區域間無休止的矛盾,根源可歸結為兩點,“其一是以金屬為基礎的貨幣”,其結果是人的勞動不是為了商品,而是為了金銀。產品愈多則物價愈低賤,加之“金銀便于儲藏,其本身也可以用于投機”,通脹、失業等社會問題由此派生。“其二是資本的私有”,迫使無產勞動者依靠別人的資本來生產,從而產生勞動力的剝削。[6]
針對上述問題,閻提出兩項對策,一是模仿中共“合作券制度”發行“物產證券”,即使用“合作券”(晉鈔信用掃地后,產生的一種變相紙幣)替代以金屬為基礎的貨幣,將“物產證券”作為民眾參與勞動換取生活物質的“中介”,以期消滅資本剝削與增殖;二是用“按勞分配”替代“資本私有”所造成的分配不均的問題,意圖“(消除)資產階級和商人……自由貿易和私人商業也不準存在”。[7]他同時強調“強迫勞動”作為其實踐內容,“拒絕勞動就要受懲罰,他們必須集體工作,而且必須互相監督”[8]。顯然,閻氏的經濟制度包含了很大的軍事組織成分。
哈里遜·福爾曼坦言因時程有限,“新經濟制度”在克難坡之外地域實施情況以及是否接納該項政策,不得而知。若以“在克難坡所看到的這些穿著整齊、營養充足、得到滿足的人民可作標準的話”[9],“閻將軍家長式”“很像烏托邦”的“新經濟制度”運行的還算良好,但斷言“新經濟制度”的成敗為時過早。
2.強制推行“兵農合作制”
“兵農合作制”亦稱“兵農合一”。1942年豫省旱蝗兩災接至,民眾饑荒波及晉、陜等地。次年,晉省糧食供應緊缺,軍隊逃匿人員劇增。為化解兵源和糧食供給難題,閻氏遂推行“兵農合作制”,其要點是同村役齡男子每三人編入一“兵農互助協作小組”,一人常備兵役,余二人則兼顧三人“份地”,以供養服兵役者及其家庭人員。為了“更好”保證此項制度的推行,他提出政府“可以拒絕分配土地給不做工者或吸鴉片、賭博、偷盜、欺騙等罪犯,從軍隊逃亡或斥退的士兵也要剝奪土地”[10],借以剝奪這些人的工作權和生計權。
閻斷言該項制度不僅能消除“逃避兵役的弊病”,提高士氣,還有望將“犯罪和監禁”等社會痼疾一齊廢除。“在與中外記者交談中,閻錫山十分強調‘兵農合作制的核心思想及其在現實中的成功。”[11]閻認為無產階級是共產主義的基礎,二者相輔相成。欲“消滅”共產主義,不能僅僅依靠武力。否則,盲動“剿共”只會擴大“赤禍”,與“資敵”無異。故閻氏推行“兵農合作”的另一深層次目是為了防止治下民眾因戰、災、貧等成為流民而被一江之隔的中共所“煽惑”,轉而聽信、追隨中共。施行“兵農合一”可以使其有田耕、有組織、有仗打,“就不會有到處漂泊的流浪漢去參加‘非法軍隊了”[12],最終達到“穩民于晉”的“保晉”大業。對于閻錫山“烏托邦實驗”,哈里遜·福爾曼給出“最溫和的評語就是:這是一種仁慈的獨裁”[13]。美國《時代》《紐約時報》雜志訪延的左翼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與妻子邱茉莉的信中印證了這種說法:“在這里,沒有上帝,只有閻錫山,學校和辦公室都掛著他的畫像。”[14]
(二)陜甘寧“內循環”式經濟實踐
全民族抗戰初,陜甘寧邊區政府即確定“休養民力”的基調,提出“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障戰時生產品的自給”[15]的戰時經濟政策。財政供給主要由國民政府發放的軍費和海外華僑及后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兩部分構成;然而,上述局面亦未支撐太久,即被蔣氏打破。1939年1月,“溶共、防共、限共”成為蔣氏當局的“政治共識”,陜甘寧邊區邊界的國民黨軍事存在由1939年的31萬至1940年猛增至50萬(最多時)。至此,陜甘寧邊區內150余萬人口已被蔣氏當局完全隔絕在不足9.9萬平方千米、土地貧瘠的區域內。[16]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非生產人員的大量增加,使邊區的財政經濟遇到了極大困難。邊區“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17]。
艱難形勢下,邊區政府不得已采取經濟“內循環”經濟實踐——即推行“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以反擊蔣氏當局的軍事蠶食與經濟封鎖。到1942年,“大生產運動已經發展到整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和其他抗日根據地”[18]。至哈里遜·福爾曼訪延時,邊區“內循環”經濟實踐已從小規模的生產進入到“實現豐衣足食、建設革命家務”的新階段。
1.組織起來,注重激發各群體內生動力參與生產競賽
在哈里遜·福爾曼看來,邊區政權同閻氏在克難坡“家長式”經濟實踐中動輒“不做工,沒飯吃”的強制性勞作不同,中共應對經濟困局始終都在圍繞如何激發包括軍隊將士、政府人員、普通民眾、老道士、盲人等在內的各群體的內生動力參與生產競賽而同心協力。“每個人無論是最下層的農民還是最高層的政府官員,都在制定生產計劃,制定一年在農業生產上希望完成的大綱。”[19]
在推行“內循環”經濟實踐的過程中,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既反映了大生產的目的和基本經濟規律,也確保了邊區經濟建設的正確方向。同時,“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20]因此“人們熱情地投入大生產運動,這種狂熱已經超過了它的提倡者最樂觀的估計。”[21]
是年6月1日,哈里遜·福爾曼一行人自晉入陜“進入紅色中國”。次日,在第18集團軍120師359旅旅長王震的陪同下參觀了南泥灣的生產實踐。作為邊區經濟的“內循環”實踐的前鋒和旗幟,“無論搞生產還是作戰都一樣地努力,一樣地富有創造力。去年春天開荒,他們(359旅戰士)天亮以前就上山,直到天黑才下來。除了吃飯的時間以外,他們不肯休息,軍官只好下令:不在規定時間內不去做工”[22]。1944年,第359旅的將士們種地達26萬畝之多,收獲細糧3.6萬石,交納公糧1萬石,實現了每人生產6石1斗細糧,“每10人一頭牛,每3人一頭豬,每人一只羊和上百只雞”的計劃,達到了“耕一余一”(即耕種一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下一年吃的糧食)的基本目標。“他(賀鱗,時任359旅第718營營長)把士兵的肉食從每月兩磅的最低標準增加到每月六磅以上。此外,他還能供給他們幾乎無限量的蔬菜”,以至哈里遜·福爾曼等人由衷地贊嘆:“這大概是我所見過的軍隊中營養最好的隊伍。”[23]“就我所知,世界上從來沒有其他軍隊曾這樣大規模地做過,而且這種方法實在是造成軍民之間驚人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動力。”[24]
此外,中共在邊區積極推行“減租減息”“貸款促耕”“減稅降費”以及“招徠流民”等系列配套寬松政策,普通民眾在“變工隊”“扎工隊”等新的互助合作生產形式的組織下生產熱情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延長縣吳滿友鄉麻塔村變工隊自發競賽后,同等時間內,刨梢速度超過兩倍以上。[25]變工隊的組織形式還從農業領域擴展到國營、軍工、私營等企業,肥皂、火柴、紙張、化學用品、陶器、彈藥等產品都發展起來了。在哈里遜·福爾曼看來,盡管“他們的產量如以美國標準來衡量則不值一提,但紅軍來到陜北之前,那里根本沒有一點工業”[26]。《時代》雜志左翼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感嘆道:“一路上我們看到了發揚南泥灣精神的大生產運動已經使原來以貧瘠著稱的邊區大變樣。”[27]
2.儀式與生產,注重持續發揮勞動模范的正反饋效應
所謂“正反饋效應”,即一件事情的發生、發展受到了另一件事情的刺激,促進了其正向發展。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進化是陜甘寧政權的一項極為重要政治儀式,[28]“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著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29]。對此,哈里遜·福爾曼深表認同,他認為“技術和才能要用特殊的榮譽和物質來表彰,以鼓勵其成就。勞動英雄被推崇、贊美、獎勵、尊敬,以鼓勵別人和他們競爭”[30]。
哈里遜·福爾曼的視角下的邊區政府注重“儀式”即勞動英模的正反饋效應的事例非常多,同閻氏在克難坡“每天十二個小時的強迫勞動”有著鮮明區別。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到來的1944年,陜甘寧邊區勞動英模評選及獎勵活動已日臻完善,進入到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31]
訪延途中,他見到了不同類型的模范,如359旅的李位、日籍勞動英雄岡田吉雄(日本俘虜,工程師。因發明抽水機而榮獲勞動英雄稱號),農民勞動英雄吳滿友、李來增,工人勞動英雄李之華(鍛工)、佟玉新(鍋爐工),婦女英雄郭鳳英等。在哈里遜·福爾曼看來,將一批“二流子”改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英雄是中共注重持續發揮勞動模范的正反饋效應中所呈現出一個最為獨特的現象。“共產黨一九三五年來到邊區時,這里的二流子大約有七萬。……到一九四四年春,只剩下三千九百六十七人沒有改造過來。”劉生海是邊區最有名的二流子,曾經妻兒見其沒出息而決然離家。經過改造洗禮后,劉擁有了“六頭驢、一頭騾、三頭牛、八十一只羊,并且更種了一百五十畝地。他的家人也回來了……他的榜樣促進了同村的另外兩個二流子的改造”。劉還通過向吳滿友挑戰進行生產競賽,最終被選為甲等勞動英雄。所以,哈里遜·福爾曼對此次訪延之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即“延安是勞動人民的社會”[32]。反觀蔣氏當局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行前所拋出的諸如“陜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種植鴉片,人民生活困難”等謬論則不攻之破,國共站位高下立判。
3.發行并穩定邊幣本位幣,減少法幣使用的負外部性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鬩墻御侮”。中共讓渡貨幣改革金融制度,以法幣(國民政府本位幣)為邊區本位幣,收停“蘇票”,并依照協議,不設銀行、不發貨幣。然而隨著蔣氏當局軍費激增和國土淪陷加劇,加之日本在淪陷區禁用法幣,國統區內日益增大的法幣發行量與日益減小的流通區域,致使法幣購買力極速疲軟,其負外部性(亦稱外部成本或外部不經濟,指個人或群體的行為影響了其他個人或群體,前者使后者支付額外成本費用,但后者又無法獲得相應補償的現象)在邊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皖南事變后,蔣氏當局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付邊區,企圖把邊區軍民餓死、困死。[33]國共兩黨博弈從軍政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這對以法幣為本位幣的陜甘寧邊區而言不啻于一場滅頂之災。為化解邊區財政困難,避免邊區百姓遭受法幣跌價損失,同時亦為堅決反擊蔣氏當局發起的經濟戰爭攻勢,邊區政府果斷頒行《關于停止法幣形式的布告》《關于發行邊幣的布告》《廢止法幣實行邊幣的訓令》等三道法令,確定將邊幣作為邊區本位幣。而蔣氏當局卻本末倒置,強稱“邊幣”是八路軍把自己置之法外的“物證”,并對哈里森·福爾曼等西方記者大肆宣傳“邊區政府發行不合法的紙幣是中央不發軍餉的原因之一”[34];還在綏德、延長、洛川地帶有組織地開展邊幣與法幣兌換的黑市,用邊、法幣兌換產生的差價影響邊區內部及定邊、隴東等國共邊界的物價,擾亂邊區財政建設,破壞邊區金融市場的正常秩序。
作為回擊,陜甘寧邊區政府則通過“發行運鹽”“調劑法幣,推行邊幣”“打擊法幣黑市”“公開代買代賣”等系列舉措堅挺邊幣,[35]以期逐步擺脫長期通脹狀態下法幣的負外部性。在哈里森·福爾曼看來,“雖然重慶認為它(邊幣)不合法,但它已獲得了邊區人民的信任”;反觀“重慶幣(法幣)與美金折合率也是一個人為而荒唐的數字。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邊區政府已經成功地防止了通貨膨脹”[36]。
三、關于他者視角下
國共經濟博弈實踐的再思考
國統區的“克難坡”經濟實踐與陜甘寧的“內循環”經濟實踐是抗戰后期國共兩黨間由“封鎖與反封鎖”軍事對峙而衍生出各具特點的經濟發展路徑,亦可視為歷史演進過程中的“變態”與“常態”。
誠然,閻氏推行“克難坡”經濟實踐是彼時復雜局勢下的“最優解”;但閻氏在經濟活動中發行旨在作為收據、不能增殖的“合作券”以替代貨幣的流通作用,并輔以具有強制性質的“兵民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干預“生產者”主觀能動性,達到對轄區民眾的最大約束力,這是保守主義的“理想性”表達,是歷史演進中的“變態”。同自帶“正統”屬性的閻氏不同,中共應對蔣氏當局政治抹黑、軍事圍堵等危局下的發展路徑選擇只能是由“外”轉“內”,以“內循環”經濟策略為基線,注重激發“人”這一經濟活動中的最活躍的因素,以重構“生產者”的組織形式并參與生產競賽,以邊幣為邊區本位幣,直面蔣氏當局(包括閻錫山在內的國民黨地方軍閥勢力)在貨幣博弈中的各種“破壞性”手段,努力提高貨幣斗爭的藝術。中共正是“邁出”了發行邊幣的關鍵一步,才在真正意義上用經濟手段將陜甘寧邊區社會凝結成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為之后中共在更廣泛地域的金融實踐打牢基礎。這就是理想主義(共產主義)的“現實性”表達,是歷史演進中的“常態”。
隨著學界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研究的深入,基于國民政府政策制定及實施的結果的評價漸趨多元化。一些學者認為“實行戰時經濟政策,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干預,乃至“強制管制”,總體上順應了全國抗戰的潮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抗戰過程中國民黨當局及其地方勢力(閻錫山等)無不從各自利益取向出發,漠視民生,加之國統區經濟調控舉措時常失靈,通貨膨脹常年保持高位,使得民眾漸趨失望于國民政府。反觀陜甘寧邊區,在蔣氏當局殘酷的“封鎖”中生存并壯大起來,不僅歸功于正確的金融政策,更仰賴于新生政權的強大動員能力和廣泛的群眾基礎作為支撐。
注釋:
[1][6][7][8][9][10][13][16][18][19][21][22][23][24][26][30][32][34][36](美)哈里森·福爾曼:《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第26頁,第26頁,第32頁,第28頁,第32—33頁,第33頁,第52頁,第61頁,第61頁,第61頁,第77頁,第40頁,第67頁,第71頁,第42頁,第64—66頁,第73頁,第70頁。
[2][11]任文:《第三只眼看延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97頁,第50頁。
[3]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21名成員分別是哈里遜·福爾曼、岡瑟·斯坦因、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莫瑞斯·武道、普金科、科馬克·夏南漢神父、張文伯、金東平、謝秋爽、孔昭愷、趙超構、趙炳烺、周本淵、謝保譙、鄧友德、徐兆慵、楊嘉勇、魏景蒙、陶啟湘、張湖生、楊西昆。
[4][5]吳志娟:《明訪·暗戰: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國共輿論宣傳戰》,華中師范大學2014年博士論文,第48頁,第48頁。
[12][14][27]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沈蘇儒、賈宗誼、錢雨潤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頁,第209頁,第213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頁。
[17][20][29][3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第928頁,第898頁,第892頁。
[25]米曉蓉、劉衛平:《陜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頁。
[28][31]岳謙厚:《邊區的革命(1937—1949):華北及陜甘寧根據地社會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頁,第100頁。
[35]王金昌、張曉東:《陜甘寧邊區經濟典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頁,第189頁,第197頁,第201頁。
作者:中共屏山縣委黨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