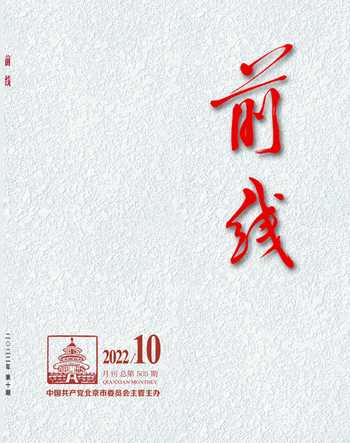人工智能帶來重大傳播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智能化革命是一場劃時代的跨越,是從工業文明向著數字文明的深刻轉型,正在帶來傳播領域的巨大變化。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一系列現象級改變,如何從總體上把握技術驅動下社會傳播領域的變化趨勢、深層邏輯及演化機制,已成為實現傳播實踐有序發展和不斷升級的必答題。
人工智能引發傳播網絡總體性重構
社會的智能化是一場革命。事實上,人工智能技術的全面滲透導致的關鍵變化,是對傳播網絡所鏈接的全部關系的總體性重構。不同于對某些傳播環節及某個傳播要素所進行的“小修小補”的改良型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全面滲透將創造一個無限量的巨大信息網絡,并將從前無法納入其中的更加多維的關系連接納入進人的實踐體系的可操控范圍中,也即從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全面走向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系統連接,創造智能終端之間的超級鏈接體系。
顯然,當一系列新的關系要素實現了對于人類實踐的“入場”,便會使得社會傳播成為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并在多重、多維的復雜因素的交織影響下實現“換道行駛”。媒介的迭代與技術的升維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持續地為傳統社會中相對無權者賦能賦權,數字技術改變了傳媒業因機械復制技術所形成的一對多、點對面式的信息壟斷格局,瓦解了傳統社會信息不對稱的大眾傳播秩序;“人人都是傳播者”極大地推動了豐富多彩、縱橫交錯的不同連接方式的交流與傳播的實現,實現了更多的傳播模式的涌現:物成為新的公共信息承載者,社會熱點的表達凸顯后真相、非理性等特點,關系認同、情感共振成為社會溝通與社會共識建立的關鍵,而平臺級媒體及作為其運行內在引擎的智能算法則成為信息傳播的關鍵性中介。
人工智能促成傳播生態根本性變革
在人工智能技術強大作用下,媒介產業的變革方向和媒介融合的發展路徑已經成為現階段傳播領域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進程中如何實現新傳播環境下的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的目標,達到主流資訊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的境界,必須有一個生態級意義上的羽化成蝶的深刻改變。
從傳播內容的供給側來考察,短視頻和直播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社會性傳播的門檻降到如此之低,每位用戶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人工智能時代無人機普及,各種環境中攝像頭、傳感器的無所不在,都將進一步超越傳統媒體的時空局限與感官局限進行豐富多彩、立體多維的信息采集,而其中的某些具有社會價值的信息則可能經智能系統自動加工后直接發送給多元用戶。概言之,數字技術帶來的“泛眾化”的傳播供給側,致使多元傳播彌漫在人們的各類日常生活的場景中。
就傳播形式的豐富和擴張而言,人工智能時代的傳播因其傳播形式的全息化、多樣態,信息傳播已滲透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而傳播技術的應用會以用戶場景為聚焦點而不斷創新信息的組織形式、傳播模式和內容形態。隨著以短視頻為代表的視覺傳播成為社會傳播的主流形態,內容傳播者因應當下移動化、碎片化和社交化的傳播場景,通過碎片化的視覺表達和情感共振、關系認同的傳播模式廣泛應用,使得內容生產與傳播形式轉型為一系列直擊人心的混合情感傳播模式。
智能化也使傳播渠道發生了全新的變化。面對媒介生產和用戶端的賦能賦權,極具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信息生態出現了供需危機,內容傳播的精準化已成為互聯網發展的下半場傳播轉型的重點。依托機器算法且擁有海量用戶及強大黏性的平臺遽然崛起成為平臺型媒體,并將逐漸躍升為新的行業主導者和傳播規則的制定者,實現向傳播權力中心的躍進。
人工智能推進傳播實踐革命性轉向
傳播技術的智能化發展為現實社會以及虛擬網絡空間中的傳播機制和傳播效應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也帶來了元宇宙、區塊鏈、物聯網、XR(現實擴展)、云計算、流媒體視頻等技術的新發展,它們正在深刻地改寫傳播領域以及社會發展深層邏輯。這已經不是一項彎道超車的發展模式,而是一項換道行駛的全新發展模式。
全社會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論認為,媒介可以與其他社會范疇相互建構,作用于人類社會形態的媒介形式其意義遠勝于其內容。這一理論視角強調了媒介邏輯對社會的建構作用,也強調了媒介與社會的相互形塑,人作為居間主體,其實踐具有能動性,因此可以通過宏觀和中觀型態與實踐的分析對媒介化進行解構,探究行動場域中不同社會角色之間社會交往和關系的變動模式,更好地幫助我們把握媒介化進程中的微觀、中觀、宏觀層級變化。
型態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型態”是指智能新媒介技術催生出新的社會行動方式和組織起的新的社會交往關系,包括個人與組織、個人與媒介、社會與媒介關系的變革,它將全面助力智能新媒介邏輯對社會實踐的形塑。以型態與社會實踐的視角展開探索與創新,以“點—線—面”的實踐試點為依據,運用更為貼合的理論工具,以期在未來傳播中對媒介化理論與實踐及其社會效果的把握有全新的突破。
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互構。在過往的傳播實踐中,將媒介與社會相分離的實踐模式忽略了媒介的作用過程,變成單純強調媒介與社會之間的決定/非決定關聯的實踐范式。我們認為,借鑒SCOT(技術的社會建構)路徑,同時對媒介演進基本邏輯與實現機制作出探索,不僅只考慮科技物體本身,也考慮科技物體的發展過程,同時關照到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及社會對媒介的租用,思考媒介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形塑、相互生產的互構關系及其實踐。
媒介影響社會結構的制度化。制度化的行動路線,即將媒介的形式視為一種獨立的制度化力量,強調并致力于實現媒介作為社會現實框架的組成要件。媒介邏輯被用來描述媒介所具有的制度的、審美的、技術的獨特樣式及特質以及借助正式和非正式規則運作的方式,從而提升媒介有效地影響更為廣泛的文化和社會的能力。
(作者:喻國明,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傳媒經濟與管理學會專業委員會會長)
責任編輯 / 丁兆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