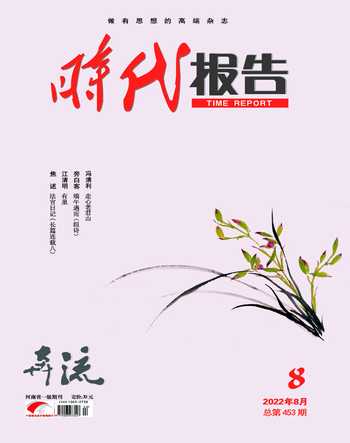水墨王者

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文藝圈的朋友甚多,但給我印象最深的當數王非。
第一次見王非是在十多年前。那時候,他的女兒王一寶恰好是我高三畢業班的學生。當時正值春節,王非從北京回老家探親,有朋友邀約,我有幸第一次見到他。王非身材瘦小,皮膚白皙,眉清目秀,眼光澄澈,更是飽覽群書,才思敏捷,睿智健談,透出一種天然的秀氣、才氣與靈氣。只一頓飯的工夫,我就為他的魅力所傾倒。
后來,隨著接觸漸多,我們的交往也日益加深。酒逢知己千杯少,話既投機不嫌多,只要一見面,我們便談社會,談生活,談家鄉,甚至談哲學,談藝術,談得最多的是畫畫,每每徹夜長談,“不知東方之既白”。從他那里,你會受觸動,受啟迪,受熏染,受鼓舞。十幾年來,我一步步完成了對他由相識到了解,由驚嘆到崇拜的過程。
王非1984年畢業于阜陽師范學院美術系,在做了幾年的中學美術教師之后,不甘寂寞和沉淪的他便只身去北京闖蕩,成為早期“北漂”的一員。他先是到北京畫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繼而去中國佛教協會做佛教文化研究,后來從事藝術編輯工作,率先創辦了國內首個民營美術雜志《藝術狀態》,盡管承受著物質生存與藝術生存的雙重炙烤,但他還是把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到自己最喜歡的畫畫上,并且明確而堅定了自己藝術追求的方向——當代水墨。
誠然,在藝術的人生中,王非無疑是不幸的,他有許多先天不足: 出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安徽西北部最偏遠的農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普通農民,既無物質基礎,又無社會地位,甚至連書香門第也算不上,他手無寸鐵,一個人孤軍作戰,深入藝術沙場,無異于徒手在白紙上作畫。但唯其如此,才更顯得他三十多年在藝術道路上跋涉之艱難,意志之堅定,精神之可貴,成就之難得。有人說,荒蠻之地出大家,王非通過幾十年奮斗,要用最堅實的腳印再一次去驗證。
非者,不也。人如其名,名副其實,在他的骨子里,對世俗,對藝術,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批判性,并從中找到一種新的語言——當代水墨,去闡釋自己始終未泯的夢想。因此,作為一個藝術家,王非有自己鮮明的個性、觀念、風格與追求。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對傳統的亦步亦趨,沒有某一流派的條條框框,沒有對某種風格的刻意追求,他走自己選擇的路,畫自己喜歡的畫,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與一輩子只愿畫一張畫或只能畫一張畫的畫家不同,每隔一段時間,他的作品都會呈現出不同的思考與變化,早期神話題材的旱魃系列,后來的紅粉、虛殼、關系、花開此處系列及現在的面孔系列等等,是他在藝術探索之路上留下的一個個腳印,每一個腳印都是那樣的清晰而堅實。其中,《鏡像天庭》《豐欲的困倦》更是他當代水墨探索之路上的里程碑,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反響。2016年開始,他連續兩年應文化部“中國國家展”之邀,參加21屆、22屆洛杉磯國際藝術博覽會,其面孔系列成了博覽會上最受關注和最受歡迎的作品,許多作品被組委會及外國畫廊收藏。不少專家學者更是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國當代水墨的希望!
王非不做畫家,只做藝術家,做一個開拓者、孤獨者和思想者。他認為,當代水墨是對當代文化的思考,是有責任有使命有擔當的思考,屬于東方傳統與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產物。水墨只是一種語言,用這種語言既可以展示天分,抒發才氣,繪制理想,也可以創新傳統,表達哲思,堅守探索,最終去闡釋人類未泯的夢想。他還固執地認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讓作品承載時代,讓時代塑造風格。作品應該代表一個時代,代表眾多人的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風格不應該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因此,當代水墨作品應該打破傳統水墨的羈絆與程式,以全新的語言重構時代精神,展示時代的多元化。這應該成為一個當代水墨藝術家孜孜以求的藝術理想。他在肯定藝術來源于生活的同時,還提出了生活模仿藝術,可以先創新后學習的主張。
有一段時間,我看到他創作的山水畫,古樸,典雅,空靈,頗具宋元明清之風。我疑心他又回歸傳統了!那時候,他對古典詩詞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經常與我探討唐詩宋詞中的藝術手法,探討詩詞中景與情,情與理的關系。由此進一步深入研究古代的山水作品,創作了大量傳統風格的山水畫。“要跳得出來,必須先入得進去。”“拳頭只有蜷縮回來,打出去才更有力量。”“現代水墨是相對于傳統水墨而言的,跳出傳統必須先進入傳統。”他如是說。
有人說,王非“在一個藝術工作室的黑箱子中孤獨摸索”,“多年來,他在黑夜中做黑白水墨藝術”。是的,在藝術追求的道路上,王非是真正的探索者、跋涉者,更是罕有的堅守者和成功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王非又是幸運者。
鑒于王非在中國當代水墨藝術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產生的廣泛影響,近年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爭相聘任他為客座教授、研究生導師。去年暑假,我偶然成為清華大學王非藝術研修班的一名編外學生,有幸在馬鞍山聆聽了他幾天的課程。幾乎與所有的美術導師不同,他不教所謂的“短平快”的速成技巧,不承認藝術道路上的“終南捷徑”,更反對學生們學自己的畫,他反復告誡學生:“你們不要學我的畫,否則,一種可能是只能在我的身后亦步亦趨,永遠超越不了王非,或者一旦超越了我,那你學的就更不像王非的了!我也是在不斷地否定自己的過程中作畫的。”
他認為,個性是藝術家的特質,風格是藝術家的生命。于是,他從美術史講到美學史,從美學理論到哲學體系,從美術理論到美術創作,從傳統繪畫到當代水墨,從藝術流派到藝術風格,可謂博古通今,學貫東西,視野遼闊,見解獨到。他提醒學生:“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只有登上山頂,才知道哪兒的風景最美。你只有掌握了這些知識,才能知道你自己最需要什么,最適合什么。”幾天的旁聽學習,讓我進一步認識到王非的大視野、大手筆、大格調與大情懷,對王非的學生們油然而生羨慕之心。在研修班交流群里,我忍不住向十幾位青年畫家發了感慨:
“盡管我不懂繪畫藝術,但我略知文學藝術,藝術規律應該是相通的,從藝術史的發展規律上,我可以作出一個大膽的預言:王非必將是一個載入美術史冊的人物,你們年輕,可以拭目以待!”
“盡管我沒有同你們一起很幸運地學習繪畫,但我很慶幸自己能成為王非老師的一個很幸福的學生。王非是一個藝術的巨人,你們完全可以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衷心祝福你們能夠站住站穩站久站好,盡快達到一個讓你們的同行們仰望的高度!”
我后來得知,這些學生中有不少是研究生畢業后,在美術界各自領域里或嶄露頭角,或業有所成,他們是為了尋求突破慕名來拜王非為師的。有一個畫家曾代表國家參加“2016年洛杉磯國際美術展覽”,在展覽期間認識和了解了王非之后,報了“清華大學王非藝術研修班”拜師學藝的。
除去畫畫,讀書幾乎成了王非生活的全部。在他的家里,除書房之外,床頭邊,沙發里,馬桶旁,樓梯的臺階上,到處都堆放著書。每次我們在一起,他總不忘提醒我多讀書,甚至推薦幾本書給我讀。王非的當代水墨博大精深,融匯了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剪紙、哲學、美學、宗教、歷史……藝術之樹常青,根深才能葉茂。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一幅美術作品就是一個生命,其中既有藝術方面的虛與實、濃與淡、疏與密、遠與近,又充滿著哲學層面的陰與陽、對與錯、善與惡、是與非等等,是一個對立統一體。正如水墨畫乃中國所獨有一樣,水墨藝術家王非也應該是中國當代藝術家中獨一無二的。畫家不計其數,王非只是王非。
如今,王非一直走在中國當代藝術探索之路的前列,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最先鋒最前衛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家鄉的驕傲,是中國當代水墨藝術的驕傲,必將以在當代水墨領域探索創新的豐碩成就,在美術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對此,我深信不疑。
王非是水墨的,正如他的畫一樣,有自己明晰淡雅的線條和色彩,有深邃遼遠的意境和韻味,有超然純粹的品質和追求,有理性睿智的思考和發現。王非就是王非,一個水墨的王非。
天下攘攘,皆欲何往?人間熙熙,異途同歸。畫家何其多,王非獨不同。在攘攘熙熙的當代水墨藝術世界里,孰為王者?且看王非!
作者簡介:
李燦光,安徽臨泉一中高級語文教師,臨泉縣作協副主席,《臨泉文藝》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