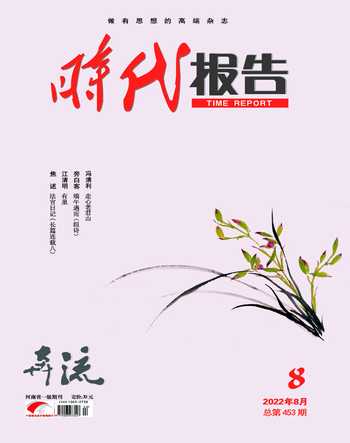家的樣子(外一篇)
馬志娟
我的家是什么樣的呢?
我的家必定得是寬敞的,有四間以上的臥室,盛得下我的父母、妹妹、兩個女兒和我、我的先生。
家里的墻壁得是白色的,月白,純凈又溫馨。家具得是實木的,讓我時時刻刻能接觸到植物,哪怕只是曾經的植物,也會讓我感覺是生活在大自然的世界里。
窗簾是藍色的,那是海的顏色、天空的顏色,即使在陰天的日子里,我的世界也是晴天;即使聞不到大海的味道,還可以通過海的顏色感受到海的寧靜和廣博。
窗戶得是落地的,讓我經常沐浴在陽光之下,接受陽光的愛撫,讓內心的明亮溫暖與外界的明亮溫暖合二為一。
窗前得有白色的鐵藝花架,花架上得有幾盆花,不能光有綠色盆栽,得有開花的花,讓我在花開花謝間,感受生命的輪回,沉寂與繁華。
我的臥室得有一張足夠大的床,不僅要承載我的身體,還得承載我多變的夢境,那里有童年的美好回憶,有青年的意氣風發,有中年的恬淡沉著,還有對溫煦的老年生活的規劃和向往。
廚房里各種鍋灶家具要齊全,因為那是最有生活味的地方,酸甜苦辣咸,人生百味,最后都匯成香噴噴的飯菜味兒,被一股腦地端上桌,從中品出濃濃的母愛來。
餐桌兼做我的電腦桌,其實本來是梳妝臺兼做書桌的,但是我不喜歡那些脂粉味兒,怕熏壞了我清新的文字。我寧愿坐在餐桌前,讓我的文字多些甘甜的水果味兒、溫暖的飯菜味兒的熏染,熏出些人情味兒,暖心。
生活在這個家里的成員,必定是內心充滿著愛,渾身散發出愛的光芒的。
我的父親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除了拉二胡之外,更多的時間都用來寫作,把自己畢生積累的知識,用簡潔樸素的語言表述出來,引領我們去認識這個世界。父親的內心充滿了對大自然、對親人、對生活的熱愛。
我的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可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家庭婦女,她是一個有修養、有內涵、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年輕的時候,她挑起家庭的重擔,把我們三個孩子撫養成人。年齡大了,又幫著我們帶孩子,用她的巧手做美味的飯菜、精美的繡花鞋,用一肚子的故事滋養我兩個女兒的心靈,讓她們從小懂得是非曲直、美丑善惡。我現在還記得她年輕時,心情好的時候,會細聲細氣唱《送軍》,調子拉得長長的,韻味十足。
我的妹妹是一個殘疾人,她三歲的時候發高燒,燒壞了智力神經,從此成長的只有身體,心靈永遠留在了三歲。妹妹一直跟隨父母生活,父母走到哪里,就把妹妹帶到哪里,須臾不離,像一個尾巴。
我的大女兒是一個聰明懂事的孩子,大學一畢業,就開始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小女兒性格比較內向,不太愛說話,但很懂事,喜歡學習,成績也很好,很戀人。
當然,這個家現在還缺席一名家庭成員,雖然生活也算幸福,卻不夠完滿。這個先生的崗位暫時空缺,雖然也有前來應聘的人員,卻屢屢因心靈的契合度不夠而一觸即離。盡管父母一直很憂心,我卻信奉順其自然。已經人到中年,把一切都看透看淡,能遇到心靈的知己,就彼此做個伴,相互扶持走向老年。如果不能遇到,也絕不將就,經濟獨立的女人獨自生活,真沒什么大不了。與書為伴,知曉古今中外多少事,心靈絕不孤單;以筆為伴,寫出苦辣酸甜諸般味,精神豐富圓滿。
我的家,就是我的港灣,不管外面有多少風風雨雨,這里始終陽光燦爛,即使面對雷霆萬鈞,我也坦然展現歡顏。
母親的素質
因身體出點小問題,最近幾天住醫院,醫院是中醫院,采用的治療手式有針灸、拔罐、足浴、火療、艾灸、按摩、理療、敷中藥等等,病人常常會在公共的治療室碰面,其間看到了人生百態,有呼啦啦一大家子圍著老人的孝親場景,有年輕的男孩獨自坐著輪椅做治療的孤獨景象,有老兩口互相攙扶的溫暖情形,其間最不能叫我忘懷的,是兩位母親。
與第一位母親相遇在衛生間。那是醫院的公共衛生間,只有兩個小隔間,空間逼仄。我跨進門的時候,一位年輕美麗的母親正站在第一個小隔間的門口,在跟自己的女兒說話,透過半掩的小門,我看到了那個四五歲的穿著精致的小女孩,女孩蹲在蹲坑上,聲音童稚甜美。年輕的母親看到我愣在門口,對我和善地笑笑,朝里努努嘴說:“里面是空的。”意思是告訴我里面小隔間沒人。
我回以一笑,說聲謝謝走進去。旁邊的對話在繼續,只聽那個母親柔聲說:“他們都不在家,他們去學鋼琴了,學跳舞了。”小女孩馬上說:“媽媽我也要學鋼琴,學跳舞,媽媽我喜歡跳舞。”母親回答:“好呀,過幾天我們去報名。”隔壁傳出了女孩高興的答應聲和窸窸窣窣整理衣服的聲音。忽然我聽到那個母親說:“不行,上完廁所必須沖水,踩那個腳踏板,對,就是那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們要保證公共衛生間的干凈,好了,踩一下就夠了,不能浪費水資源,記住了嗎?好了,出來吧。”絮絮的話語聲遠去了,我微微地笑了。記不清在哪里看到過這樣一句話:“母親的素質決定民族的素質。”我想,這位年輕美麗教養良好的母親,正好佐證了這句話的正確。
常常會聽到有母親抱怨自己的孩子“好吃懶做,亂花錢,自私、冷漠”,甚至聽到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一代是垮掉的一代,沒有擔當,沒有責任感等等。我想說,這些母親在抱怨孩子的時候,可有自檢自省過嗎?我們自己做好榜樣了嗎?我們把孩子該做的事放心地交給他們了嗎?
沒有,孩子小升初的時候,我們不顧他的反對,給他報了他不喜歡的學校。孩子參加學校集體勞動掃雪的時候,我們巴巴地跑到學校接過了他手中的掃帚。送孩子上學的時候,我們接過了他手中的書包。家里買了孩子愛吃的水果,我們把水果放進冰箱只準孩子吃。不管自己日子過得好不好,孩子的吃穿用度一定要比照富裕家庭的標準,美其名曰“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我們替孩子做了太多的決定,我們剝奪了他們鍛煉的機會,我們努力讓孩子活出我們想要的人生,可是我們忘記了,那是他的人生,憑什么用他的人生去實現我們自己沒有實現的夢想?在塑造孩子的道路上,我們又苦、又累,又要跟擰巴的孩子斗智斗勇,最后把他們塑造成了遠離我們初衷的模樣。
另一位母親的出場有點小驚悚。那時我正趟在針灸床上,臉上扎著針,迷迷糊糊在半夢半醒之間。忽然聽到有男人的聲音:“抱住我抱住我。”又聽到有“哎喲——哎喲——”的女聲,似乎在撒著嬌,判斷不出年齡。之后是抱了人安放在隔壁床上要求撒手的聲音。
我漸漸清醒了,微微側了臉覷過去,那是一個瘦弱干癟的老人,短短的花白的頭發,窄條臉,滿臉皺紋,臉頰上兩坨高原紅,眼神散亂,穿著紅毛衣和花棉褲,一個壯實的中年男子,正在給老人脫衣服,可能穿穿脫脫多次了又不得法,紅色毛衣的胳肢窩下破了一個洞。
男子問在場的一個女醫生:“趙大夫呢?”“在醫生辦公室呢。”男子請他旁邊病床的一個陪護人員幫忙看著老人,急急走出去了,十幾分鐘后回來,身后跟著一個男大夫。在老人不斷的呻吟聲中,男子卷起了老人的衣褲,露出干瘦的胳膊和雙腿,醫生給老人在臉上、胳膊上、手上、腿上、腳上都扎了針。這針雖然細,可扎的時候還是有些疼的,老人一直在似撒嬌似痛苦地哼哼著,男子在旁邊耐心地安慰和勸說著。扎完了,老人終于安靜下來,男子立在床邊,不時提醒老人“腿不要翹”,他旁邊是一個輪椅。
我跟著松了一口氣,撩起眼皮問那個男子:“這是你媽嗎?”“就是的。”“多大歲數了?”“八十了。”我奇怪地打量打量他:“你多大了?”“四十八。”他比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一些,也就三十幾的樣子。“你媽什么病呀?”“腦出血。”“多久了?”“三個月了,半個身子不能動了。”怪不得坐著輪椅呢。我同情地說:“照顧病人也挺累的啊。”他憨厚地笑笑:“兩個人換著陪呢,白天一個晚上一個。” 又補充說:“老媽把我們養大也不容易呢,這都應該的。” 這也是一個孝子呀。
后來,我又在針灸室遇到了這對母子,依然是溫和的提醒和溫柔的動作。那個母親語言含糊,說話支離破碎,但是兒子能聽懂。那個男子說,他媽媽尿頻,每晚起夜四五次,都得人抱著去上廁所,誰也睡不好,在肚子上做艾灸,希望能改善一下。這是一個樸實的農民,家住奇臺縣漲壩村。
閉上眼睛,我默默地想,這個兒子雖然文化不高,卻能盡心盡力照顧自己的母親,母親年老體弱,半身不遂,對兒子有了深深地依賴,他們現在相處的模式不像一對母子,倒像一對父女,母親返老還童了,這大約是一個“母親”最高的境界了。
“久病床前無孝子”,這個兒子卻做到了,這個好兒子是誰培養的呢?是母親。這也是一個好母親,雖然現在她已經在時光和病痛的雙重作用下失去了靚麗的容顏和健康的身體,可是她曾經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培養出一個道德高尚的公民,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兩個母親,兩種人生,都是高素質的好母親,一個已經功德圓滿,一個還在路上。
加油,中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