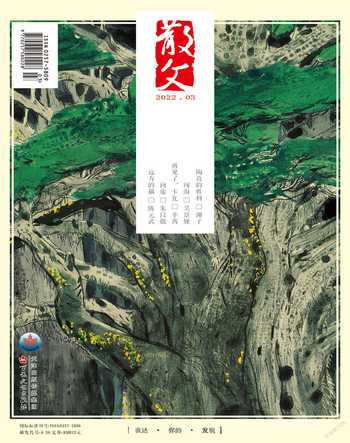再見了,卡瓦
辛茜
卡瓦死了,他的死來得太過突然。
卡瓦是一位藏族青年,生活在青海湖南岸江西溝鄉大倉村。走出家門,穿過村人簡陋的房舍,沿著冬天黃草夏天綠茵的小路向北,就來到了青海湖邊。這里,可以一覽無余地看見湖水,和大海一樣寬廣明亮的天空,聽漁鷗、鸕鶿、斑頭雁不停鳴叫。
金色的馬先蒿在陽光下閃爍,夏季的傍晚如此親切,卡瓦的心臟宛如湖水在輕輕顫動。每當這個時候,他都會覺得自己已經遠離了這個世界,正擺動著翅膀,在金色的光線下飛舞。他鐘情于這片湖水,忘不了夏日晴空下,湖水的嬌艷明朗帶給他的興奮與歡樂,也忘不了冬天銀灰的、迷霧一樣的湖面,讓他感到的寂寞與孤獨。
卡瓦原名娘吉本,畢業于西北民族大學少語系。他喜歡寫詩、寫散文、寫童話,喜歡作家托爾斯泰、黑塞、加繆、毛姆、馬爾克斯、王爾德,喜歡留言博客,渴望每一種擦肩而過的緣分,更期待愛情降臨。卡瓦這個筆名是他給自己起的,藏語意為“雪”。因為他出生的那天,山溝里下了一場大雪。
卡瓦的詩《我不是罪人》獲得過第二屆“崗尖梅朵杯”全國藏族大學生新創詩歌大獎。卡瓦的散文《假如我死去了》《我的憧憬》《回鄉筆記》,文字優美而悲傷。2014年,卡瓦與朋友拍攝完成了微型紀錄片《雅礱江邊的孩子》。同年,又出版了童話繪本《飛蛾》。他心地善良,敏感易傷悲。他相信,愛會改變一切。
他曾夢見一個春天,黃昏的太陽剛要落山,他牽著愛人的手,在大西洋最西邊的海岸奔跑。他的幸福,如海浪般拍打著海岸線。他曾夢見有一個冬天,白雪飄落,村子里的人早已沉沉入睡,他不出一絲聲音地哭泣,然后靜靜離去。
可是,卡瓦真的死了,死得悄無聲息。那一天,青海湖的陽光沒有那么強烈,沒有拍打著云朵的邊襟,也沒有流淌出金汁般的酥油。那場景歷歷在目,叫人心碎。人們簇擁在他早已冰涼的遺體旁,惆悵,無助,悲傷……
土地是這樣的沉重,青海湖的美艷、沉寂、荒涼,讓他學會了獨自承受。他留戀大地上詩意棲居的人們,也向往那些離開家鄉、四處流浪的人。為了父母的期待,他曾離家追逐遠方。可最終,他還是回來了。伴著秋日的黎明,無盡的憧憬、憂傷與鄉愁,他與村民一起收割,一起喝青稞酒,一起唱老掉牙的牧歌。
除了放牧、寫作、畫畫,卡瓦還是一位保護青海湖裸鯉的志愿者。他讀過七百年前一位女作家的書,那本書里寫滿了青海湖,寫滿了女作家對青海湖的一片深情。他覺得自己是青海湖人,從小在青海湖邊長大,保護青海湖是分內的事,所謂“分內”,就是他應該做的。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骨子里有著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性。
當然,他也很喜歡放牧。如果可以,他寧愿選擇和父母一樣的游牧生活,在草原上娶妻,生子,慢慢老去。
夜深了,卡瓦還在寫詩。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寫在漆黑的夜的臉頰上,寫在寒冷的風的翅膀上:
心的翅膀伸展到天空盡頭,
天邊的暴風卻猛烈地刮著,
在岸邊形只影單地站立著,
手高高地舉起示意著分別,
有一天我不再回來的時候,
在此岸邊永遠地沉沉睡去,
讓血與肉化作天然的肥料,
獻于花朵草木滋生的養分。
8月的一個周末,我來到青海湖畔大倉村。多杰扎西幫我找到了卡瓦的家,他們是遠親,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容易的事。卡瓦的父親和母親都在,這不免讓我有些緊張,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對失去兒子的老人。
落座后,多杰與卡瓦的父親在輕聲交談,我觀察著屋內的陳設。這是一個普通的藏人之家,沒有過多的裝飾。溫柔的奶香中,陽光灑滿連著灶臺的大炕,灶膛里跳動著火焰。霧氣蒸騰,我看見穿著紅色上衣、藍色牛仔褲的卡瓦,悄無聲息地穿過長長的陽臺,走進屋子,面對墻柜里擦得亮閃閃的碗盞,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端坐的這張沙發上,與父母交談。
卡瓦的父親知道我為卡瓦而來。他目光凝重,沒有我想象中的悲切神情。他用藏語平靜地訴說著八歲開始上學,聰慧、善良、靦腆的兒子;假期里揣著一包青稞炒面、一壺熱水,把羊群趕到湖邊,一邊照看,一邊趴在草灘上寫作業的兒子;長大后,成為村里唯一的大學生的兒子。以及再后來,共和縣政府對他們家每年一次的探望。除此,他再無多言。
卡瓦的母親是勤勞的女人,身著紫色藏裝,體態健碩,長發濃密,黑紅的圓臉飽經風霜。她為我們燒好奶茶、端上饃饃,不動聲色地打量我。我很希望她能坐下來和我聊聊,可她卻一刻不停地忙活,來來回回走動。不一會兒,她一聲不響地端來一碗餃子。先給了我,接著又端來一碗給了多杰扎西。最后,依然十分恭敬地用雙手端給了卡瓦的父親。
屋子里靜悄悄的,沒有人打破沉寂。我們一邊安靜地吃,一邊想著各自的心事。一位中等個頭、皮膚黝黑的年輕人走了進來。他是卡瓦的哥哥,會說漢話,卻也沉默著。我端詳著他,情不自禁地對他說,卡瓦和你長得很像,不過他比你長得高,好像比你更加強壯。他聽了一怔,露出一絲微笑。過了一會兒,一個眉眼十分俊俏、眼睛又黑又亮的小伙子走進來,看了看我,又出去了。他是卡瓦姐姐的兒子,身后跟著一個調皮的男孩,也是卡瓦姐姐的兒子。卡瓦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他是家中老四。
飯后,我提出為卡瓦的父母親拍照。卡瓦的母親頷首答應,快步走進臥室,拿出來兩頂禮帽。一頂給了卡瓦的父親,一頂端端正正地戴在自己頭上。隨后,我被邀請到卡瓦住過的屋子。屋子里的陳設原封未動,如卡瓦生前一樣,電視柜上有他的兩張照片。一張是在雪山下,另一張在青海湖邊。照片上的卡瓦,凝目注視,心無旁騖。桌子上整整齊齊擺著他的畢業證書、獲獎證書、詩集、童話繪本《飛蛾》。原來,在我吃餃子的時候,卡瓦的母親和哥哥,已經為我準備好了一切。
有人說,青海湖是大地上的一滴眼淚。有人說,青海湖的水下是魚,風上是鷹。鷹是另一個世界的居民,靈魂部落的首領;魚是湖中精靈,主宰著環湖流域蕓蕓眾生的命運。而卡瓦,是草原的天使,牧人的英雄,父母心頭的肉,哥哥姐姐永遠的遺恨和傷痛。
一群群斑頭雁掠過青海湖上空,一匹又一匹赤紅色的馬像流浪的歌手,在草原上徘徊,相互問候。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青海湖唯一的水生物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青海湖裸鯉,民間稱作湟魚的,原來竟也是有鱗的,只因青海湖流域海拔越來越高,湖水越來越咸,營養越來越少,它們有鱗的身體無法適應嚴酷的生存條件,才忍痛褪鱗,以增厚皮下脂肪,抵御寒冷。它們在湖水中艱難覓食,與清潔的灘地、瘦弱的蘆葦、低矮密集的苔草、成千上萬的候鳥,構成純粹簡單、強大又無比脆弱的生態鏈,維系著雄居青藏高原東北部、擁有巨大湖泊水體的高原濕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捕魚者在青海湖畔扎下的帳篷白茫茫一片。瘋狂的捕撈,讓裸鯉數量由1958年總量三十二萬噸,下降到兩千七百多噸,那魚翔淺底、萬鳥沸騰的景象不復重見。之后,政府雖連續四十年封湖育魚、嚴厲打擊、禁止捕撈,但因低溫干燥,營養貧乏,加之裸鯉本就生長緩慢,青海湖裸鯉資源恢復緩慢。
2015年6月26日晚上七點半,兩名魚販子正在大倉村湖岸偷捕青海湖裸鯉。卡瓦和村里的四個年輕人聞訊迅速趕到湖邊。看到他們匆匆趕來,狡猾的魚販子急忙把夜里布下的漁網投入湖中,面對卡瓦的指責勸誡,拒不承認。卡瓦又氣又急,為了當面取證,更為了阻止他們再次偷捕,毫不猶豫地獨自向湖中走去,準備拆卸漁網。
卡瓦下了水,岸上的其他幾個人頓覺心神不安,剛要勸他趕快上來。沒想到,話還沒說出口,往湖里走了不到二十米的卡瓦就陷入了湖水。
同去的四個年輕人和兩名魚販立即下水施救。可是誰都不會游泳,他們找不到他。從卡瓦下水到陷入湖中,整個過程僅一分鐘,沒有掙扎,沒有聲響,施了魔法般的湖水,就這樣讓一個活生生的,只有二十六歲,還來不及與心上人見面的年輕人消失了。
夜深了,6月的青海湖氣溫驟降,冰冷的空氣無奈地咀嚼著苦澀的湖水。只有受驚的幾只普氏原羚竊竊私語,憂郁的音調格外凄涼。
許多人趕來,眼里含著淚水,手里捧著松香。為卡瓦年輕的生命點燃酥油燈,祭獻食品,誦經超度……
如果生命有顏色,卡瓦應該是藍色的。他為湖水而生,又消融于湖水。像凡高的《星空》,深邃,絢麗。如果生命是音樂,卡瓦應該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激越,燦爛,閃耀著浪漫與激情。
一年又一年過去,大倉村的村民可能已經忘記,往年這會兒,卡瓦正站在湖岸,面對湖水凝神靜思,讓歡悅的情緒溢滿心房。相鄰的莫熱村是卡瓦母親的娘家,我趕到莫熱村去見卡瓦的舅舅,村里正舉行儀式,祭拜藏族人的水神。山坡上桑煙裊裊,巖石上掛滿水神雕像,清泉自山間涌出,兩邊開滿了花。
卡瓦的舅舅沉浸在神秘的氣氛中,似乎淡忘了這個曾經給予家族榮譽的親外甥,什么也說不出來,什么也想不起來。
午后的草原寂靜無聲,寬闊的原野在白云下凝固不動,卡瓦的父親和哥哥帶著我來到他遇難的地方。
湖水上漲,卡瓦下水的地方離湖岸又遠了二十多米。我默默肅立,心中悵然。古老的湖水與8月的藍天一樣縹緲不定,不可逆料。湖水在風中激蕩,勾起了我壓抑的悲傷。我感到一種巨大的力量,莫名的恐懼,恰似心葉顫動,危立于懸崖。卡瓦是一個最接近自然的人,也是最堅強的人,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他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融入了一場幾乎沒有人看見的巔峰決戰,令盜獵者望而生畏。
草原靜謐,靜謐得令人窒息,又無所依傍。我踮起腳尖,和卡瓦的哥哥一起,把我帶來的哈達舉過頭頂,系在石碑上。那石碑素樸簡約,只鐫刻著一行字:
您無畏的精神永存于我們心中
浪花層出不窮地涌現,湖水在天邊曼舞,我一步一回頭。卡瓦的呼吸就蕩漾在湖水里。微風中,蒿草彎腰俯視蒼莽大地,起起伏伏。陽光不再灼熱,遠望中,金色的馬先蒿、紫色的野蔥排列成行,頭戴金冠,身披如意,將一座石碑、一個草垛般的白塔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安放在看得見湖水、聽得見濤聲、嗅得到湖水氣息的沙地上。
再見了,卡瓦。
責任編輯: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