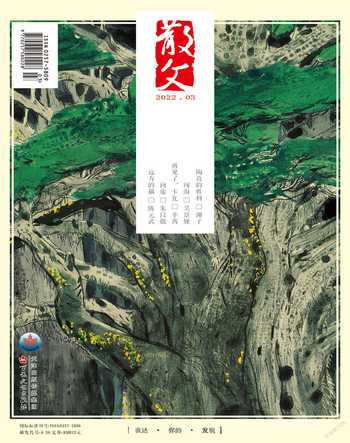秘密退場
指尖
那塊亮晶晶的手表,它的突然消失,讓我們對自己的記憶產生懷疑。手表的所有者小馬,更是神情怠倦,唉聲嘆氣,無比沮喪。他用好幾天時間,翻尋石頭周圍的狗尾巴草族,氣急敗壞地揪拽著它們,仿佛那塊手表被草木和土壤鉗制,不得不成為它們的同類。他變成一株飽滿的狗尾巴草,垂下沉甸甸的頭,目光呆滯,盯著那塊米色砂石,并試圖用一種超越時空的虔誠,祈求那塊用一年多工資、托人從外地購置的西鐵城手表,重新被擺放在蜂窩狀的石頭上,在漸漸涼下來的風和漸漸沉下的暮色中,再重新回到他的手腕。
這么貴重的物件突然消失,同樣讓我們手足無措,忐忑不安,我們重復并發揚著小馬的翻尋手法,草根,草葉,草根下的砂石和淤泥,像警犬一樣,沿著小小的不規則的球場周圍巡回,一遍,兩遍,無數遍。
林場院子里,沉默像夜幕,從山頂落到峰腰,再從樹尖跌到草尖。那塊消失的手表,跟半天的月牙同時從山頂閃出來,帶著一股冷漠和訕笑的神情,仿佛在指責并嘲諷我們懦弱自私的罪行。
我悄悄閉上眼,那個下午,便帶著尖刺和惡意,從許多個下午中脫殼而出。
那是個舒適得讓人想笑的下午,這在溫度偏低的林區是不多見的。我們將宿舍門大敞開,三個人在屋子里說著無關緊要的話,每句話的尾音,都被傻笑聲霸占。而男宿舍那邊,一陣一陣的哄笑和爭辯聲傳來,最終,他們打鬧著出了院子。那天下午,他們在宿舍門口大呼小叫,喊人來打籃球。師傅們大約不屑年輕人毫無誠意的邀請,極其矜持地坐在各自宿舍里,喝茶或者抽煙。最終出現在球場的,也只是這幾個喊叫的人——司機小顧、木匠小李、廚師小馬和技術員小于。我們三個女孩出門,略帶造作,慢吞吞出現在球場時,廚師小馬剛脫下他的夾克衫,左折右折,疊出一個明顯的小坑,放在狗尾巴草中的那塊石頭上,然后將手表從手腕上脫下來,擱入其中。小馬走出去,又返回來,壓了壓衣服上的手表,這才放心回到籃球架下。
暗黃色的籃球從別人騰躍的手中,毫無懸念地向小馬飛奔而來,并在小馬手腕的帶動下,在空中畫下完美的弧線。廚師小馬心中頗為得意,一直在笑,嘴大張著,兩排牙齒全部露在外面,在得到幾次夸贊后,一改之前吝嗇的性情,竟應承晚上請他們喝酒,不喝散裝的,要兩瓶高粱白。
那天晚上沒有人喝上酒,飯都吃得馬虎。承諾請人喝酒的廚師小馬,更是連食堂的門都沒有進去,幫廚的我們,不得已做了一頓晚飯應付。灶臺邊,少了他的身影,顯得冷清許多。他用大半夜的時間,拿著手電筒在籃球架下逡巡。
小馬長長的喟嘆聲,讓我們心懷歉疚,仿佛那塊手表的消失,是我們的失誤造成的。我們成為時間的同謀,都有偷盜或者協助手表消失的嫌疑,可能將它藏在黑暗的某處。它失去被擰轉發條的機會,表盤中細微而清晰的聲音,漸漸遲緩下來,最后停止運行。時間無法倒流,也無法重現,這種遺憾和驚恐也讓我們惶惶不可終日。雖然我們情愿張開臂膀,讓小馬搜身,乃至將抽屜上的鎖打開,讓他翻檢,但我們躲閃著目光,避免跟小馬對視,同時又不得不用極其夸張的語調,跟小馬保持著適當的親近。小馬說,他要再攢錢,還要買塊手表。我們都沒有應和,像一堵沉默而悔恨的墻。
秋深了,林場周圍的樹影比之前重了很多,早上起來,院子里鋪了一層落葉。我們幾個要用一上午時間,才能將落葉清理干凈。午后,一把火將帶著水汽的落葉點著,煙霧遲疑地凝結在林場院上空,氤氳不散。宿舍里,同屋的女伴為突然消失的發卡而揪心,她翻箱倒柜找尋,拉出抽屜,將里面的東西一股腦倒在床上,又將放衣服的小木箱子打開,把里面的衣服扯出來,全不管地上的塵土。后來她急中生智,把褥子翻開,露出床板,在確定沒有發卡后,又鉆入床下。她從床底下爬出來,頭發蓬亂,衣服上沾著一片一片的灰塵,她跪在那里,抬起頭,覷著一只眼,對著我喊:把手電筒遞我一下。
那枚發卡是在縣城集貿市場購買的,深紅色塑料材質的發卡,在眾多顏色和形狀的發卡中,讓她一眼相中,來不及議價,便毫無猶疑地將它收入囊中。其后,在書店我挑書的當兒,她又偷偷從包里將發卡拿出,喜滋滋欣賞半天。晚上,回到宿舍,她對著墻上的小鏡子,將頭發仔細攏起來,用皮筋束住,然后把這個“8”字形的發卡別在腦后。不停地問我:好看嗎?好看嗎?我從抽屜里拿出一面小鏡子,站在她身后,于是,通過兩面鏡子,她看到自己腦后的那枚發卡,正在燈下閃著微微的亮光。
有天,她竟然纏著木匠小李,給她打一個木盒子,專門來放這枚發卡,這事讓剛剛學會打個小板凳的小木匠為難了,他一會兒揶揄她,要給發卡打棺材,不吉利,一會兒又說,重量輕的發卡,最好就放在紙盒子里。但架不住她的糾纏,最終,小李不得不答應,只是延緩了時間。管村的婦女們在苗圃地勞作,休息的時候,偶爾會走進林場大院,剛好她出門,于是,在打完招呼后,她有意將頭往一旁扭了扭,對方立即被她的發卡吸引,不停夸贊:這發卡多么好看啊,無論顏色還是形狀。
而現在,如此心愛的物件,竟然在一夕之間消失不見了,怎不叫她心急。床下一無所獲,她用笤帚掃出一堆細細的塵灰,又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扒拉開它們,直到忍不住打出一串響亮的噴嚏。滿是灰塵的面孔,溢著熱淚的兩眼,她坐在凳子上的樣子讓人看起來好傷心。
你說,它哪兒去了呢?
她盯著我的目光中,漸漸滲入了深重的懷疑。我心下一驚,忍不住惶恐,躲閃著她凌厲的目光。直到許久后,不小心碰到自己的頭發,才釋懷下來。我的短發,是不需要那樣一個發卡來裝飾的。
出宿舍,去食堂的路,去木匠房的路,去會議室的路,去廁所的路,所有我們慣常走的路,都低著頭細尋了一遍。你去管村供銷社了嗎?她搖搖頭。我們失望地停在了那堆熏得失卻水分的落葉前,煙霧終于在半空中散開,之后被勒成一條細細的灰布條,蜿蜿蜒蜒,一直飄升到半空中。她伸手就去翻掀,火焰騰地一下躥出來。
冬天不知不覺已經滲入日子很久了,司機小顧將洗凈的墨綠色喇叭褲從水盆里撈出來,擰干,抖平,晾在失去葉子的樹枝上。一夜之后,這條褲子竟無影無蹤了。當他在雪杉樹上、樹下扒開密密的杉針,反反復復尋找那抹跟雪杉相似的墨綠色褲子時,我像之前的同屋一樣,正鉆在床下,尋找突然消失的書。那是用林場的信紙訂成的一本自制小書,某種意義上并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書。但在我心里,它比其他書籍更加重要,也更值得珍視。在翻掀被子、褥子、枕頭和抽屜無果后,我毫不猶疑地鉆進了黑乎乎的床板下面,幻覺中,床跟墻的縫隙間,它悄悄地掉下去,像一個玩捉迷藏的孩子,等待我找到它。我的同屋顯然成為有經驗的人,她及時將手電筒拿在手里遞過來,可是,手電筒卻沒有點亮,電池沒電了。這種不大順當的尋找,讓我更加堅定了床下那個藏者的真實存在,借著窗口隱隱約約的光,我伸出手,毫無目的地在地上摸索,直到同屋將一支蠟燭點燃,并蹲下來,燭光通過她的手臂,照亮床下的空間。我看見了一只布滿灰塵的鞋,看到歪斜地貼著床角的蒼蠅拍,看到幾張寫滿字的紙片,無一例外,它們都罩附著厚厚的塵灰,在被尋訪和拯救的等待中,漸漸灰心,黯然無光。我把幾塊同樣灰乎乎的磚頭搬出來,幾只蜘蛛突然在細細的塵土中四散奔逃。那本手抄的《唐詩宋詞選》,它不在這里,是的,它不屬于床下世界。
司機小顧已經開始破口大罵,他極其肯定,那條墨綠色的喇叭褲被某人順走了,一個雙手要在日后時間中日益爛掉的人,利用黑夜和寒冷的掩護,正在他的唾罵和憤恨中,漸漸壯大成形。
而我,灰頭土臉地坐在地上,想起第一次在管村某戶人家窗臺上,見到那本《唐詩宋詞選》時的情形。那本薄薄的紙張發黃的小冊子,其后幾天被我不停翻閱,我喜歡“滿眼風波多閃爍,看山恰似走來迎。仔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的意境,為“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而傷懷,憎恨“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里”的行止。
還是同屋提醒我,你這么喜歡,可以抄到本子上啊。
我肯定不能將它們抄到日記本上,于是,我將信紙裁開,又找到一本《山西林業》雜志的中間插頁,包了書皮,然后開始夜以繼日地抄寫。那是跟隨文字行走的三天,每一個字,每一句,都被我反復糾結、惆悵過。我把它放在枕畔,每天讀誦,并在它的陪伴下酣然入睡。
可是它不見了,這讓我的夜晚又變得極其漫長。我用幻覺來促成它的存留,它在任何一個可能被我遺落的地方:山楂樹下,雪杉樹旁,會議室的椅子上,食堂的飯桌上……它兀自飄在半空中,向著我搖搖晃晃而來,我禁不住高興地伸出手。醒來時,枕邊空空如也。
來自縣城的小顧,失去了當下最流行、自己最喜歡的那條褲子后,對林場的好感蕩然無存。乃至日后再不跟我們廝混,還常常請假,直到漸漸把宿舍里的東西都搬完,我們才知道,他要調走了。
所有被我們覺察并極力想挽回的消失,其實只是無數消失的一部分而已。時間中,一些事物正在從我們的生命中秘密退場,比如,十七歲的四季,放在盒子里等待褪去酸味的山楂果,喜歡過的那幅畫,揣在口袋里的手絹,銀灰色的鋼筆,一塊磨損得只剩下一角的橡皮,一張飯票,插在鏡子上的合影,還有少量的錢,一些寫在日記本里的心事……沒有偷盜者,也沒有撿拾者,更沒有拯救者,我們懷著惋惜、傷懷、感念和遺憾,沉默地吞咽被事物拋棄的恥辱,漸漸習慣它們緩慢或快速的消失進程。小馬的上海牌手表替代了消失的西鐵城,手腕上又重現那道白圈圈。而同屋女孩剪掉了長發,燙成小卷,不再需要一個發卡來裝點。我們開始變得極其健忘,開始享受著新事物的到來,開始坦然地表達出自己接納它們的欲望。
責任編輯: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