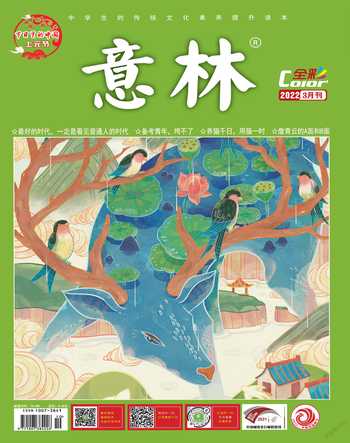灌臘腸
明前茶

一到大雪時節,路過肉鋪的顧客都會像我一樣伸頭往里張望:“趙叔來了沒?該灌香腸了!”
聽到有人念叨他,趙叔立刻從“回”字形的案板后面伸出腦袋,舉起被酒和辣子腌紅了的手,招呼道:“您還真準時,這會兒腌,趕得上臘月底分送親友,怎么樣,還要黑豬肉、黃酒‘五年陳’,不放麻辣?”
我的口味趙叔已記得,但照習慣他還得確認一遍。臨近臘月,好多單位突擊做了被疫情耽擱的體檢,血脂高的要灌“瘦腸”,血壓高的要“減一半鹽”,血糖高的要“去甜”。趙叔立刻給大家發撲克牌大小的硬紙殼,讓大家把口味寫在上面。寫完,稱肉,看著趙叔把紙殼別在袋子上,顧客就可以走了。隔兩三小時回來,臘腸已經整整齊齊灌好。
當然也有樂意看著趙叔親手灌腸的,因為只有這個季節才見得到他。趙叔是江西人,至今與老伴在家里種著幾畝稻田,只有嚴冬農閑才上城里來,與兒孫共同生活一兩個月。他們老家出小刀手,大雪節令一到,得雇人灌臘腸,老兩口大清早送完孫子上學,就到肉鋪去“上班”了。
看趙叔灌腸實在是一種享受。他是一個講究人,與眾不同。別人灌臘腸,把肉粗粗一切,沖沖洗洗,倒入大木盆,把調料往里一撒,一瓶黃酒一倒,拌勻,立刻就進灌腸機,半小時內,一大包沉甸甸的肉腸就灌好了。趙叔瞧著直搖頭:肉里的血水沒控出,調料就進不去;調料進不去,灌香腸的放鹽放辣就下手重。這水淋淋的肉腸得曬到幾時才干?恐怕等曬干時也咸得很了。
托趙叔灌腸,你得等,因為洗切完,他安排了一個“控水”的過程:肉放在不銹鋼大篦子上,篦子架在木桶上,肉上面再壓上一大塊壓石板。壓上半小時,肉里的腥水盡數流出,肌理變得緊實,才堪調味。趙叔準備的調味料也講究,黃酒必須是會稽產的“三年陳”或“五年陳”,糖必須是黃冰糖,砸碎后預先放在黃酒里化開,辣椒粉必須是四川二荊條磨成,花椒得挑陜西韓城的……
他唯一允許顧客自帶的調料是白酒,他有一個比啤酒蓋大不了多少的酒盅,管你帶來的是什么酒,他都得先嘗一口,看是不是適合調味香腸。若是醬香太烈有可能奪了肉香本味的,他喝完一言不發,把酒瓶子塞還你。顧客乖乖接了,賠笑道:“還用‘五年陳’,還用‘五年陳’。”
趙叔邊灌腸,邊跟相識幾年的顧客嘮嗑。顧客以家中主廚的大媽居多,少不得跟他埋怨些家中瑣事。趙叔也是個有閱歷的人,他一面坐在小板凳上,像魔術師從袖管里源源不斷地掏出手巾一樣,拉出一截又一截的香腸,一面三言兩語就開導了人家:“媳婦把一半香腸捎給了娘家,好啊,你不覺得親家母如今待你兒子更上心了?”
“不癡不聾不做家翁,要我說,孫子要上什么補習班還用你操心?你只管蒸臘腸、炒青菜,喂飽了孫子找朋友跳跳廣場舞。就算擔心他們管得不好,你也要放手。哪個人頭一次腌臘腸,能腌得人人稱好的?不成功,才知道明年怎么改。”
灌臘腸的過程,趙叔以自己的經驗開導顧客,修補了客人四處漏風的恓惶心態。灌完臘腸,趙叔用一根竹扦子,將幾十節臘腸一點點戳上放氣孔,這不僅僅是為了加強腸衣內外空氣的流通,加速水分的收干,更平衡了腸衣內外的壓力。老客們說得好:在老趙這里灌的香腸,你插根竹扦直接放在火上燒烤,腸衣都不可能迸裂。
(楊賀勤摘自《西安晚報》2021年12月15日 圖/李酉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