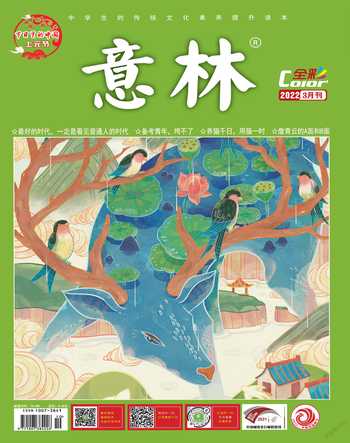天底下的牛肉都應該和土豆永結同心
蔻蔻梁

抵達布達佩斯那個晚上,我的錢在火車上被偷光了。明知道沒有什么找回來的希望,還是執拗地完成了報警落案等一系列手續。千辛萬苦找好住處之后,天已經黑了——在歐洲的夏天,這就意味著已經超過晚上十點。拖著極差的情緒進入一家位于地下室的餐館,連菜牌都不想看。
“給我一個Goulash就好。”我說。還在國內的時候,在東歐當過外交官的朋友馬里奧就說了,去匈牙利沒什么太多吃的,不是魚湯就是Goulash。
我喜歡這個發音,Goulash,各種摩擦音在口腔里翻滾,感覺自己的舌頭非常酥麻。一個大碗被端上來,紅彤彤的一片。在某些香港的匈牙利餐館里,這道菜也許會被翻譯為“匈牙利濃湯燴牛肉”,在我嘴里,它就是土豆牛肉濃湯。不管是哪種翻譯,“濃湯”這兩個字,還是一看就讓人很開胃。
這是道非常傳統的匈牙利國菜,大概就跟我們的四川火鍋一個道理。作為一個農牧業大國,匈牙利菜自然以肉為主。追溯到最早的做法,得回到九世紀。那時候的游牧民族把大塊牛肉煮好,撒上各種香料腌起來,然后放在太陽下曬成干肉。接下來,把它們裝到羊胃做成的口袋里,到煮的時候,就在草地上支起架子,將大鍋吊在架子上,把干肉扔到白水里一煮,加上土豆、面疙瘩,各種有的沒的能當時就手的香料,煮啊煮啊把硬如石頭的肉煮軟了,就可以吃了。
我簡直太著迷這種野蠻的吃法,什么前菜主菜,什么小菜主食,一大碗呼嚕下去,要淀粉有淀粉,要蛋白質有蛋白質,要脂肪有脂肪,要維生素有維生素,真是豪情萬丈,難怪要叫匈牙利(Hungry)“餓國”。《格林童話》里也有一則類似的故事,說是窮孩子沒有飯吃,就煮個石頭。精靈看到了心下不忍,就把鍋里的大石頭變成肉。不知道為什么,吃著Goulash的時候,老想起這則童話,覺得那個窮孩子吃到的那鍋石頭肉湯,一定也非常美味。如果碰對了季節,你的Goulash里會有一種叫作Paprika的匈牙利紅辣椒,不十分辣,但非常香。
在整個中歐,甚至在北歐,這道菜都是非常常見的料理。只是名字各有差別而已。
我認為食物到了某個節點都會大同小異,只要是這樣的組合,就一定難吃不到哪里去,好比將土豆和牛肉搭配在一起,這種節點,歐洲人能找到,亞洲人能找到,全世界人都能找到,實在不好說是誰發明的。俄羅斯人、中國人、匈牙利人、德國人、法國人,哪怕不懂吃的美國人,都還知道牛肉漢堡旁邊得配薯條呢。
同樣的道理還有將肉放在面里,意大利人做出了比薩,山西人做出了臊子面,東北人做出了餃子。你們又要說比薩是馬可·波羅從中國帶過去的了,人家意大利人才不贊同這種說法,正如俄羅斯人一門心思地認為餃子是他們發明的——他們倒是敢在中國說說這話試試看?
于是這一晚的Goulash很好地療愈了我。一種吃起來完全不異國的口味讓人覺得心里踏實了許多。錢被偷光了?去柜員機再取一點出來就好了嘛,又不是世界末日。
(楊賀勤摘自《假裝好吃》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圖/豆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