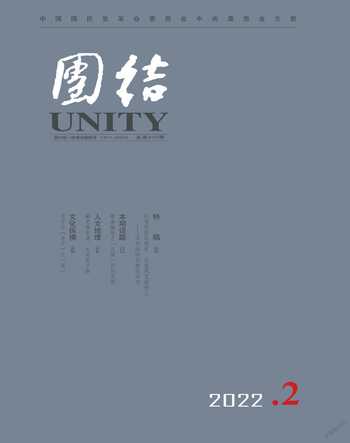步量故土,史述吾鄉吾民
——記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馬俊亞
◎喬文娟
(喬文娟, 民革江蘇省會委宣傳處干部/責編張 棟)
淮北地區, “在唐以前是生態良好的魚米之鄉, 演變至明清民國前期, 成為窮山惡水之地; 從優質稻米產地變成了粗惡雜糧之區; 從發達的手工紡織業中心退化成了紡織絕跡的經濟邊緣地帶; 從家詩書、 戶禮樂的文化沃土, 變成了殺人越貨的盜寇樂園; 從精英輩出的人文薈萃之地, 淪為江南體力勞動者的主要來源地”。 這是一個區域自然生態、 經濟產業、社會人文的全面退化, 弄清楚這種退化何以發生、 如何延續深化, 對人類, 對國家, 對民族都是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對于淮北人來說, 今天淮北已經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巨大的改善, 但千年積弊也并未消除干凈, 去追問這個問題不僅關涉那些宏大意義, 更加關系那幾個古老而永恒的問題, 我們從哪里來, 我們何以至此, 我們將向何處去。
馬俊亞是淮北人, 他為故鄉為這幾個古老的問題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自泥土中成長
馬俊亞1966 年出生于江蘇沭陽的一個農村家庭。 這個時代, 這個地方的農家子弟, 他的童年, 勞苦和饑餓可想而知。
馬俊亞的村子中間有清朝治河時被廢棄的后沭河穿過。 馬俊亞經常帶著轆轆饑腸和哥哥一起用平板車拉黃泥, 黃泥被泛濫的黃河從黃土高原帶來, 不適合五谷生長, 只能用來填坑蓋房。 村子西面是范圍曾達數百平方公里的青伊湖和桑墟湖, 村子因此被稱為 “湖東口”。 村西南是民國時著名匪窟司家蕩。 村東也是曾達數百平方公里的碩項湖, 鄰村叫 “陸口”。村南是古漣水, 直通鹽河。 村北稍遠是沭河。 縱橫的河汊湖澤帶來的, 除了打豬草、 割柴禾之暇的摸魚場所, 還有年年進村入戶、 淹沒莊稼的澇水, 和水退之后的鹽堿荒灘, 以及鄰壑之間的爭吵毆斗。
“男孩子不吃十年閑飯” 是長輩的教誨。 由于父親被事故燒成重傷, 馬俊亞8 歲時就吃不到“閑飯” 了, 給家里和生產隊干各種農活、 體力活就成為生活的主題, 在此之前, 哥哥姐姐早已開始承擔成年人的辛勞和責任, 但卻掙不到工分。 秋收分配時, 馬俊亞家常常都是 “透支戶”,分不到幾斤糧食。 馬俊亞的主食通常是摻雜著野菜的玉米糊, 他能吃幾大碗, 但根本不抵餓,“往往在捱到上午第二節課的時候就餓得直冒冷汗”。 每年馬俊亞家總有一段時間斷頓, 母親便會冒著 “投機倒把” 的風險與人合伙做 “炒牌”(一種烤餅), 原料小麥磨成80%的白面, 15%的粗黑粉, 5%的麩皮, 白面做成炒牌賣掉, 粗黑粉和麩皮便是利息供家人食用。
馬俊亞的童年可盼的是外公。 外公曾做過私塾先生, 不僅會帶來吃糠咽菜省下的糧食, 讓他吃飽一些, 還會教他四書五經、 千家詩、 給他講詩詞韻律, 在淮北農村貧瘠的精神土壤中為他帶來難得的啟蒙。
還在農村時, 馬俊亞就知道, 村里最漂亮的姑娘都會外嫁, 有的嫁給河南的礦工, 有的嫁給了城里的瞎子, 有的嫁給了吃國家糧 (城鎮戶口) 的傻子, 有的嫁給了國營農場的二流子……當1984 年, 馬俊亞以沭陽縣華沖中學總分第一、高于 “一本” 錄取分數線40 多分的成績考取蘇州大學歷史系, 成為村里第一位大學生之后, 富裕繁華的江南更是直觀地成了貧困荒蠻的故鄉的對照。
大學時代的馬俊亞每天流連于蘇州大學紅樓圖書館的古籍之間, “因貧窮, 家境不好, 在上大學期間也沒有多余的錢從事其他娛樂活動, 我最大的興趣就是讀書”。 讀書、 讀史不僅給他留下了扎實的文化和史學功底, 也逐漸喚醒了他的故鄉之問。 “讀研究生時, 我開始對近代經濟史比較感興趣, 就計劃先研究江南社會, 然后再研究蘇北, 這樣或許觀察得更準確。” 這也是他后來一直堅持的兩個研究方向 (江南社會經濟與淮北社會生態) 的由來。
求學期間雖然生活有些緊巴窘迫, 但為了學術研究他從不吝嗇。 為了訂閱 《中國史研究》 和《歷史研究》 等刊物, 不惜縮衣節食; 為了查史料, 不惜花費到北京上海等地。 馬俊亞曾多次到上海拜訪丁日初先生, 每次只能住一晚10 元左右的旅店; 到北京, 汪敬虞先生每次必留飯, 與他長談做學問與做人的道理。 在他人都在抱怨論文難以完成的時候, 馬俊亞只用一年半的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寫作, 余下的讀博時間大多花在對蘇北的調研上。 1996 年, 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崔之清教授應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段本洛教授邀請,參加馬俊亞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 崔之清教授認為論文寫得相當出色, 并將馬俊亞推薦給南京大學歷史系張憲文教授作博士后研究。 因此, 他也成為南京大學第一個歷史學博士后并提前出站。
追問故鄉: 被犧牲的 “局部”
“我的研究不是坐在書齋里喝著清茶或咖啡進行的, 而是在泥濘的鄉村道上捧喝路邊的河水完成的。 20 世紀90 年代, 我曾十多次對江南鄉村做過調查。 對淮北的調查次數就更多了。 所以, 我自信我的成果一定很 ‘真實’。”
1991 年碩士畢業后, 馬俊亞到浙江師范大學工作, 被派到時在蔣堂鎮的金華一中鍛煉一年。他決定認真系統地閱讀馬恩著作。 于是, 馬俊亞在空閑的時間里精讀 《資本論》, 一年做了近30本讀書筆記。 之后, 又一鼓作氣, 把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讀了大半。 由此, 馬俊亞確立了自己的“生活決定意識” 的歷史觀。 “吃透了原著, 我開始敢講話了, 敢講自己的歷史學觀點了。”
早在1995 年, 馬俊亞就開始了對蘇北的調查研究, 直到2010 年歷時15 年的時間, 《被犧牲的 “局部”: 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 (1680—1949)》 (繁體版) 一書才得以出版, 厘清了江南與淮北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的地區性差異, 通過江南與淮北的系統對比, 找出了故鄉落后的原因。
期間, 他對書里劃定的研究區域的每個縣都做了田野調研, 深入閉塞偏僻的鄉村, 由于沒有經費資助, 常與小商小販同住。 有時無緣無故被人詈罵, 被村民圍毆。 “可以說, 是真實的 ‘生活’ 給了我許多史學的觀念和論點。”
經過查閱史籍、 大量的田野調查, 馬俊亞在 《被犧牲的 “局部”》 中闡明了淮北落后于江南的根本原因。 他認為, 淮北地區社會生態的變遷正是馬克思所說的 “行政權力統治社會”而造成的負面結果, 封建中央政府以 “顧全大局” 的名義而有意犧牲這一 “局部利益”。 江南由于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合理配置, 較早形成了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鏈, 得以用少量的耕地,養活眾多的人口。 相反, 淮北的 “發展” 走了一條與江南截然相反的道路。 在唐以前, 淮北屬于國家的 “核心” 地區, 自然環境與農業生產條件非常優越, 是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1128 年, 宋軍人為掘開黃河大堤造成黃河奪淮,初步破壞了淮北的水利系統; 明代以后, 政治中心北移, 運送江南貢賦的運河漕運日益吃重,治黃治河力度空前, 但其指導思想卻不是為了民生, 而是維持漕運和保護祖陵的政治需要。為了保護大運河的安全, 把所有的黃河河水全部逼到了淮北, 后來高家堰的修筑在平地上高懸起一個巨大的洪澤湖, 整個淮北的水網系統都嚴格為運河服務, 而非農業民生, 淮北成了災荒頻發、 匪患深重、 社會生態崩潰的落后地區。 因此, 淮北地區的生態畸變和民生困苦被視為局部利益, 讓位于專制朝廷利益。
在運河之外, 淮北還有另一個高踞民生之上的大局, 鹽務。 鹽業自始至終都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柱, 敲剝萬民的抓手。 但鹽業的利益分配是基于與國家核心權力的親疏遠近, 完全由政治權力掌控, 絲毫不會惠及作為主產地的淮北, 只給淮北留下勞役, 和被剝奪限制鎖死的社會經濟。
《被犧牲的 “局部”》 在豆瓣上評分 8.9,這個社科名著級別的評分, 很直白地肯定了書的質量。 考慮到這是一本區域社會生態史著作,專業性強, 主題小眾, 專業讀者比重高, 這個評分可能還是偏保守的。 馬俊亞的著作當然不止于此。 他有專著 10 部, 其中 《被犧牲的 “局部”》 獲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優秀成果二等獎, 《區域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比較研究: 以江南淮北為例(1680—1949)》 獲江蘇省第十四屆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除了自己的著述, 馬俊亞還翻譯了很多外國名著, 英國霍布斯·鮑姆的 《史學家: 歷史神話的終結者》、 美國柯博文的 《走向 “最后關頭”: 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影響》、 彭慕蘭的 《腹地的構建: 華北內地的國家經濟和社會變遷》。 在 《歷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社會學研究》 《中國經濟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 Modern China (美國)、 Modern Asian Studies (劍橋大學) 等數十種海內外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中國社會經濟史和生態史專題研究論文100 余篇。 獨立承擔或主持的省部級以上課題13 項, 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大運河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研究項目 《近代中國社會環境歷史變遷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招標項目 《中國抗戰經濟研究 (1931—1945)》 等。
在中國古代, “史” 的本義是公正。 《說文解字》: “史, 記事者也。 從又, 持中。 中, 正也。” 我們所想像中的史家, 大約也是如此, 中正平和, 古井無波。 但馬俊亞似乎不完全如此,在他的文章和著作里, 在龐雜的史料和嚴謹的梳理分析背后, 常透出一種濃烈情感, 一種對吾鄉吾土的深切探究和因之縈繞的千年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