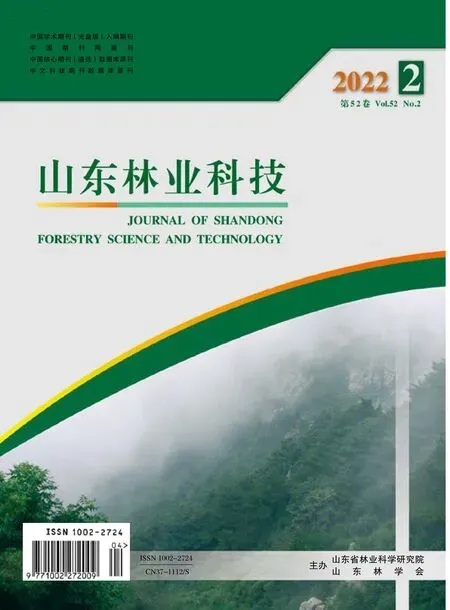一種暹羅炭疽菌Colletotrichum siamense引起的棗炭疽病
解小鋒,楊緒強,亓玉昆,孟曉曄,韓鳳英,劉文璋,劉 慇,韓傳明,王清海
(1.山東省林業(yè)保護和發(fā)展服務(wù)中心,山東 濟南250014; 2.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qū)文昌林業(yè)站,山東 濟南250300; 3.山東省林業(yè)科學(xué)研究院,山東 濟南250014; 4.山東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院,山東 濟南250100)
棗(Zizyphus jujuba Mill.),鼠李科、棗屬,果肉甘甜味美,汁多果脆,富含豐富的維生素和礦物質(zhì)元素,被譽為“天然維生素丸”。棗為中國特有樹種,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栽培歷史。棗樹適應(yīng)性廣、抗逆性強,在我國新疆及黃河中下游流域均有分布。 近年來,隨著栽培模式的升級、品種的更新?lián)Q代,我國棗栽培面積及產(chǎn)量穩(wěn)步增長,2019年我國棗產(chǎn)量達746.4 萬t。
由炭疽菌屬(Colletotrichum sp.)真菌引起的炭疽病是棗產(chǎn)區(qū)的一種重要植物病害,造成嚴重的經(jīng)濟損失[1]。僅2007年,棗炭疽病在山西省柳林、晉中地區(qū)造成了14 億元的損失[2]。 炭疽菌屬真菌全球性分布,危害寄主范圍廣,尤其危害鱷梨、芒果等高檔水果,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嚴重。 國內(nèi)已有的報道表明棗炭疽病的病原菌為膠孢炭疽菌(C.gloeosporioides)[1,3-8],在棗炭疽病菌鑒定方面,大多數(shù)文獻依靠形態(tài)學(xué)特征,少量文獻通過形態(tài)學(xué)特征和ITS 序列分析相結(jié)合的方法。目前研究表明,膠孢炭疽菌是一個復(fù)合種[9],是否有其他炭疽菌可以引起棗炭疽病,尚不清楚。
2019年8月,作者在山東省濟南市仲宮鎮(zhèn)小門牙村棗園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棗葉(品種:仲秋紅)上出現(xiàn)圓形或不規(guī)則形褐色病斑,病葉率達30%以上,感病棗樹樹勢較弱。 因此完全有必要明確其病原種類,為該病的有效防控提供理論依據(jù)。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材料
感病棗葉片,2019年8月,從山東省濟南市仲宮鎮(zhèn)小門牙村棗園采集。
1.2 方法
1.2.1 棗炭疽病菌株分離純化
樣品分離采用常規(guī)的組織分離方法。 采集的棗炭疽病病葉70%乙醇表面處理后,在葉片病健交界處,用無菌的解剖刀切成小組織塊(5 mm×5 mm)。 然后依次1%次氯酸鈉(1 min),70%乙醇溶液(1 min),無菌水沖洗3 次。將處理后的小組織塊置于PDA 平板上(5 塊/皿),28℃,散光條件下培養(yǎng)。5d 后,挑取單個菌落菌絲,置于新的PDA 平板上,散光條件下28℃培養(yǎng)7 d,在接種點附近產(chǎn)生橘紅色分生孢子團,用移菌環(huán)刮取少量孢子置于無菌水中,配成孢子液,在PDA 平板上涂布、培養(yǎng)。2d 后挑取單個菌落,獲得純化菌株。獲得純化菌株均在山東省林業(yè)科學(xué)研究院森林保護研究所保存。
1.2.2 致病性測定
獲得單孢菌株致病性通過離體接種的方法進行測定。 選取成熟、新鮮、健康的棗葉(品種:‘仲秋紅’),自來水沖洗30 秒,自然晾干,75%的酒精消毒處理,備用。 隨機選取JNZG11、JNZG311、JNZG313 菌株在PDA平板上培養(yǎng)7d,制成孢子懸浮液(×106孢子/mL),備用。 用無菌針(φ = 0.5 mm)輕微刺傷葉片,在傷口處接種200 μL 孢子懸浮液,以無菌水為對照。 將處理后的棗葉置于含有少量無菌水的無菌燒杯中,用保鮮膜封閉,28℃,培養(yǎng)7 d,觀察葉片的發(fā)病情況,并與田間癥狀進行比較。
1.2.3 病原鑒定
1.2.3.1 形態(tài)學(xué)鑒定
選取JNZG11、JNZG311、JNZG313 菌株作為代表性菌株, 置于PDA 平板培養(yǎng)(28 ℃、12 h 光照/12 h 黑暗)培養(yǎng)5 d,觀察記錄菌株的培養(yǎng)特征。5d 后挑取菌落產(chǎn)生的子實體(黑色小粒點),制作玻片,通過尼康50i顯微鏡(Nikon Eclipse 50i,日本)、QImaging 照相系統(tǒng)(QImaging 加拿大)、cellSens 軟件,觀察分生孢子及附著胞形態(tài)并測量其大小。
1.2.3.2 分子鑒定
采用改進的CTAB 法提取供試菌株的DNA[10]。 選取以下6 種保守基因進行擴增與測序,分別為:核糖體轉(zhuǎn)錄間隔區(qū)序列(ITS)、幾丁質(zhì)合成酶A 基因(CHS-1)、肌動蛋白基因(ACT)、β-微管蛋白基因(TUB2)、3 -磷酸甘油醛脫氫酶基因(GAPDH)和鈣調(diào)蛋白基因(CAL)為目的基因。 以ITS1/ITS4、CHSⅠ-79F/CHSⅠ-354R、ACT-512F/ ACT-783R、βt2a/βt2b、GDF-1/ GDR1、CL1/ CL2 分別為ITS、CHS-1、ACT、TUB2、GAPDH和CAL 基因的引物進行擴增測序。 擴增反應(yīng)體系25 μL(Taq 酶mix 12.5 μL,上游引物下游引物各1 μL,ddH2O 8.5 μL,DNA 模板2 μL)。 PCR 參數(shù):預(yù)變性(95°C,5 min)、變性(94°C,30 s)、退火(ITS:58°C,30 s;CHS-1、GAPDH: 56°C,30 s;ACT、TUB2、CAL: 59°C,30 s;)。 PCR 產(chǎn)物送往上海派森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進行雙向測序。
將各個菌株 (JNZG11*、JNZG12*、JNZG14*、JNZG15*、JNZG311*、JNZG313*) 的ITS、ACT、CHS-1、GAPDH、CAL 和TUB2 基因序列提交到GenBank數(shù)據(jù)庫中 (基因編號:ITS: MT570098、MT570094、MT570096、MT570095、MT570093、MT570097;ACT: MT894282、MT894284、MT894293、MT894288、MT894289、MT894292;CHS -1: MT894270、MT894271、MT894272、MT894273、MT894274、MT894275;TUB2: MT894280、MT894276、MT894278、MT894277、MT894281、MT894279;GAPDH:MT894283、MT894287、MT894285、MT894286、MT894290、MT894291;CAL:MT894268、MT894264、MT894266、MT894265、MT894269、MT894267)。選取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復(fù)合種內(nèi)的43 株菌株作為參考菌株[11],以C.boninense 模式菌株MAFF 305972 為外圍菌株。 通過MEGA 7.0 軟件中的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構(gòu)建多基因(ACT-CHS-1-GAPDHITS-CAL-TUB2)系統(tǒng)發(fā)育樹,以自展法(Bootstrap)進行檢測(循環(huán)1000 次)。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棗炭疽病癥狀
2019年8月, 作者在山東省濟南市仲宮鎮(zhèn)小門牙村棗園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棗樹葉片受害嚴重, 病葉率達到30%以上。 危害棗樹葉片, 在葉片形成圓形或近圓形斑點,病斑中央褐色,凹陷,輪紋狀排列小黑點,四周黑褐色,病斑外圍有淡黃色暈圈。 葉脈對病斑擴展限制作用隨著病斑擴大, 幾個病斑擴展成不規(guī)則形壞死斑,部分壞死斑脫落,中央形成穿孔(圖1),嚴重影響葉片光合作用,后期造成葉片早落。

圖1 棗炭疽病田間癥狀Figure 1 Disease symptom on leaves of jujube in field
2.2 離菌株致病性
棗葉片接種孢子液5 d 后, 在葉片接種部位均表現(xiàn)出癥狀,發(fā)病率為100%(圖2a),而接種無菌水的葉片未表現(xiàn)出癥狀(圖2b)。葉片病斑圓形或近圓形, 中央稍微凹陷,黑褐色。 病斑擴大成近圓形或不規(guī)則形的壞死斑,壞死斑有黑色小粒點(子實體)產(chǎn)生,少量橘紅色粘質(zhì)(分生孢子)(圖2a)。接種后產(chǎn)生的癥狀與田間觀察的癥狀一致。 通過同樣的分離方法,從接種產(chǎn)生的壞死斑上可以分離到與接種菌株形態(tài)特征一致的菌株。 由此可見,本試驗分離獲得的菌株可以引起棗炭疽病,是其病原菌。

圖2 致病性試驗(a)果實接種后病斑;(b) 對照Figure 2 Pathogenicity test (a) necrotic lesions on leaves inoculated with isolate JNZG313; (b) control with sterile water
2.3 棗炭疽病菌形態(tài)學(xué)鑒定
在PDA 培養(yǎng)基上,菌絲初期白色,菌絲致密,菌落平整,邊緣整齊。 后期逐漸形成淡黃色,背面色素黑褐色(圖3a)。分生孢子單胞無色,內(nèi)含油滴、紡錘形至橢圓形(圖3b),大小為(11.1-) 12.7-13.3 (-17.8) ×(-4.4)5.2-5.5 (-6.3) μm (13.0 ±1.2 × 5.3 ± 0.5 μm, n = 50),長寬比為2.5。 附著胞卵圓形、不規(guī)則形,深褐色(圖3c),大小為(7.3-) 8.6-9.2 (-9.8) ×(-5.1) 5.8-6.9 (-7.0) μm (= 8.9±0.7×6.3±0.7 μm, n=50),長寬比為1.4。 通過觀察發(fā)現(xiàn)JNZG311 JNZG313 產(chǎn)孢較多,JNZG11 產(chǎn)孢較少。 其分生孢子附著孢大小、菌落形態(tài)與膠孢炭疽菌復(fù)合種(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complex)形態(tài)學(xué)特征一致。

圖3 Colletotrichum siamense 形態(tài)特征(a)菌落形態(tài);(b)分生孢子;(c)附著胞Figure 3 Colletotrichum siamense (a) cultural character; (b) conidia; (c) appressoria
2.4 棗炭疽病病菌多基因序列分析
將獲得的6 株菌株的6 個基因序列串聯(lián)后, 與暹羅炭疽菌模式菌株ICMP 18578 相似度為99.6%。 在采用最大似然法構(gòu)建的多基因(ACT、CHS-1、GAPDH、ITS、CAL、TUB2)系 統(tǒng)發(fā)育樹(圖4)中,以粗體表示的為模式菌株, 在分支節(jié)點處標注自展率, 標尺指示為0.02 步變化。 系統(tǒng)發(fā)育樹最高對數(shù)似然值為-8965.61。 本試驗獲得的6 株菌株(JNZG11*、JNZG12*、JNZG14*、JNZG15*、JNZG311*、JNZG313*)聚在暹羅炭疽菌(Colletotrichum siamense)進化分支上(自展率94%)。

圖4 利用最大似然法基于棗炭疽病菌ACT、CHS-1、GAPDH、ITS、CAL和TUB2 的基因數(shù)據(jù)構(gòu)建的系統(tǒng)發(fā)育樹。 (自展率標于節(jié)點處,所用模式菌株由粗體表示,以Colletotrichum boninense MAFF305972 為外圍菌株,標尺指示0.02 步變化。 )Figure 4 Phylogenetic tree of isolates of red-fleshed apple anthracnose with allied taxa calculated with sequence data of concatenated ACT,CHS-1, GAPDH, ITS, CAL, and TUB2 using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1,000 bootstrap replicates; bootstrap values indicated at nodes, the highest log likelihood =-8965.61).
結(jié)合分離菌株的形態(tài)特征、培養(yǎng)性狀、多基因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以及致病性測定,明確了暹羅炭疽菌可以引起棗炭疽病。
3 結(jié)論與討論
炭疽菌屬植物真菌1790年首次發(fā)現(xiàn),1831年建立炭疽菌屬,距今已有230 余年的歷史,其分類一直比較混亂。依靠形態(tài)特征、寄主范圍為主的分類系統(tǒng),以及ITS 序列對復(fù)合種內(nèi)的近源種不能有效區(qū)分。 直到2009年Cai et al 提出了利用多基因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結(jié)合形態(tài)學(xué)并輔助其它鑒別手段的綜合方法,逐漸被接受,成為目前比較權(quán)威規(guī)范的炭疽菌分類方法。 棗炭疽病是棗樹生產(chǎn)中常見的一類重要的植物真菌病害, 國內(nèi)已有的報道認為其病原為膠孢炭疽菌(C.gloeosporioides),其分類依據(jù)主要依靠形態(tài)學(xué)特征或輔以ITS 序列分析。 本實驗通過感病棗葉樣本組織分離、 單孢純化、致病性測定,表明分離獲得單孢菌株均可以引起棗炭疽病。 通過對分離菌株ITS、CAL、TUB2、GAPDH、ACT、CHS-1 等多基因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 結(jié)合形態(tài)特征、 培養(yǎng)形狀, 確定分離獲得菌株為暹羅炭疽菌(C.siamense)。 本次研究結(jié)果首次明確了暹羅炭疽菌可以危害棗(Z.jujuba),引起炭疽病,這與已有的棗炭疽病原種類報道不同。
近年來,國內(nèi)外學(xué)者在蘋果、核桃、芒果、草莓、辣椒[12]等寄主上發(fā)現(xiàn)多種炭疽菌侵染危害。隨著炭疽菌屬真菌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確實存在多種炭疽菌侵染同一寄主的現(xiàn)象。 臺灣青棗(Z.mauritiana)炭疽病病原已被證實存在果生炭疽菌 (C.fructicola) 和暹羅炭疽菌(C.siamense)等2 種病原菌[13]。 臺灣青棗又稱印度棗、毛葉棗,為鼠李科棗屬植物,與Z.jujube 均為棗屬,是否存在果生炭疽菌侵染危害Z.jujube,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次實驗受采樣地點和采樣數(shù)量的限制,僅分離獲得暹羅炭疽菌一個種,隨著今后采樣量的增加,是否會有其它炭疽菌或炭疽菌新種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暹羅炭疽菌是Prihastuti et al (2009年)在泰國咖啡上首次發(fā)現(xiàn),引起咖啡炭疽病[14]。 暹羅炭疽菌分布范圍廣,已在非洲、美洲、大洋洲、亞洲均有發(fā)現(xiàn)[15-18]。 隨著對暹羅炭疽菌的關(guān)注,危害寄主的種類范圍越來越廣,本研究首次發(fā)現(xiàn)暹羅炭疽菌侵染棗引起炭疽病,棗是其新寄主。 因此,在棗炭疽病研究及制定防控方案時,暹羅炭疽菌同樣是不可忽視的。 目前,有關(guān)暹羅炭疽菌引起的棗炭疽病的發(fā)生流行、種群結(jié)構(gòu)以及有效的防治措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