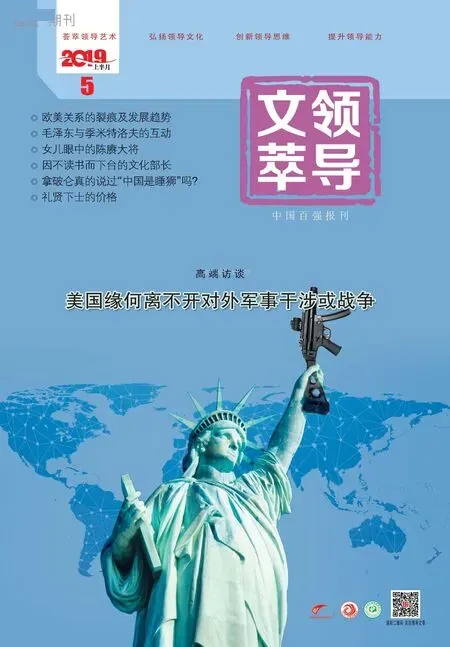破除二元結構是未來15年的重要任務
蔡昉

基于“十四五”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我國2025年要成為高收入國家,2035年要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這是一個定性和定量結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國GDP總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約也要翻一番。同時,根據(jù)居民收入與經(jīng)濟增長基本同步的要求,城鄉(xiāng)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邏輯,一方面,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共同富裕的一項重要要求,另一方面,推進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過程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和手段。目前,我國正處于破除二元結構的窗口期,緊迫性與機遇并存,通過破解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三農(nóng)”發(fā)展也可以對中國經(jīng)濟增長作出自身貢獻。
首先,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仍然偏大。雖然在過去十余年中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從基尼系數(shù)仍然顯著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貢獻來自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這個情況可判斷,我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仍過大。這也說明,在任何國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需要通過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數(shù),同時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務尚不均等。從某種程度上看,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還大。
再次,不徹底的城鎮(zhèn)化降低社會流動性。現(xiàn)行戶籍制度造成城鎮(zhèn)化的不徹底性和不完全性,進而降低了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不充分表現(xiàn)在很多方面,非正規(guī)就業(yè)是其中一個重要體現(xiàn)。我國未落戶農(nóng)民工在城市就業(yè)大多數(shù)屬于非正規(guī)類型。目前城鎮(zhèn)就業(yè)中個體就業(yè)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至少占全部就業(yè)的30%。非正規(guī)就業(yè)意味著就業(yè)不穩(wěn)定、工資報酬偏低、社會保險覆蓋不充分,以及職業(yè)提升空間小。就業(yè)非正規(guī)化嚴重降低了社會流動性,尤其是減少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此外,戶籍身份的固化還降低農(nóng)民工外出、出縣、出省和進城的比例,并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兒童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進一步降低了社會流動性。
這些問題如何影響我國未來15年實現(xiàn)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目標?這需要從中國經(jīng)濟面臨的挑戰(zhàn)來看。首先,中國的人口在加速老齡化,因此一個重要的挑戰(zhàn)就是應對即將來臨的第二次人口沖擊。在過去十余年的時間里,我們已經(jīng)度過了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對中國經(jīng)濟的沖擊,即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頂峰后,開始以每年幾百萬的速度負增長。由此產(chǎn)生的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放慢、資本回報率下降、生產(chǎn)率提高速度放慢等,為中國經(jīng)濟帶來了供給側的沖擊。
2025年之前,我國將達到總人口的峰值,隨后進入人口負增長,即第二個重要的人口轉折點。這對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將造成新的需求側沖擊,如何實現(xiàn)潛在增長率將成為新的挑戰(zhàn)。具體表現(xiàn)為三種效應不利于居民消費:第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數(shù)量停滯,消費需求也就停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消費也會負增長。第二是年齡結構效應。由于中國老齡化嚴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覆蓋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不足,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難以擴大。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由于富人傾向于儲蓄,而窮人又滿足不了消費意愿,因此,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的不足、過度的儲蓄,從需求側抑制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
我們可以以國外機構對中國經(jīng)濟的悲觀預測作為參照系,看應對這些挑戰(zhàn)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凱投國際認為中國由于未來勞動力增長是負的,因此難以實現(xiàn)自己的增長目標,預計中國不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jīng)濟體。悲觀的預測主要基于兩個原因:第一,伴隨老齡化加深,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將是負增長,削弱了經(jīng)濟增長潛力,這是供給側的因素;第二,中國人口負增長抑制消費,使既有增長潛力不能實現(xiàn)。這兩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我們可以以供給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側(居民消費)改革為著力點,通過消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應對經(jīng)濟增長挑戰(zhàn)。
首先,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是關鍵。目前,我國80%的農(nóng)業(yè)勞動力人均對應的耕種面積僅在1畝到7畝之間,對比一些國家家庭農(nóng)場擁有的大規(guī)模土地面積,中國農(nóng)業(yè)的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受到土地規(guī)模的嚴重制約。據(jù)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jù),我國農(nóng)業(yè)勞動力人均生產(chǎn)率為3830美元/年,僅為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應對這個問題,一方面要靠分子效應,即依靠科技提高單位勞動的農(nóng)業(yè)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應,即通過向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轉移減少單位產(chǎn)出使用的勞動力。
其次,勞動力轉移和城鎮(zhèn)化助力經(jīng)濟增長。假設在“十四五”期間,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比重降低10個百分點,即從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農(nóng)勞動力供給可以增加2.7%。這就否定了凱投國際等關于中國未來勞動力是負增長的假設。這就是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即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來增加勞動力供給,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
再次,規(guī)模經(jīng)營既有潛力也有需求。小農(nóng)戶利用各種生產(chǎn)社會化服務,在實際擁有的耕種面積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xiàn)規(guī)模經(jīng)營,獲得規(guī)模經(jīng)濟收益。
最后,科技創(chuàng)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產(chǎn)品市場創(chuàng)新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包括豬循環(huán)的難題。難點不在于創(chuàng)新能力,而在于農(nóng)業(yè)比較效益低、在技術上存在免費搭車現(xiàn)象,因而不能產(chǎn)生創(chuàng)新激勵。因此,第三次分配領域不僅要倡導慈善事業(yè),更主要的是鼓勵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包括倡導科技向善。
綜上,消除二元結構是未來15年重要的改革任務,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誤。從這里的分析來看,這些改革都可以產(chǎn)生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從供給側看就是提高潛在增長率,從需求側看就是擴大居民消費,以保障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xiàn)。當我們把改革舉措落在了鄉(xiāng)村振興的整個過程中,改革紅利也就可以成為戰(zhàn)略實施的動能,可以解決鄉(xiāng)村振興的資金來源和激勵來源等難題。
(摘自《理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