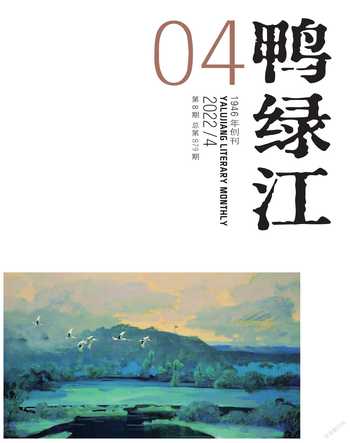喚醒(組詩)
空房子
把腳步移出來,把心裝進去
黃泥墻,黑土瓦,木制門
算是最好的朋友了
剩下的還有四壁,站在原地
風掠過,尚存的氣息
是先父咳嗽的回音
母親虛脫的汗漬
不約而同地涌出來
給舊時光握手道別
一個下了地,一個進了城
如同被季節錯過的稻田
漸漸荒蕪。情感的負罪
套牢了余生的悟性和寄托
房子空了,村莊空了,心空了
在澆筑鋼筋水泥的日子里
一個轉身,記憶里的空房子
不經意間就顯山露水
稻香
體內的脂肪越積越厚
盤中餐,我們更加熟稔
香米、貢米、御貢米、珍珠米
陳列在超市貨架上的差價
卻很少關注,鄉下稻草長高的方式
這些在我生命里繁復的漿果
如何歷經揚花、下彎、散籽的陣痛
又怎樣喂養過我們殘缺的童年
那些年的稻香,是一個村莊的根須
被血色和汗水喂養
是父親和母親常年的焦慮
時光的營養饋贈我們太多
擱淺在農事之外,從稻香里走出的足跡
不忍拒絕城市的霓虹
村莊的孤獨漫成了生活外的眺望
只有那些困守的父老鄉親
還在一年四季背著太陽,用雨水和節令
培育稻香,卻無法醫治
城市的忙碌和健忘
咀嚼稻香,就是
咀嚼一個時代的沉浮
喚醒
寒光,一次次劃開負重的日子
老祖宗告訴我“刀不磨要生銹”
我又一次,目睹水和陽光
碾過歲月的疼。那么鋒利的刀
在時光面前撐不起腰,銹跡斑斑
故事的結尾,總會逆向而行
看似終點,又是開端
在石頭上霍霍幾下
鎖眉之后,重見天日
消失
說消失就消失,措手不及
那些走鄉串戶的挑擔
生長在記憶深處的呼聲
被推土機鋼筋水泥侵占
被慌亂的雜草擠推
隱隱約約的炊煙被風吹散
飄到了河的另一岸
熟悉的影子呢,不再屬于我
一群鳥從上空飛過去
連鳥屎也沒留下一粒
有車經過村莊,一個急剎
滿滿的鄉愁溢了出來
沒能驚醒柴門里的犬吠
也許,它正躲在蒼涼的氣氛中
黯然神傷
提及舊事
那時候我們都還小
赤著腳,在枯槁的陽光下
泥鰍一樣滑溜
高舉棍棒咿咿呀呀
嘴邊纏繞著英雄的名字
拖著清鼻涕越跑越快
丈量,整個村莊四季的風
喘息聲還未平息
眉目之間,翻越一年又一年
今天,我們是自己的英雄
在酒杯間豪氣干云
突然就炸開了關于舊事的記憶
年幼時的那些棍棒
就像卡在喉嚨里的刺
一吐為快
草
背“草背篼”的年齡
奢望漫山遍野都是草
手里的刀輕輕一揮
就能填飽耕牛簡單的欲望
事實上,是要踏遍溝溝壑壑
占領遙遠的地方
從遙遠的地方回來
厭惡極了眼前漫山遍野的草
只是一個轉身,就淹沒了
父親那本已荒蕪的墳頭
趕馬人
路過村莊,一條響馬鞭
孤獨的鞭梢直指晨曦
轉眼間就到了黃昏
青草和枯葉的顏色沒有區別
心無旁騖地走路,趕馬,吆喝
使喚整個村莊的柴米油鹽
東家長西家短之外游動的影子
一輩子都沒停下
反芻數十年的光陰
生活是一條走不完的路
遠方在延伸,那里有兩座墳墓
一座屬于自己
一座留給驅趕的馬匹
宿緣
無須四處尋覓,到了季節
去安放我疲憊的鄉村
就近種下大豆、高粱、稻谷、紅薯
生活的邊角地帶
花花草草天生素顏,沒有上鎖
任憑裝進兩眼的倉庫
不做仗劍的俠客
用鋤頭敲打土地的背脊
莊稼和花草醒過來
像是天生慧根,與我結下一世宿緣
味道
我的身上總帶有泥土味
時而夾雜著汗味
偶爾還有牛屎馬尿味
因此,我與這座光鮮的城市
在某些細節上格格不入
我曾用城市的自來水
涂抹香皂,高檔的洗發水、沐浴液
一次,兩次,無數次
沖刷掉那些味道
偶有事實在短期內幻化成假象
眼睛騙不了感同身受
我總能嗅到存留在我身上的味
恍若相依為命的愛情
誰也離不開誰
扔不掉的就留下吧
這個城市里,與我味道相同的
還是大有人在。忽略那些味道
我們就不再是我們了
那就等同于沒有根的浮萍
一切都是虛的
兩棵桃樹
老桃樹上掉下一個桃子
入土,生根。小桃樹
從果實里獲取生命密碼
坐在搖籃一樣,晃悠晃悠
長高了,掛果了
風吹過來,愈發滄桑的老桃樹
柔聲對小桃樹說
好啊,你也當母親了
游戲
找個同齡人,一起回到十來歲
席地而坐,用剪刀石頭布玩游戲
一筆一畫,就像一磚一瓦
多么富有啊,有城堡,有槍炮
一段歷史復活在面紅耳赤的爭論之間
互相攻打
你轟了我的炮,我奪了你的旗
最后剩下的,只有那么多橫豎交織的線條
一段厘不清的記憶
消失在歲月的游戲中
作者簡介:
蘭采勇,刊物編輯,中國詩歌學會會員,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重慶市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偶有詩文發表,已出版個人作品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