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因婚致貧的人
□ 宋 曉
一
婚禮前的一個月,張鈺哲去未婚妻家吃飯,岳母在飯桌上從家里近況問到婚后計劃,話題最終繞到彩禮上。
自從2019 年哥哥結完婚,家里給出10 萬彩禮后,剩下的錢只夠勉強給張鈺哲辦一場婚禮。岳母提出要8 萬彩禮,張鈺哲希望未婚妻理解自己的難處,卻也實在不好意思開口,在當地,這個數字并不算高。
婚禮和婚宴在縣城一家有些年頭的酒店舉行,跟近幾年新開的、裝修得富麗堂皇的新酒店相比,這家酒店的消費水平還能讓張鈺哲承受。兩家人商量好,各收各的禮金,酒席錢張鈺哲家付。婚禮前一晚,張鈺哲和父母在客廳里坐著烤火,翻出了家里的人情賬本,粗略算了一下,禮金能收回十來萬元,再加上張鈺哲打工攢下來的三四萬元,應該足夠支付婚禮成本和彩禮。
由于女方家親戚太多,酒席增加了11 桌。敬酒的時候,張鈺哲不自覺計算著,光是酒席,就比原計劃多了2.6 萬元。
這場婚禮收來的11 萬禮金最終全部搭進婚禮,沒有一丁點兒剩余。張鈺哲不忍心讓父母再去借錢,為了承諾的彩禮,他以創業需要錢為理由找高中同學借了5 萬元。
婚禮只是開始。
一個來自湖南某縣城的男青年看見朋友在婚禮酒席上花了30萬元,表示難以理解:就算請所有親朋好友吃頓飯,要花這么多錢嗎?別人向他“科普”:婚禮酒席并不只是吃頓飯的事情,伴手禮、請柬、策劃、婚禮布置、酒店、場地,樣樣都要花錢。但他還是覺得荒唐,“30 萬,兩個人可以環球旅行了”。
一個北京男青年坦白,自己特別逃避算結婚賬。彩禮和宴請親朋的費用都不算什么,但房價是真沒轍。以他每月一萬元出頭的工資,靠自己買房是不可能的:按照大多數同齡人的購房模式,家里出完首付,自己還月供,那將是一筆“巨款”。沒結婚還能住家里,對他來說,結婚可能就是踏上了“貧窮之路”。
二
更多普通人的婚姻,沒有遭遇彩禮帶來的痛苦和撕扯,但婚姻帶來物質生活水平的下降,藏在生活的細節里。
沒有任何緩沖期,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進入婚姻之后,章子云工作8 年攢下來的10 萬元錢迅速散去,買房、裝修、買家具讓她和丈夫幾乎花光積蓄。
隨之而來的是婚后的各種人情往來。婚后的第一年就趕上表弟、表妹相繼結婚,到手的禮金這就還回去了。因為遠嫁東北,回老家的路費也是不低的成本。表弟結婚那段時間,算上禮金和機票,她花了當月一大半的工資。
算起來,雖然完成了人生里一個重大任務——買房子,住得也更舒服了,但婚后從未停止的支出,使得危機感一直壓著章子云。婚后好幾年,她都覺得“緩不過來了”,更沒有可能再恢復以前的生活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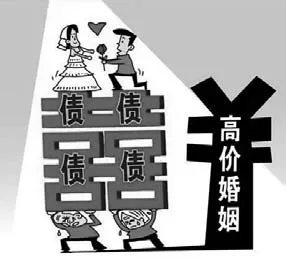
消費自然是呈斷崖式下跌的,以前章子云會用外國品牌的化妝品,現在,她的梳妝臺上幾乎全是“平價替代品”。她開始干自己以前絕對不會干的事情:蹭奶茶店的椅子歇腳,但不點一杯奶茶。衣服幾乎不買了,一年有兩套能穿出去的就行。
同樣“消費降級”的還有郭杏兒。
婚前的郭杏兒沉迷于各種文藝生活,一周要進兩次電影院,各種影展、藝術展、書店新上的文創產品都不會錯過。2020 年結束的時候,她翻看豆瓣的年度總結,自己標記的電影數從前兩年的300 多部下降到了17 部。
小兩口結婚后,雙方父母和兒女的相處模式迅速發生了變化。結婚以前,郭杏兒的婆婆即使身體不舒服,也不會打擾兒子。但是婚后有一次,郭杏兒帶著婆婆去醫院,門診不能報銷,檢查費用和醫藥費花了她不少錢。郭杏兒的父母也開始考慮以后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打電話的時候,得知父母最近看好一塊公墓,她主動打過去幾萬塊。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肆意生活一去不復返了。她意識到,婚后最大的變化是自己不再被當作小孩,女兒的、妻子的和兒媳婦的責任在這一年里同時降臨。
三
不同于以上兩位女性在變化的家庭關系里窺尋婚姻里的經濟關系,張雯是在走向離婚的時候,才從寫滿了財產權利和義務的離婚協議書上意識到,或許當初根本忽略了婚姻究竟意味著什么。
張雯的婚姻是以一沓18 頁的離婚協議收尾的。這個在美國讀博、始終記得要做現代獨立女性的女青年,在憧憬中走進婚姻。但婚姻遠比她想象的復雜。
這段婚姻并沒有持續太久。她無法忍受“喪偶式”育兒,疲于平衡讀博和母職,產后2 個月,她靠著止疼藥坐進了課堂,直到痛感麻木。
但這些勞動無法被看見。反過來,哪怕丈夫一丁點兒家務、育兒的勞動都不貢獻,自己掙的錢,他都有權分一半。假如突然離世,自己的養老金、壽險、意外險等很多保險,也許全部都是丈夫的。而婚姻存續的時間越長,離婚時丈夫便越有理由索要配偶贍養費。在離婚協議書上,她把這些項目一項一項解除。
張雯的婚姻所遭遇的更像是一種隱形的貧困,因為不涉及房產分割或家庭儲蓄分割,兩人都沒有損失什么,也沒人因此獲利。可是在婚后,張雯的經濟卻沒有那么自如了。她和丈夫約定好,家庭開銷按照40%和60%的比例攤銷,自己少出的那10%是因為計入了生育成本。頭幾年,自己的博士獎學金足夠支撐她的生活,但生完孩子之后,由于同時面臨著育兒壓力和博士畢業的壓力,經濟開始拮據起來,她不得不借錢支付生活開銷。
如果說這段婚姻讓張雯得到了什么,她覺得是“一些教訓”。
律師吳杰臻曾在接受采訪時總結,現在女性雖然在社會上獨立了,但是一到婚姻里面,存在一種“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慣性,加上生育這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很容易回到那種女性默認犧牲的模式,又變成被動的角色。
維系或者摧毀一段婚姻,金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愛和浪漫,婚姻里還充滿了各種經濟考量。
財產問題從不同的將要步入婚姻的年輕人口中問出來,卻又如此相似:房子如何署名?如何還貸?彩禮屬于誰的財產?萬一離婚了要退還嗎?
經濟上的較量有時候到了瘋狂的程度。律師張荊在過往的法律咨詢工作里,接觸過大量的婚姻樣本。她見過一對夫妻來簽婚前財產協議,男方提出家里的房子要算成婚前財產,不管將來產生的收益如何,都是男方所有。女方緊接著提出,自己將來繼承父母的兩套房時跟男方沒關系。吵到最后,連工資里多出來的1萬塊錢也要排除在共同財產之外,兩人不歡而散。
這種計較甚至會延續到婚姻關系解體之后。張雯離婚后,由于丈夫尚未全職工作,只規定了付14%的孩子撫養費。她每個月給丈夫發賬單,其實根本沒有多少錢,有時候一件小物品的14%只有幾塊錢,丈夫也堅持要看支付憑證,甚至讓她證明錢確實是給孩子花了。她無法忍受這些經濟上的低級糾纏,現在賬單也不發了,自己獨自撫養孩子。
談戀愛時誰也沒想過會因結婚而“返貧”。但事實是,從婚姻開始到結束,甚至離婚以后的日子,每一步都可能有人在其中變得更“窮”。
“變窮”,或許對一些人來說,也是維持婚姻關系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