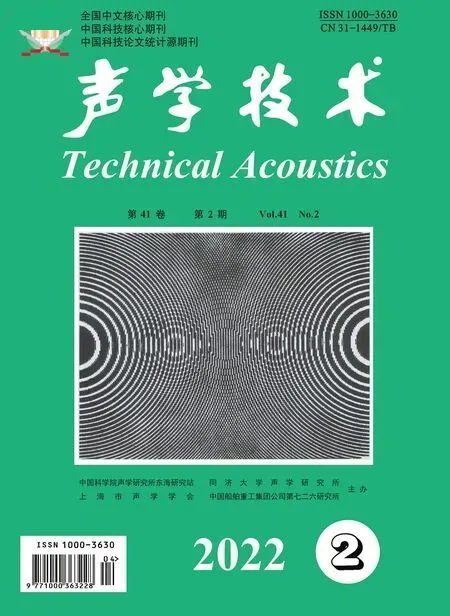樂罩對劇院音質參量的影響分析
李佳菊
(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聲學及劇院專項設計研究所,上海 200011)
0 引 言
劇院是用來表演戲劇、歌劇等的演藝場所,因為演出需要,通常配備有相當大的舞臺,呈現(xiàn)給觀眾的是臺口部分,供大眾欣賞演藝。音樂廳的舞臺(演奏臺)通常完全暴露,樂隊在演奏臺上使用自然聲進行交響樂演出。當劇院設置自然聲演奏音樂功能時,舞臺上需設置樂罩。樂罩是有自然聲演出功能劇場舞臺表演區(qū)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是防止有限的自然聲能被舞臺吸收和逸散,并為樂師提供良好的相互聽聞[1]。
最早的樂罩產(chǎn)生于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劇院通常采用臨時吊置三夾板、帆布刷油漆等輕質材料的反射板來改善在劇院內自然聲演出時的音質,獲得了較好的效果。1974年,因中央樂團和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來華演出,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劇場舞臺設置了我國第一個封閉式樂罩[2]。樂罩的廣泛使用,充分發(fā)揮了劇院的使用效率,豐富了劇院的演出形式。樂罩的形式有敞開式和閉合式。樂罩的材質也分為輕型和重型。經(jīng)過時間的驗證和從實用的角度考慮,目前比較流行的是輕型閉合式樂罩,如哈爾濱大劇院樂罩,如圖1所示。

圖1 哈爾濱大劇院樂罩照片F(xiàn)ig.1 The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in Harbin Grand Theatre
1 音質參量
音質參量是用來客觀描述音質特征的物理量,可由實測獲得。音樂的混響感,通常用音質參量的混響時間和早期衰變時間來表征;音樂豐滿度用音質參量明晰度來表征;音樂的響度用音質參量強度因子來表征;音樂的空間感用音質參量早期側向聲能比和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來表征,樂師間的相互聽聞用音質參量舞臺支持度來表征[3]。
數(shù)據(jù)樣本從50多座劇院的實測數(shù)據(jù)(測試標準參考ISO3382[4])中選取了上海大劇院、哈爾濱大劇院、北京保利大劇院、重慶大劇院、無錫大劇院、嘉定保利大劇院、武漢琴臺大劇院、大連達沃斯會議中心大劇院、東莞玉蘭大劇院、廈門嘉庚藝術中心大劇院、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重慶施光南劇院、恩施州文化藝術中心劇院、上海文化廣場劇院、深圳南山文體中心劇院、上海城市劇院、福建大劇院大劇場、孝感市文化中心大劇院、杭州大劇院、敦煌大劇院、海口灣演藝中心、青島城陽大劇院、深圳光明文化藝術中心大劇院、廈門思明劇院,共24個完善的廳堂為樣本庫,對24座劇院加樂罩前后聲場空場的混響時間、早期衰變時間、明晰度、強度因子、早期側向聲能比、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舞臺支持度實測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分析。
2 樂罩對劇院音質參量的影響統(tǒng)計
2.1 混響時間
混響時間T30是聲能從-5 dB衰減到-35 dB所需的時間,是最重要的音質參量。24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混響時間平均值對比如圖2所示。

圖2 24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混響時間平均值對比圖Fig.2 Average reverberation times of 24 theatre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the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從圖2可以看出,24座劇院加樂罩前的中頻(500~1 000 Hz)混響時間平均值是 1.55 s,加樂罩后的中頻混響時間平均值是 1.78 s,中頻混響時間平均提升量為 0.23 s。加樂罩后,中高頻混響時間有比較大的提升,但是在低頻,特別是125 Hz,增量為-0.17 s。
圖3為加樂罩后中頻混響時間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圖。從圖3可以看出,加樂罩后的觀眾廳中頻混響時間的增加量落在0.18~0.28 s的最多,有16座。加樂罩前后 24個大劇院的中頻混響時間增量的平均值為0.23 s,標準差為0.082 s。

圖3 加樂罩后中頻混響時間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圖Fig.3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of mid-frequency reverberation time increment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2.2 早期衰變時間
早期衰變時間(Early Dccay Timc, EDT)是由聲源停止后聲能最初衰減10 dB所需的時間推算得到衰減60 dB所需的時間。早期衰變時間與人耳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
加樂罩前后,早期衰變時間數(shù)據(jù)有效的劇院有23座。23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早期衰變時間平均值對比如圖4所示。圖4可以看出,在加樂罩前,23座劇院的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平均值為 1.32 s,加樂罩后,23座劇院的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平均值為1.64 s,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平均提升量為0.32 s。

圖4 23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早期衰變時間平均值對比圖Fig.4 Average early decay times of 23 theater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the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加樂罩后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如圖5所示。從圖5可以看出,加樂罩后的觀眾廳中頻早期衰變的增加量落在 0.23~0.4 s的最多,有14座。加樂罩前后23個大劇院的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增量的平均值為0.32 s,標準差為0.11 s。

圖5 加樂罩后中頻早期衰變時間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圖Fig.5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of mid-frequency early decay time increment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2.3 明晰度
明晰度C80為早期聲能與后期聲能的比值,單位為dB。其中,早期聲能指0~80 ms內到達的聲能,而后期聲能則為80 ms以后到達的聲能。加樂罩前后,明晰度數(shù)據(jù)有效的劇院有23座。C80的表達式為

式中:p(t)指脈沖響應在測點位置處的瞬時聲壓。23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明晰度平均值對比如圖6所示。加樂罩后明晰度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如圖7所示。圖7中的明晰度C80(3)是 500 Hz、1 kHz、2 kHz三個倍頻帶的明晰度值加以平均。不同的演出形式C80適應的最佳值不同。加樂罩前后,明晰度有效數(shù)據(jù)有23座劇院。23座劇院加樂罩前的C80(3)為2.5 dB,加樂罩后的C80(3)為-0.32 dB。

圖6 23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明晰度C80(3)平均值對比圖Fig.6 Average clarityC80(3) of 23 theatre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the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圖7 加樂罩后明晰度C80(3)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圖Fig.7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of clarityC80(3) increment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加樂罩后的觀眾廳C80(3)的增加量在-3.42~-1.64 dB(中值-3.42 dB,-2.53 dB,-1.64 dB)的最多,有18座。加樂罩前后23個大劇院C80(3)增量的平均值為-2.53 dB,標準差為0.89 dB。
2.4 強度因子
強度因子G是指從一無指向性聲源到達廳堂中某一座席處的聲能,與同一聲源在消聲室中10 m距離處所測得的聲能之比再取對數(shù)值[5],單位為dB。加樂罩前后,強度因子數(shù)據(jù)有效的劇院有 20座。20座劇院加樂罩前后強度因子平均值對比如圖8所示。加樂罩后Gmid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如圖9所示。圖9中的強度因子Gmid是 500 Hz、1 kHz兩個倍頻帶的強度因子加以平均。

圖8 20座劇院加樂罩前后強度因子平均值對比圖Fig.8 Average strength factors G of 20 theater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圖9 加樂罩后Gmid增加量正態(tài)分布曲線圖Fig.9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 of strength factorGmidincrement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20座劇院加樂罩前的Gmid為 1.46 dB,加樂罩后的Gmid為4.0 dB,加樂罩前后各頻率強度因子有顯著提升。加樂罩后的觀眾廳強度因子Gmid的增加量落在1.972~3.173 dB(中值 2.572 dB)的最多,有14座。加樂罩前后20個大劇院的強度因子Gmid增量均值為2.57 dB,標準差為0.8 dB。
2.5 早期側向聲能比和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
早期側向聲能比JLF表示接收位置上前 80 ms內從側面到達的聲能與總聲能的比:

其中:p8(t)是指用“8字型傳聲器接收到的瞬時聲壓;p( t)是指用脈沖響應在測點位置處的瞬時聲壓。JLF應該是全頻段的,但是我們一般計算JLF(4)作為單值評價量,JLF(4)是 125 Hz、500 Hz、1 kHz,2 kHz 4個倍頻帶的早期側向聲能比加以平均。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IACC是某一瞬間到達兩耳的聲音的差異性的量度。IACC是0時,說明兩耳上的聲音完全不同。
加樂罩前后,早期側向聲能比和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的有效數(shù)據(jù)有12座劇院。12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早期側向聲能比平均值對比如圖10所示。12座劇院加樂罩前后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平均值對比如圖11所示。圖10、11顯示,12座劇院的早期側向聲能比和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變化不顯著。

圖10 12座劇院加樂罩前后早期側向聲能比JLF(4)平均值對比圖Fig.10 Average early lateral reflection energy ratiosJLF(4) of 12 theatre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圖11 12座劇院加樂罩前后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IACC平均值對比圖Fig.11 Average double-e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ACCof 12 theatre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2.6 舞臺支持度
舞臺支持度ST-carly定義為距離無指向性聲源1 m處測得的直達聲后最初10 ms內到達樂師位置的聲能與同一位置處 20~100 ms內到達的聲能之比,表達式為

加樂罩前后,舞臺支持度的有效數(shù)據(jù)有4座劇院。4座劇院加樂罩前的平均ST-carly為-18.9 dB,加樂罩后的平均ST-carly為-11.11 dB。4座劇院加樂罩前后舞臺支持度平均值對比如圖12所示。由圖12可以看出,加樂罩前后舞臺支持度有顯著提升,平均提升了7.8 dB。

圖12 4座劇院加樂罩前后舞臺支持度ST-carly平均值對比圖Fig.12 Average stage support degreesST-earlyof 4 theatres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3 總 結
3.1 加樂罩前后數(shù)據(jù)
表1中為加樂罩前后T30、EDT、C80(3)、Gmid、JLF(4)、IACC等音質參量的增加量和它們的標準差。

表1 加樂罩前后的音質參量變化匯總Table 1 Summary of acoustic quality parameter increments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3.2 觀眾廳角度
3.2.1 混響感
混響時間和早期衰變時間是表征混響感的音質參量。
混響時間加樂罩前后,混響時間增加量平均值為 0.23 s,增加量最多的是北京保利大劇院和敦煌大劇院,增加量為 0.39 s。但是在低頻,特別是125 Hz,增量為-0.17 s。分析原因是樂罩通常為紙蜂窩結構或者鋁蜂窩結構,此種構造面密度比較低,對低頻聲能吸收很大,導致低頻混響時間呈負增加。吸聲系數(shù)曲線如圖13所示。

圖13 樂罩吸聲系數(shù)曲線Fig.13 The acoustic absorption coefficient curve of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如要提高低頻混響時間的增量,可以考慮增加樂罩的面密度。因樂罩過重會增加舞臺的荷載,從而需要性能更高的舞臺地面,進而會增加工程的造價。因此合理控制樂罩的面密度,使其吸收掉的低頻聲能在合理范圍內即可。
加樂罩后,早期衰變時間增幅較明顯。加樂罩后的觀眾廳中頻早期衰變的增加量最多的是上海大劇院,增加量為 0.57 s。很多劇院因為臺口八字墻的角度受到音箱室的位置限制,有時在聲學有效反射的位置進行音響口開洞,從而減少觀眾廳早期反射聲的覆蓋,樂罩的出現(xiàn)較好地彌補了這一點,為觀眾廳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早期反射聲,從而提升了音質參量。
3.2.2 明晰度
明晰度是表征音樂演奏過程中可分辨程度的物理量,與豐滿度是相對的物理量,C80越大,音樂的明晰度越高,豐滿度越低。加樂罩后的樣本中,明晰度變化量最大的是北京保利大劇院,明晰度的增量為-3.8 dB。樂罩對明晰度的改善均衡了大劇院在演奏交響樂時音樂的清晰度和豐滿度。
3.2.3 強度因子
強度因子表征響度的物理量,加樂罩后的觀眾廳中頻強度因子的增加量均值為 2.57 dB,增加量最多的是上海文化廣場,為4.2 dB。20座劇院的低頻125 Hz強度因子G125增加量均值為1.9 dB,低頻強度因子G125增加量相對中頻強度因子較弱,跟樂罩的聲學特性有關。G125與音樂的溫暖感有關,加樂罩后劇院的G125均值為4.2 dB,而交響樂廳通常有較高的G125值,根據(jù)華東院聲學所《劇院音樂廳音質參量的檢測和深入研究》[6]課題研究成果,國內 17個 1 200座交響音樂廳的G125均值為5.4 dB。這可能是一些指揮家認為音樂廳無可替代的原因之一。
3.2.4 空間感和親切感
早期側向聲能比和雙耳互相關系數(shù)是表征廳堂中空間感的客觀參量。空間感是指聽眾在廳堂中產(chǎn)生的被聲音所包圍的感覺。
空間感與親切感因與劇院的體型設計密切相關,加樂罩前后,劇院觀眾廳的體型并未發(fā)生變化,故音質參量JLF、IACC變化不顯著。
3.2.5 觀眾廳脈沖響應
以孝感市文化中心大劇院為例,觀眾廳加樂罩前后的脈沖響應如圖14所示。樂罩對舞臺進行了物理上的隔離,在增加體積的同時,減少了吸聲面,每座容積隨之增大,代表房間聲場屬性的脈沖響應發(fā)生了變化。這對聲場的改變是根本性的,從而會伴隨各音質參量的變化。

圖14 孝感市文化中心大劇院加樂罩前后觀眾廳脈沖響應對比圖Fig.14 The pulse responses of the auditorium in Xiaogan Culture Center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3.3 舞臺角度
3.3.1 舞臺支持度
舞臺支持度是表征舞臺上樂師間的相互聽聞、樂聲的融合的物理量。
加樂罩前后,舞臺支持度改變量最大的是海口灣演藝中心,改變量為9.8 dB。
3.3.2 舞臺脈沖響應
以孝感市文化中心大劇院為例,舞臺加樂罩前后的脈沖響應如圖15所示。

圖15 孝感市文化中心大劇院加樂罩前后舞臺脈沖響應對比圖Fig.15 The pulse responses of the stage in Xiaogan Culture Center before and after assembling acoustic reflection cover
樂罩減少了自然聲被舞臺空間的稀釋,樂罩內部的聲能密度也明顯升高,豐富了早期反射聲。舞臺支持度的明顯變化說明了這一點。舞臺支持度的提高,很好地改善了樂師間的聽聞,促進了音樂的融合。
4 展 望
樂罩向著美觀和高效實用的方向發(fā)展。定制型樂罩,是追求美觀的設計師,結合觀眾廳的設計風格,對樂罩的外觀進行了藝術設計,使其和觀眾廳的裝飾風格融為一體。聲學改進型樂罩,是在樂罩的側板和后板上增加橫向水平板,聲音從樂器發(fā)出后,經(jīng)過側板和后板的反射,改變原本向上的傳播路徑,提前向下反射到舞臺區(qū)域,從而使樂隊獲得有效的二次向下反射聲,更好地提高樂師間的相互聽聞,激發(fā)了演奏者的熱情,使觀眾與演奏者產(chǎn)生共情,從而享受整個演出過程。
致謝感謝多年來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聲學及劇院專項設計研究所的同事對數(shù)據(jù)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