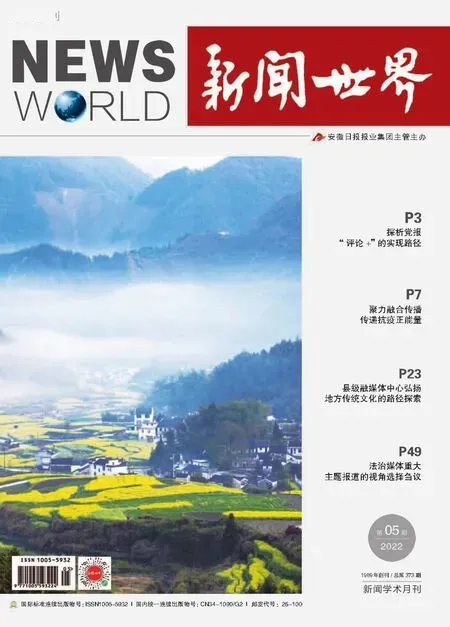全媒體視域下微紀錄片轉型路徑探究
孫華健
【摘? ? 要】在當今人人都可以成為傳播主體的時代,出現了全民媒體、全程媒體、全息媒體等。微紀錄片作為新媒體和互聯網結合的一種新形態,傳播能力較強,受到受眾的喜愛。隨著受眾需求增加、評判能力提高,微紀錄片要實現更好地發展,就必須加強內修外練,實現跨界融合。本文將分析全媒體視域下微紀錄片的現狀和特點,從選題角度、敘事創新、傳播規律等方面著手,探討微紀錄片在借鑒傳統紀錄片優勢的基礎上如何實現創新發展。
【關鍵詞】微紀錄片;全媒體;轉型
一、引言
全媒體時代下,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革新,人們接收信息的方式、審美的標準以及社會關系的建構等,都與傳統媒體時代產生了較大不同,體量小、主題鮮明、內容直觀的微紀錄片應運而生。作為短視頻主要傳播形式之一,它不僅能夠滿足新時代受眾多元化需求,還承載著意識形態建設、文化傳承發揚的社會責任。這一系列的變化使得微紀錄片在新媒體平臺和傳統媒體中蓬勃發展。
二、全媒體視域下微紀錄片的現狀及特點
(一)碎片化生態圈的建構
“微紀錄片”的概念最早由鳳凰衛視提出,一般指時長在10分鐘左右的紀錄片。“微”不僅表示時長短,還包括由制作技術決定的敘事策略、傳播互動、營銷方式的變化。“微”不等同于“短”、“小”、“淺”,而是全媒體時代下符合受眾碎片化閱讀需求、具有工業化制作流程和完備生態傳播鏈的概念闡釋,其內涵應包括“微而廣”、“微而深”、“微而全”等意義表達。
結合受眾的快節奏生活和碎片化時間,微紀錄片為提高傳播效率壓縮了單集時間,擴展了廣度和深度,每一集既獨立成篇,又統籌于共同主題之下。如央視大型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用每集5分鐘的電視短片講述一個個文物故事,將紀錄片扁平化、簡約化,順應了當下快、小、短的視頻潮流和傳播理念,打破受眾對文物高冷的固有認知和刻板印象,重構文物的現實環境生態。百集大型紀錄片《故宮100》以微視角選取敘事對象,通過某一特定的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來展現其歷史文化內涵。其作為微紀錄片的優秀作品,雖小但“精”,它的趣味感和生動性有增無減。
微紀錄片有別于傳統紀錄片,其秉持“快餐化”、平民化、片段化、非正式化的傳播理念,構建了完整的碎片化生態圈,是以短時長和微角度來適應全媒體視域下傳播特點的一種新形式。
(二)創作技術推動了跨類型微紀錄片的發展
一方面,手機、無人機、手持穩定器的更新換代促使人人都成為傳播主體。另一方面,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使得傳播方式更加全渠道化。為了提升微紀錄片的視覺沖擊力,在當下,移動鏡頭、延時攝影和航拍鏡頭成為每部片子的標配。通過電影化的剪輯對巨量的碎片化信息進行組合,對整體鏡頭語言的色彩性和美觀性進行精細化的后期制作,有助于提升影片質感。例如《如果國寶會說話》利用最新的3D掃描成像技術對國寶進行模型的重構,突出了細節刻畫并以多視角的方式描述了青銅樹由無到有的過程。三維立體與二維動畫創作技術,以及符合年輕人審美習慣的后期動畫賦予了國寶鮮活的生命,與新媒體技術相互結合推動了跨類型微紀錄片的發展。
全媒體視域下,新媒體的發展給微紀錄片與受眾的交互提供了便利,不僅可以通過線上或者線下的方式來進行“一對多”的傳播,通過評論、留言等來進行互動,還能通過這種傳播方式來進行商業性的有效契合。在央視微紀錄片《了不起的匠人》中,唐卡畫師以直播的方式展示了傳統西藏牦牛絨向頂級奢侈品轉變的過程,將東方的古典元素與現代西方藝術相融合,首創“邊看邊買”的營銷模式,實時向受眾推送購買鏈接,創新了互動模式。
(三)敘事手法的藝術化和敘事方式的故事化
微紀錄片注重選題角度的平民化,以迎合受眾碎片化的收視習慣,突出故事化和藝術化的敘事,對人們的身邊事進行符合時代需要的藝術化闡釋。較之于傳統紀錄片,故事化的集體記憶更加容易獲得受眾認同。在某種意義上,微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往往取決于對受眾情緒的調動能力,敘事手法的藝術化和敘事方式的故事化正是帶動受眾情緒的最主要手段。例如《故宮100》,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去觀察和記錄,立足于平和的講述姿態,依托于故事化的敘事方式,將宏大歷史聚焦于微觀人物,盡可能地調動了受眾情緒。在《再見紫禁城》中,影片以溥儀為第一人稱敘事視角,以主觀鏡頭為敘事角度,以故事化的敘事方式講述了倉皇而逃的末代皇帝,呈現出一段鮮活的歷史。
三、全媒體視域下微紀錄片的創新探究
(一)運用新技術,增強畫面美感
微紀錄片保持了紀錄片的客觀性和紀實性,如果一味地側重還原客觀事實,往往會導致畫面感染力較差。想要增強微紀錄片的美感,就必須運用新的技術手段來對畫面內容進行藝術化的再創造,達到增強視覺沖擊力的效果。《如果國寶會說話》在后期運用了大量的動畫特效和3D掃描影像技術,對文物進行影像建模重構形成立體化的動感,讓擬人化的鏡頭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進而引發情感共鳴。接收者若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閱歷還原領會出創作者的主觀情感和創作意圖,那么微紀錄片將更加具有審美趣味和真情實感。
微紀錄片的意蘊美不僅體現在解說詞合理地抒發情感,還體現在畫面和聲音的自然結合,三個主要因素結合的默契程度決定了整部微紀錄片質量的高低。為了使畫面和音樂的聯系更加密切,美食微紀錄片《早餐中國》每集都運用了不同的專屬音樂來營造食品的制作氛圍。在單集的微紀錄片中,解說詞可謂是重中之重,它既可以在觀眾觀看紀錄片的時候對畫面起到補充說明的作用,還能通過形象化的描述增強畫面內涵。例如北京電視臺的《中國夢365個故事》,每集3分鐘,通過解說詞展現記錄發生在百姓身邊的真實故事,在畫面、音樂以及解說詞共同建構的環境中,完成了對“中國夢”通俗化、形象化的闡釋。
(二)高光式人物塑造,傳播主流價值觀
刻畫人物形象是紀錄片藝術創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微紀錄片在塑造人物時主要通過展現某個人物最鮮明的特點和性格特征,以點帶面將整個人物形象展示出來。這就需要在大量的基礎人物素材當中,挖掘出最能展現人物形象的高光點進行展示,形成直擊心靈的情感傳播。也需要創作者深度接觸主人公,站在時代的角度上塑造人物形象,展現獨特價值。
在塑造人物的同時還需注重主流價值觀的引領,例如在抗擊新冠疫情、脫貧攻堅等主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著鮮明的價值引領作用,相對于其他微紀錄片的人物塑造更具有深厚的時代意義。在《武漢呼吸》中,主人公以普通人的情感經歷視角折射出宏大的抗疫視野和偉大的抗疫精神。高尚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流價值觀的呈現,能夠增強受眾民族自豪感、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三)重視多維度傳播,優化資源整合
在移動媒體時代下,受眾的需求逐漸向“短”“平”“快”轉變。對于微紀錄片時長的把控,在不同媒體平臺上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受眾應當有所細分。針對電視等傳統媒體,微紀錄片可以適當增加時長,以黃金時間段和年輕人休息時間段播出為主;而對于移動端,應壓縮時長。
擴展微紀錄片的發展空間和傳播渠道,就必須要重視多維度傳播策略,通過加強微紀錄片與“三微一端”的互聯互通,跳出單一維度電視媒介的傳播限制。短小的篇幅使得在移動終端上的隨時觀看、重復傳播變得便利化,再加上自媒體的興起和推動,使得1+1>2的傳播效果凸顯。在傳播策略上還要減少冗長的敘事,對于故事結構要做到簡明化和言簡意賅,創作風格與時俱進。例如《如果國寶會說話》,節目組充分考慮微紀錄片的碎片化傳播理念,將片頭片尾的畫外音做得符合年輕人的審美風格,年輕化的創作團隊敏銳地捕捉到更加接地氣的新鮮事物,將沉甸甸的中華文明輕松巧妙地濃縮為每集5分鐘的微紀錄片。在推動電視節目多維度傳播的同時,其故事性和歷史性也站在年輕人審美的前沿。
(四)強調記憶喚醒,提高認同感
集體是民族記憶喚醒的來源,個體只有在集體當中才能具有民族記憶和國家認同感,在微紀錄片創作過程中通過從“小我”升級到“大我”的典型故事,才能喚醒受眾的民族記憶,才能從個體認同感上升到國家認同感。講好中國故事,在故事中實現情感的升華,就必須將宏大的敘事題材進行高度的概括。在《新中國密碼》中,既有開國大典的國家記憶,又有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民族英雄。影片采用極具代表性的家國故事、英雄故事,構建家國情懷,褒獎奉獻精神。在《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正是因為構建起了受眾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橋梁,才讓受眾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獨特影響力和號召力,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五)互動模式創新,增強受眾黏性
微紀錄片要提高受眾情感體驗,調動受眾情緒,就必須激發受眾的互動興趣,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比如彈幕就建構了一種交流生態圈,提高了受眾對于節目的關注度。再如微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在創作前期便設置了官方微博,發起了抽獎或者贈送衍生產品等福利活動,吸引粉絲關注,產生互動敘事,提升作品的影響力。在微紀錄片中闡述時代情景,傳播相關的科學、知識等,也有利于增強受眾的觀賞體驗感。例如微紀錄片《“洋”貴妃》通過非遺的情景化敘事,以直觀性的視覺體驗建構起了傳統文化與受眾的情感橋梁;運用了別樣的參與方式,以路人的視角將受眾帶入京劇傳達的情感中。在情感交流中,消除了京劇與受眾的隔膜感,建構了真正的文化傳承精神。創新互動模式無疑為微紀錄片的發展提供了啟示與借鑒,促進觀賞者與創作者的深度聯結,增強受眾黏性。
(六)立體化與差異化傳播
微紀錄片是在個性化、碎片化、傳播速度快的新媒體環境下成長的,新媒體造就了大量差異化和不同需求口味的受眾。針對不同受眾,要推出差異化、立體化的品牌營銷策略。例如《了不起的匠人》團隊通過不同渠道包括微博大V、短視頻、電視廣告等領域,向不同年齡段和有著不同觀賞習慣的受眾群體推介欄目。通過口述傳播、二次傳播等擴大欄目的影響力,提高受眾關注度和認可度。
新型的品牌營銷策略要以新型的傳播模式和業態為基礎,發揮出品牌價值的功效。受眾對于作品的評價與推薦是構成品牌價值的基本要素,擅長捕捉受眾的意見進行更改,也是構建立體化品牌價值最重要的環節。微紀錄片《四季中國》,通過與受眾探討二十四節氣在中國文化中的影響,提升欄目形象,構建品牌價值。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微紀錄片必須要適時調整品牌營銷策略和方法,推動品牌價值的建構與完善。
結語
微紀錄片作為全媒體時代的產物,采用微視角的敘事手法,來進行故事化和藝術化的表達。傳統媒體的傳播是單向線性傳播,而微紀錄片的傳播是靈活多樣、可裂變的。廣闊的市場和升級迭代的技術為微紀錄片打開了想象的空間,也改變著人們的審美習慣。但較之于傳統紀錄片,其在敘事上還需要進行細致描寫和刻畫,不斷創新,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徐萬里.短視頻時代下微紀錄片的創作發展[J].記者搖籃,2021(08):103-104.
[2]石莉.微紀錄片的融合式格局建構:產業、內容與前景[J].傳媒,2021(13):56-58.
[3]鄭興.主流媒體微紀錄片講好中國故事策略探究[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21(07):94-95+111.
[4]李昂.探索新媒體時代紀錄片的融合范式與轉型路徑[J].新聞研究導刊,2021(11):177-179.
[5]徐永林.論新媒體微紀錄片中古村落形象的符號建構[D].安徽大學,2019.
[6]翟婧倩.新媒體微紀錄片《了不起的匠人》的生產流程與內容特征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2018.
[7]郭嘉良.微紀錄片“年輕化”傳播途徑的創新與探索——以《如果國寶會說話》為例[J].青年記者,2019(29):73-75.
[8]王瑋琦,夏中華.新媒介情境下微紀錄片的“新主流”傳播策略——以B站微紀錄片為例[J].新聞前哨,2020(10):103-104.
[9]馮向宇.淺析新媒體時代下我國傳統工藝類短視頻節目的發展——以廣西電視臺微紀錄片《技憶》為例[J].視聽,2018(05):34-35.
[10]秦璇.短視頻中微紀錄片的特征分析——以“二更視頻”為例[J].東南傳播,2018(04):115-117.
(作者:聊城大學傳媒技術學院2020級研究生)
責編:項賢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