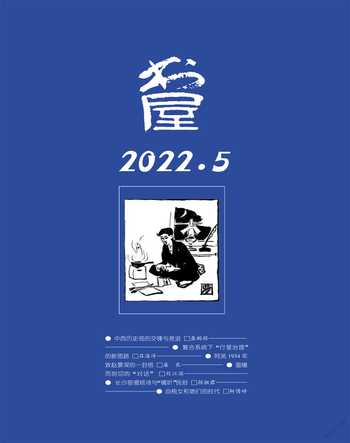為什么廢名是“說不盡”的?
鄒建軍
武漢大學陳建軍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關于現代作家廢名的專著《說不盡的廢名》(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首先是這個書名引發了我的興趣和思考:為什么作者說廢名是“說不盡”的呢?他在這部著作里說了一些什么呢?是不是還有哪些內容還沒有說到呢?陳建軍長期致力于廢名研究,已經出版了好幾部專著,包括《廢名年譜》《我認得人類的寂寞:廢名詩集》《廢名講詩》和《橋》(手稿整理本),并編有四卷本《廢名作品精選》等。他以一己之力,就已經出了這么多關于廢名的研究著作,同時還發表了數十篇關于廢名的學術論文。
廢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比較特殊的作家,出生于湖北黃梅,成長于南方的江漢大地,而發展于北方都城,氣質獨特,個性鮮明,悟性頗高,造化極大。其生前發表和出版的作品及著作不算很多,但在文學界和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陳建軍為什么因為一個廢名而寫了這么多論文,并且還有多種專著?作者說廢名“說不盡”的重要原因也許就在于此:因為他的作品豐富深厚,著作具有相當的開創性與拓展性,同時也是因為陳建軍作為浠水人的故土情結。黃梅與浠水都屬于鄂東地區,是地理和文化上的“鄰居”。廢名作品中存在著許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東西,而陳建軍對于廢名及其作品又有著許多重要的發現。
廢名是一個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現代詩人。陳建軍雖在《廢名傳略》《〈我認得人類的寂寞:廢名詩集〉前言后語》《序〈廢名先生〉》中對廢名的詩歌作品有所涉及,但他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廢名學問和人格的探討方面。他曾編過一本廢名詩集,并為廢名的詩作做了不少“注解”,也算是一種間接的評論與特有的研究。在這樣的研究中,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東西,發現了許多閃光的東西,發現了許多隱秘的東西。
廢名還是一位詩歌理論家和批評家。陳建軍對此方面比較關注,在《廢名對胡適新詩理論的反撥與超越》《廢名講〈詩經〉》《廢名關于杜甫“三吏”編次等問題的考辨》等論文中進行了討論。廢名的新詩理論是相當豐富的,其《談新詩》當時就在詩壇和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陳建軍在其著作中圍繞廢名與胡適的新詩理論之分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同時從學術的角度研究廢名與《詩經》、與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之間的關系,為廢名研究作出了重要的開拓性貢獻。
廢名還創作了不少小說作品,包括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在歷史上也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陳建軍在這部著作中著重討論了長篇小說《橋》的版本變遷問題,他以文學史家的眼光,給我們呈現了他所見到的這部小說的諸多版本,以及每一種版本所存在的問題。版本學是一個很大的學問,研究版本費時費力,一般人不愿意做,但對于文本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只看其中的一種版本,而不管前后的變化及其原因,那對于作品和作家的研究有可能會產生許多盲區,形成諸多盲點。這樣的研究有可能是“盲人摸象”,或者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當然,文學研究主要還是對于文本的研究,但選擇什么樣的文本至關重要。如果文本本身是有問題的,或者完全不顧及文本的不同面相,最終既不可能準確地把握文本,也不可能全面、科學地理解作家。
廢名一生所從事的、沒有中斷的學術研究,也是陳建軍著作中關注的重點之一。陳建軍有感于廢名學術研究價值的重大,曾專門撰寫一文,提出“別忘了,廢名還是一個學者”的觀點。那么,廢名到底是一位什么樣的學者呢?作者在本書中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回答。在另外幾篇論文中,作者對廢名的學問與思想進行了具體的討論。一篇是《廢名對進化論的反思與質疑》,集中討論了廢名關于“進化論”的看法;一篇是《廢名講〈詩經〉》,全面總結了廢名關于《詩經》的相關論述;一篇是《廢名的兩部魯迅研究專著》,具體討論了廢名關于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同時還討論了廢名對于《阿Q正傳》的研究。
陳建軍關于廢名文集及研究廢名著作的書評,同樣堪稱學術力作。兩篇是關于《廢名年譜》的,一篇是關于《廢名集》的,一篇是關于《抗戰時期廢名論》的。再就是關于廢名研究著作的兩篇序言,其性質類似于書評。我們不要小看這樣的書評,因為要寫好一篇書評,就必須通讀全書,并且要有客觀公正的評價,還要提出問題來討論。書評肯定不是一種簡單的介紹,主要還是一種學術性的評價,所以這樣的書評有利于讀者的閱讀,同時也可引起學界人士一些深入的討論。書評是學問的一種方式,是學問的開始,因為做學問總是從“讀書”開始,以“著書”結束。陳建軍的這些書評,都沒有客套話,是在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而且相當真誠、寬和,體現的正是一種做學問的態度。
這部書中還有幾篇論文是比較特別的,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些與廢名相關的軼事與掌故,作者卻把它們當成了學術問題來探討,如《說說廢名的印章》《廢名的幾副對聯》《廢名的一則題箋》《談廢名的一封殘簡》和《廢名與魯迅》等。從這些論文的標題來看,似乎不是什么學術問題,其實正是學術的角度與學問的內容。作者不僅把這樣一些并不為學界看重的東西當成一種文本,而且說清楚了它們的來歷及功能,當然也就成了一種學術發現。陳建軍對于廢名的生平事跡和作品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一些很細小的事物上都有所發現,所以他才能夠寫成論文,并且是很正式的學術論述。這樣的努力,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還有一些關于“問題”的爭論,也具有很強的史料性。《“馬良材”是誰》對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人物進行了細致的考證。《葉公超批廢名》一文以翔實、可靠的史料,解決了學術史上的一宗懸案。在《廢名致周作人信二十四封》中,作者把廢名寫給周作人的信件一一羅列出來,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詳細的討論,同時附有部分原信的影印件。文章雖然比較長,但由于證據充足,一切都被還原在那里,所以我們讀起來仍覺得趣味盎然。
此外,還有幾篇關于廢名其人的文章。在我看來,學術著作也好,文學批評也好,文學作品也好,都是作家和學者創造性勞動的產物;沒有作家本人的付出,沒有學者的案上功夫,就不會有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的產生。因此,陳建軍一開始就特別注重對作家本身的研究,如《廢名傳略》《廢名的童年記憶》和《廢名的“真”》等。不過,對于作為人的作家的研究,也需要建立在史料發掘的基礎之上。在這部書中,無論是對于人還是物,作者從來不說一句空話,每一個觀點都要以證據來落實,因此形成了一種扎扎實實的研究路向。對于作家本人的研究,包括對于他的印章、對聯、書信等研究,都有助于我們研究其思想與藝術、學術與學問,當然首要的是有助于我們對作家氣質與學者人格的研究。在文學研究中,到底是對于作品的研究重要,還是對于作家的研究重要,是有爭議的。我認為兩者都很重要,而且是二位一體的存在。對于作家的研究絕對不能離開作品,對于作品的研究也絕對不能離開作家。不過,在具體的研究中,要么研究作家,要么研究作品,不可能在一篇論文中同時研究作家和作品。陳建軍對于廢名的研究,開創了一條特別清晰的路徑,那就是作為詩人的廢名、作為批評家的廢名、作為作家的廢名和作為學者的廢名是不一樣的,所以在他的筆下存在多種多樣的“說不盡”的廢名。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陳建軍是以一種學術的眼光和學者的態度對廢名本人及其作品展開研究的。我們發現,有幾篇論文在收入本書的時候,作者另外寫有“補記”,其內容主要是文章在發表之后,有的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作者在閱讀之后,也發現自己以前的觀點或者比較絕對,或者不夠周密,所以他就在“補記”中很謙遜地進行了說明,并對識者表示感謝。這樣的學術姿態和學術胸懷在今天是相當了不起的,相信在后學那里可以產生一種榜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