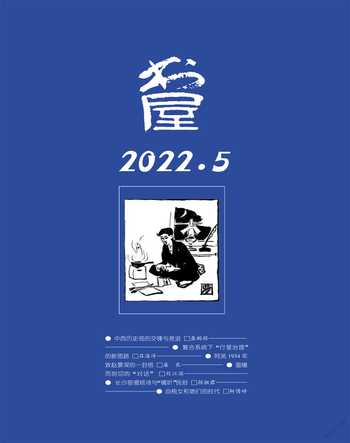閱讀的年輪
周朝暉
午后在陽臺曝書,邊整理歸類,目光邊落在一本包封的舊書上,順手拿起摩挲翻閱,心里涌起如見故人般的親切與感動。牛皮紙包的書皮上“書林秋草”四個中楷墨書,點畫稚嫩拘謹,是我學生時代的筆跡;書皮的邊角已磨破,書頁間多有茶水、油汗暈染過的斑點和蠹蟲蛀過的痕跡。這本舊書引發我的感觸,不僅因為它是我最早購讀的藏書,而且書本身自帶故事與傳奇,承載著我與《書林秋草》這本書的作者孫犁之間一段難忘的因緣。如果說,個人閱讀史也有年輪的話,那么與此書有關的記憶是其中最深的輪線,密圈勾勒,閱讀的年輪也與生命的年輪重疊,回頭重讀,算得上一個心靈史片段。
此書購于1984年夏天。當時我還是初中生,稚氣未脫,卻已是一個老“書蟲”,喜好閱讀并熱衷于買書藏書,且有了自己專屬的書架。這一嗜好,或許得益于家庭環境的潛移默化,也與當時整個時代氛圍的影響有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可以說是一個全民崇尚知識學問的年代,也是中國紙質閱讀史上的黃金時代,身在“南方之強”的廈大學府,更能感受到書香氛圍。先父在大學學報從事文字工作,兼在哲學系執教,交游往來的對象也以教研讀寫為本業的師生居多,讀書、談書、編書、寫書、出書,既是職業生計,也是嗜好,書成了生活的一大中心。從小置身于這樣的環境里,耳濡目染,很容易培養出對書的親近感情。那時我已上了中學,對書的興趣取代了以往的養花、集郵和船模制作,也不滿足于先父指定或購買的書籍,積攢下的零錢幾乎都用來買自己喜歡的書,用過期的掛歷或用過的牛皮紙書稿袋精心包裝,再一本一本充實書柜,怡然自得。大概也是從那時起,我對教輔書籍占主流的高校校園小書店失去了興趣,轉而向市區的大書店探秘尋寶。
那年剛放暑假,參加完閉學式時間尚早,我就去中山路新華書店選購課外讀物。在我的記憶中,這個書店曾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廈門一大圖書流通中心,也是幾代人心目中的文化圣堂。每當節假日,中山路的新華書店里總是人流如潮,遇到某種影響力巨大的新書刊上市,從書店玻璃柜臺前排起的長龍一直延伸到局口街的老字號中梅理發店大榕樹下。這天書店里顯得異常清靜,售貨員們難得清閑,隔著玻璃展示柜閑聊,我得以在四處從容巡回瀏覽。在文史書籍專柜前,我的目光一下子被一本《書林秋草》吸引了,只因書的“顏值”實在誘人:素凈的封面畫了兩片荷葉,孫犁題寫的書名墨色秀潤,與草綠色原稿紙相映成趣,給人一種坐擁書房的充實富足之感,一元三角五分的書價對我來說實屬不菲,但我不假思索就買下了。
那時,我已從語文教材里的《荷花淀》和父親收藏的《孫犁小說選》初步涉獵了孫犁的作品,實話說,談不上有特別的共鳴和喜歡,也許是因為年齡、閱歷的差異限制了我對小說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吧。但這本《書林秋草》卻給了我另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我讀到了另一個孫犁。書中所寫幾乎全是與“書”有關的文字,但立意與情懷完全有別于通常的“書話”與“書評”:有閱讀經驗的分享,如《野味讀書》《與友人論學習古文》;有寫作的“秘辛”,如《文學與生活的路》《談散文寫作》等;其中最具個人色彩的還有圍繞著買書、讀書、藏書的故事與傳奇,如《書的夢》《報紙的故事》等,將個人閱讀這一日常瑣事與時代風云、民族大義和人生百味交織在一起,融匯在凝練的文字中娓娓道來,真知灼見流露其間,令人想起風雨之夕與智者在火爐前的促膝談心。這本書讓我懂得了讀書的門道,開拓了閱讀的眼界,最富啟迪意義的還有它獨特的寫作范式:在閱讀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和生命體驗,并用一種收放有度的方式來講述。順便提及,半年后我的第一篇習作《契訶夫“札記本”的啟示》,就直接來自閱讀此書的感悟。
《書林秋草》也讓我接近了孫犁的情感世界。孫犁早年喜愛文學閱讀,受到魯迅文學精神的熏陶,同情支持革命,青春時代即投身全民族反抗日寇侵略的革命行伍之中,是出身延安“魯藝”的資深作家,早在抗戰時期的就以獨特的文學風格而享有盛譽。隨著革命的成功,他隨大部隊進入大城市,成了一名黨報副刊的文藝工作領導者。以他的資歷和學識,一步步進入上層并非難事,但他淡泊名利,始終保持一個讀書人本色,“一生嗜書如命”,視官位、財物和虛名如浮云,終生與功名利祿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距離。他讀書有道,每讀一本則作一記一錄,《書林秋草》里就記錄了很多有關“讀書”的故事,個中有孫犁本人的閱讀史的年輪,也構成了他精神史的一個重要截面。從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看,正是從這類“讀書記”中,我看到了被籠罩在“荷花淀派鼻祖”光環之外的另一個作家孫犁,情感上也由景行行止的敬仰轉向息息相通的“理解之同情”,再轉而親近起來。當我從閱讀《我的子部書》一文中得知,孫老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大半生節衣縮食,甚至在戰爭年代冒著槍林彈雨保護下來的書籍也被洗劫一空。撥亂反正后,雖然退還了被抄走的書籍,但已殘缺不全,特別是早年按照魯迅購書目錄搜集的子部書,如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子部叢書》刻本,都已七零八落,這使他格外傷心、痛惜,好像散失的不是書籍,而是親人,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段文字令人動容,透過字里行間,我仿佛看到老作家的落寞無奈,聽到他沉重的嘆息,只恨自己不能為老人做點什么。冥冥中如有神助似的,機會很快就降臨了。
也是暑假的一天,我在某舊書門市部淘書,意外發現了幾本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國學叢書》的散冊,加上“編著者王云五”的字樣,讓我確信它就是孫犁喪失的版本,隨之心生一念:買下寄給孫老吧,也許可以補他的殘缺,于是挑選其中品相稍好的《王守仁》《論衡》打算給他寄去。想到給一個大作家寄書,我不禁怦然心動,不敢聲張,一人關在房間悄悄寫信說明緣由。我想,既然只是寄書就不必留名,但沒有名字地址的郵件如何寄出呢?剛好當晚,有位名叫徐夢秋的哲學系年輕講師來訪,我略加思索想了一個名字作為寄件人投遞,不久后開學,也就把這事淡忘了。
一次課間休息,傳達室的校工林阿姨走進教室,手里舉著一個牛皮紙包喊道:“七班周夢秋,誰叫周夢秋?誰叫周夢秋?有天津的包裹!”一連幾遍無人回應,林阿姨轉身離去。這時我才猛然醒悟過來,急忙上前迫不及待和林阿姨確認。我第一眼就看到似曾相識的“周夢秋”幾個大字寫在《天津日報》編輯部專用紙袋上,驚喜之余猶難以置信;再看寄信人處寫著“天津市多倫道二十二號孫犁寄”,懸念才落地:孫犁給我回信了!我在蜂擁而來的同學和“嘖嘖”的驚嘆聲中哆哆嗦嗦地打開紙包,一本精裝版《孫犁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赫然眼前,眼光落在扉頁上“周夢秋同志指正,孫犁,1984年8月24日”那一刻,感覺自己仿佛立于世界之巔。對于一個少年幼稚而冒昧的舉動,孫犁竟會給予這么真誠而慷慨的回應,讓我在幸福榮耀之外又夾雜著感動和感激。唯一讓我不自在的是那個讓孫老信以為真的假名字,好像做錯事卻得到賞賜似的,連同私自冒用徐老師大名一事也讓我于心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總之頗為糾結,就先給孫老寫信致謝,特別為偽造名字的失禮道歉。
不久后我就收到孫老的回應,是一本精裝版《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簽贈寫著:“朝暉同志指正。”顯然老作家寬宥了我的冒失,并贈書給予勉勵,我也為名正言順成了孫犁的贈書對象而高興。我將這一奇遇向父母和盤托出,兩本珍貴的贈書也交父親保管。那時候,我在學業各方面的表現乏善可陳,與父母的殷切期待相距甚遠,與孫犁的這段書緣竟然一度成了他們向親友津津樂道的“殊榮”,好像犬子會因此而變豹似的。這些往事背后,也連帶著對父母周邊親故的溫情記憶。那位曾被我冒用名字的廈大哲學系年輕講師徐夢秋老師,早已躋身國內碩學名流之列,如今偶爾相見,還會拿我當年“名字侵權”的行徑打趣。
這是初中時代的往事,但由這本《書林秋草》引出與孫犁的故事還有后續。
此后經年,我奔命于中考、高考的升學應試,無暇他顧,后來又隨波逐流遠渡日本游學,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少年時代的陳年往事在忙碌奔波的異國漂流中漸漸淡忘。想象不到的是,即便遠在萬水千山之外,即便相隔十年的歲月,我在日本又與孫犁再續書緣。
說來奇巧,在日期間我認識了一個來自天津中醫學院(現天津中醫藥大學)的留學生,得知她曾是孫犁的鄰居,也住在多倫道的大雜院里,后來孫老搬離了多倫道舊居,但距離也不太遠。話題開啟,沉睡的少年記憶一下子蘇醒過來。從她的描述中,我在腦海里拼湊出一幅孫老的影像:高大的身材,孤獨的背影……盡管女同學提供的信息瑣碎,卻一下子拉近了我與孫老的時空距離,也在不知不覺讓我對那個與孫犁有比鄰之緣的女同學產生某種微妙的親近之情。相識后的第一個春假,女同學回國探親,我委托她帶一盒銀座文明堂茶點去看望孫老。
落櫻時節,回到日本的女同學給我帶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驚喜——一本孫犁簽贈的《孫犁新詩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同樣難得的還有她拍攝的孫老照片:老作家坐在帶扶手的藤椅上,很配合地對著鏡頭,消瘦的長臉,儒雅、溫厚,帶著洞察世事的睿智。根據女同學的追憶,見面情形大致如下。
老人在書房熱情接待了遠道歸來的小街坊,靜靜聽了說明,不知是否記得當年與他結下書緣的廈門少年,微笑著點點頭,起身到書柜取出兩本書,分別簽贈給我們,女同學還與孫老合影留念。“書房一塵不染,老人個子很高大,中式對襖,衣帽干凈利索,慈祥得像我姥爺。話不多,專注聽你說話,微笑著點頭。辭別時,一直站在門口目送我下樓梯……”
十多年后,我在日本與天津女同學重逢,她還清晰記著與老作家近距離接觸的每一個細節。不過那時,孫老已辭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