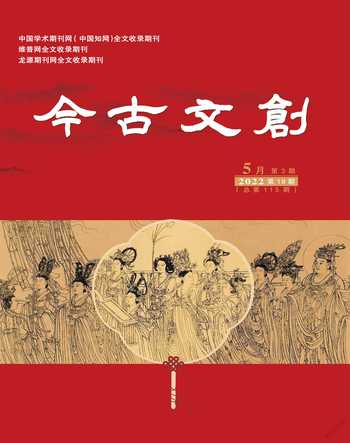謝惠連文學評價及地位變化原因淺探
【摘要】 謝惠連是南朝著名文人,留下了《秋懷》《搗衣》等佳作,鐘嶸詩品稱其為“風人第一”。謝惠連在當朝受到追捧,在后世地位卻逐漸衰微,評論家的評點也再無超出《詩品》者。隨著他的早逝和作品的散佚,謝惠連逐漸被至于謝靈運的光環下,后謝朓的聲譽也壓過了他。謝惠連作為謝靈運與謝朓文學創作的連接者,其紐帶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時代背景的發展變化也是造成他地位下降的原因。
【關鍵詞】 謝惠連;鐘嶸《詩品》;評價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9-003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12
謝惠連,是南朝謝氏家族作家群體的重要成員之一,為謝靈運族弟,與其并稱“大小謝”,二人又與謝朓合稱為“三謝”。能與謝靈運、謝朓二人并舉,足證謝惠連所具備的文學才華。然而時至今日,謝惠連在文學史上的傳唱度和地位卻遠不及余下二者。本文就將針對這一現象淺要地發表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謝惠連作品的當朝評價
與那些在自己所處年代無人賞識,到后世才逐漸被發掘的文人不同,謝惠連的才氣在他所處的南朝就得到了肯定和追捧,引起擬作之風,擬作人員甚至包括梁簡文帝蕭綱和江淹這一類極具地位的人,充分體現了上流社會和主流文壇的高度肯定。
依據《宋書》的記述,謝惠連的文賦在南朝梁時就已獲得“甚美”“高麗”等高度贊譽性的評價,且這種贊美著眼于評判文章的語言風格,即所謂的“形式美”。謝惠連侄謝莊《月賦》借鑒謝惠連的《雪賦》,學習的也主要是形式和謀篇布局。南朝梁蕭統《文選》收錄了《雪賦》《祭古冢文》及五首詩歌(《泛湖歸出樓中望月》 《秋懷》 《西陵遇風獻康樂》《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搗衣》),體現了對謝惠連的肯定。
鐘嶸的《詩品》側重于評價,評謝惠連為“才思富捷”“風人第一”,評述語涵蓋了對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語言特色的分析,可以算作現存最早的關于對謝惠連詩風格的全面評價,且評價較高。《詩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決定了鐘嶸對謝惠連的評語成為其評價體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里程碑,因此下文將著重分析。
二、鐘嶸《詩品》的評價及原因
在鐘嶸生活的時代,九品中正制十分盛行,論人論事常常劃分等級,而人的等級常常與其家庭世族的地位息息相關。鐘嶸的《詩品》也保留這種劃分等級的評述方法,將人分為上品、中品、下品三種品類,不過不再是以家世為憑據,而是以人的文學造詣論長短。《詩品》依據每一位詩人詩作的體制風貌特色與優劣得失對漢至梁的文人及其流派進行評價,定出上品計十一,中品計三十九,下品計七十二。謝惠連被鐘嶸評定為中品,其評述語如下: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
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霞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父喪期間,謝惠連違背孝禮,依舊與友人相互酬唱,宋文帝對此不滿,不僅喪失了原本作為謝家大族子弟的特權,甚至被剝奪了做官的權利,直至元嘉七年才解除禁令,步入仕途。擔任司徒彭城王劉義康的法曹參軍是謝惠連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官經歷,之后就再未有過政治上的成績,故鐘嶸稱其為“宋法曹參軍”。[1]這一人生經歷也為其文學作品的創作奠定了基調。
“富捷”二字在首句提出,可以被看作為鐘嶸對謝惠連的總體概括。據車柱環校證:“鍾書或言‘富捷’,或言‘富健’,而取義有別。此言才思,自當以作‘富捷’為是。”[2]“富”“捷”二字一個側重內容充實有力度,一個突顯構想的迅速、“下筆如有神”,為文不僅速度快,質量也高。
據《宋書》記載:“(謝惠連)十年,卒,時年二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謝惠連具有如此才思,卻英年早逝,鐘嶸稱贊其為“蘭玉”,是極高的贊許,對其二十七歲就逝去的惋惜也就可以想見了。
《詩品》專注于研究五言詩,因而對謝惠連品評的范疇側重于詩歌領域。《詩品序》中就已經提及:“惠連《搗衣》之作,為‘五言之警策’。”《秋懷》《搗衣》是謝惠連僅存作品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兩篇作,很大程度上地展現了他的文學創作水準范式。謝惠連的作品在南宋時期已大量散佚,現存收錄最為完備的是逯欽立所著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也僅輯其詩33首(包括殘篇1首)。盡管其存詩不多,但所包含的題材卻非常豐富。
《泛南湖至石礬詩》《泛湖歸出樓中望月詩》《三月三日曲水集詩》描繪山水風物,寓情于景;《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 《代古詩》寫盡深閨女子的離愁別緒、百轉柔腸;《隴西行》《從軍行》《卻東西門行》《長安有狹邪行》抒發仕途的失意,嘆報國無門、壯志未酬;《豫章行》《與孔曲阿別詩》蓄滿了對友人的珍重、懷念和依依惜別;《西陵遇風獻康樂詩》則將厚重的兄弟情義都熔鑄其中……
謝惠連與謝靈運交往密切,志趣相投,可稱得上是“忘年交”,位列其“四友”之一,常常以詩相互往來,因而文風受其影響也是再正常不過了。謝靈運詩歌“尚巧似”,遣詞造句都經過反復錘煉、精雕細琢,而謝惠連詩歌的遣詞造句不可避免地受其浸染,語言也表現出綺麗雕琢的特質,遣詞用句都細致精警,描寫情景細致婉轉,意蘊綿長,“文已盡而意有余”。與此同時,二者的詩又自然清麗,通達曉暢,毫無阻塞之感,渾然天成,這正是鐘嶸所倡導的。《詩品序》曾言,詩歌應該追求“自然英旨”,這是提倡言語本位的審美傾向,而謝詩的語言風格所具備的審美藝術特質正與其不謀而合。
當然,謝惠連的詩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獨具自家清冷幽寂的詩風格調,這恐怕與他不得志的一生息息相關,總無法在詩中抹去這一份愁緒與哀怨。細細品味謝詩,其內心的感傷、凄愴、無奈滲透在字里行間,“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謝惠連的詩承接謝靈運與謝朓二人,不似靈運般極重描繪山水風景,而是大大增加了抒情部分的比重,為謝跳開啟情景兼具的藝術格調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啟蒙作用。[3]
謝惠連的詩歌受到樂府民歌的影響,沾染了民間創作的色彩,以舊形式為框架,以民歌式詠嘆勾畫整體意境,與當時盛行的佶屈聱牙的詩風截然不同,語言自然明快,頗具清新之意趣。[4]謝詩所抒發的感情皆為作者真實所感,因而具有強大的情緒感染力和審美價值,風力與辭采并兼,無怪乎被鐘嶸評價為“風人第一”。
鐘嶸《詩品》在評述完謝惠連后,還輔之以一段故事傳說,記述了一段謝惠連為謝靈運創作所帶來的刺激與靈感的傳奇故事,這在整個《詩品》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只有謝靈運與江淹享有同樣的殊榮。以筆者的理解,這大概是鐘嶸表達贊揚的一種獨特方式。《謝氏家錄》一書今已散佚,無法考證,然而結合各部史書所記載的時間線索來看,似與此敘述存在矛盾,恐怕并非實事。無論如何,鐘嶸引用此條,意在言明謝惠連與謝靈運存在文學上的密切交往,甚至謝惠連的才思能予以謝靈運思考與啟發,凸顯其文學造詣之高,對其愛重之心不言而喻。
三、《詩品》后時代學者的選擇與遺忘傾向
遺憾的是,盡管對謝惠連的研究并沒有斷絕,卻沒有超越《詩品》的突破性評述面世。明王夫之《古詩評選》共收錄了謝惠連詩歌15首,其中古樂府歌行六首,五言絕句一首,五言古詩八首,每一首詩歌后都附加了王夫之的評述語。“謀篇之工,益使風神掩映”“唯簡斯貴也”“而小謝當之,但覺廣遠”“平極!凈極!”等贊嘆之詞在評價謝惠連詩歌時不絕如縷,表現了王夫之對謝惠連極端的贊賞之情,“固不在洞庭張樂下也”,甚至覺得謝朓、王融等人“喧薄”,無法與之相較。然而觀察王夫之收錄的詩歌,卻無《秋懷》《搗衣》二名作,對謝惠連作品的贊譽有可參考之處,但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了。張溥的評價比較全面,也相對中肯,代表了一種主流的論斷。
謝法曹集,文字頗少,惟《祭古冢文》簡而有意。曹子建伏軾而問髑髏,辭不逮也。《雪賦》雖名高麗,與希逸《月賦》,僅雁序耳。詩則《秋懷》 《搗衣》二篇居最,《詩品》云:“康樂銳思,無以復加。”
除了贊許性的評價,對謝惠連的詩文不大認可的評論家也不少。清沈德潛在《古詩源·卷十一》中就認為“謝宣遠詩,一味鏤刻,失自然之致”。顯然,沈德潛認為謝惠連的詩模仿痕跡很重,沒有自己的特色,且因過度模仿而使得詩歌變得僵硬,無通暢之感。沈德潛的評價,忽略了謝惠連對山水詩的創新和近體詩的開拓之功,筆者認為有失偏頗。
四、謝惠連地位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連接者”的身份劣勢
在鐘嶸《詩品》中,謝惠連與謝朓二人均居于“中品”,可謂并重。傳統稱呼中,也為世人并稱“三謝”,也是將三人齊稱之意。但很顯然的是,如今,時人對于謝惠連及其作品的了解早已遠遠不如謝靈運與謝朓。謝靈運作為第一個大規模寫作山水詩的詩人,成就卓著,有定鼎之功,使得描寫山水景色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傳統題材,成為南朝詩風轉變的開啟者。而謝朓,則是南宋詩風第二次變化的代表人物。南宋詩歌在這一階段逐漸趨向追求新巧細密的語言,并注重對偶,到永明年間,終于出現了清新流暢、講求聲律為特色的新詩體——“永明體”。謝朓的詩清新秀麗、音節和婉、情景交融、詩意連貫,將山水景物題材詩歌的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對梁陳詩風的影響很大,可謂“古今獨步”,對唐代詩人更是影響深遠,促進了近體詩的形成。二者的貢獻,有一個很明顯的相通之處,就是開創了一個時代。無法否認,這確實是謝惠連所缺乏的,他承擔的更多算是一個“連接者”的角色,承接了兩端的謝靈運與謝朓,將山水詩的脈絡傳承并發展下去。這種“連接者”的角色,在文學史地位的競爭上確實一直處于劣勢,因其作用常常為研究者忽視,籠罩于開創者光環的陰影之下。事實上,謝惠連確實遭遇了這樣的命運。清沈德潛在《古詩源·卷十一》中表述得十分直接:“謝宣遠詩,一味鏤刻,失自然之致。”后人對謝惠連整體評價從未超越《詩品》,基本都認為謝詩藝術風格主要模仿謝靈運,雖不俗卻無創新出彩之處,無賞識之士,這樣一來,謝惠連的地位自然日趨衰落。
(二)謝惠連的早逝與作品的散佚
謝惠連的早逝與作品的散佚算是其地位下降的客觀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能夠接觸到的研究對象所處時代的一手史料一定會不斷衰減,對該人物的了解也只能通過史料記載來還原。這樣一來,品評詩人的文學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流傳至今的他所創作的詩歌材料。謝惠連在這一方面也占盡了劣勢。盡管他在十歲左右就開始有所創作,然終其年歲也不過十七八年而已。他的早逝,阻止了他獲得更大成就的可能,使他對詩家的貢獻止步于此。倘若假以時日,以其才智,未必不能進一步大有作為。
上文已經提到,自南宋末始,謝惠連的作品已經散佚大半,到明朝,所輯作品多為孤章殘篇,大多作品只收錄到零零散散數幾首或十幾首,最多的也不過33首。然據《隋書·經籍志》載:“宋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而《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均載五卷。無論如何,謝惠連創作的詩歌原先至少有數百之數,只可惜大多沒有保存下來。誠然鐘嶸評價中提及的《秋懷》《搗衣》二首代表作很幸運地保留下來了,不過在鐘嶸的時代,他所能接觸到的作品勢必比現在更多,客觀上能夠更充分地衡量謝惠連的水準。如王夫之在《古詩評選》中選擇的作品就與《詩品》不同,因此二人的評價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是故按照今天的評判標準,散佚的作品中也許有可能存在未被鐘嶸挖掘卻精妙之詩,然其均隨歷史湮滅,最后的可能也蕩然無存了。
(三)歷史語境的變遷
任何評論文章都免不了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從當時流行的文學審美范式到整個社會的風俗文化特征都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作者的批評取向。魏晉時期,特別是到了東晉末期,玄言詩大興,詩歌中出現大量玄奧的說理,甚至連山水詩的創立者謝靈運也不能免俗,幾乎每首詩都以玄言結尾。而鐘嶸提倡“自然”“直尋”,推崇語言清新流暢的自然之美,反對刻意雕琢,批判創作中堆砌典故和苛責聲律的弊病加以批評上;認為用典貴在“直尋”,要即景會心,用直接的形象來描繪詩人的感情,這樣才能有自然英旨。鐘嶸提倡詩歌創作的自然性、純粹性、無目的性,不必刻意地追求意象和典故,也不拘泥于“四聲八病”的格調韻律中,更不需要“為賦新詞強說愁”,只為“吟詠性情”而進行文學創作。[5]而“抒情性”正是鐘嶸又一力倡的為詩標準。這正是謝靈運所缺乏而謝惠連自覺補足的創舉。自此詩歌描寫景物不再為單純描繪,而更多轉向借景物渲染氣氛,最終目的是抒發詩人主體的情感傾向。在這一維度上,謝惠連的詩歌特色與鐘嶸的批評標準相契合,因此贏得了鐘嶸的贊許。而后世中這類情景交融的作品越來越多,在客觀上抹去了謝惠連詩歌獨到的色彩,這大概也是他被忽略的理由吧。
(四)品評者個人好惡
鐘嶸特別強調詩歌“怨”的功用,并將這種“怨”聚焦于個體的哀樂。謝惠連一生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使他的作品很多時候都帶有一種憂傷的情感。《秋懷》《搗衣》等代表作中都很明顯地帶有哀傷的基調,這正是他生活的底色,暗含了他的愁苦和不滿。這與鐘嶸對“怨”的追求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確立了謝惠連“中品”的地位。這就是品評者個人好惡造成的評價地位差異了。對于謝惠連而言,鐘嶸確實承擔了他的“伯樂”之責,使得他在今天仍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可惜后世再沒有出現此等發掘他的有識之士了。
五、結語
謝惠連的作品自然曉暢,寓情于景,是山水詩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謝惠連的文學成就與其如今所擁有的文學史評價地位是不夠相符的,其在詩歌領域的貢獻和創獲應該配得上更高的贊譽,可謂“明珠蒙塵”。鐘嶸的評價盡管受到個人取向和時代價值的影響偏差,對其文學地位的定位,在筆者看來,倒還算是準確的。后世習慣于將謝惠連作為提及謝靈運時一帶而過的人物,只關注他與謝靈運的交往過程和單方面受到靈運的影響,而忽略了他的貢獻,讓人不禁覺得有些惋惜。
參考文獻:
[1]古沙沙.鍾嶸《詩品》謝惠連條疏證[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4,29(3):28-33.
[2]曹旭.詩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郁慧娟.謝氏山水詩的流暢婉細——“三謝”中的過渡詩人謝惠連[J].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2007,20(1):22-24.
[4]陳欣婷.鐘嶸《詩品》謝惠連評述[J].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15(3):15-18.
[5]鄧依妮.鐘嶸對謝惠連品評所表現的文學思想[J].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8,32(3):87-90.
作者簡介:
黃楠,女,漢族,江蘇海門人,蘇州大學文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