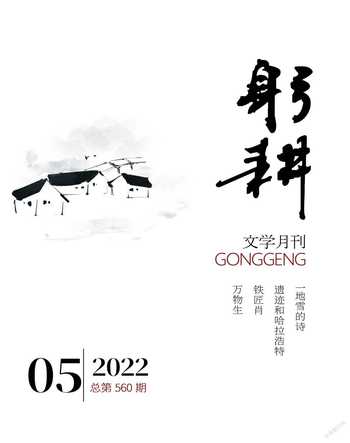北宋人物二題
張爾工
呂夷簡
呂夷簡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宦海沉浮,一生三次為相,前后盤踞北宋政壇20余年,有人把他視作“奸臣”,也有人譽他為“名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還在呂夷簡做宰相時,就曾遭到過諫官王素、孫沔和蔡襄等人的猛烈討伐。稍后,蔡襄更是列出呂夷簡的“五大罪狀”,上書宋仁宗,稱呂夷簡為奸邪小人。蔡襄說的也許有些道理,那陣子呂夷簡已經賦閑,可王拱辰、夏悚、章得象等人還常去呂府去拜訪他,而這些人的品行,都是為當時人所唾棄的。
當然,罵呂夷簡罵得體無完膚的,要數歐陽修了。“賢愚倒置,紀綱大墮”“二十年問,壞亂天下”“罪惡滿盈,劣跡彰著”等等,這些都是歐陽修《論呂夷簡劄子》中的句子。可謂對這個呂宰相是恨入骨髓。
作為北宋鼎盛時期的一個宰相,呂夷簡果有這么不堪嗎?
回過頭來,先了解一下呂夷簡的發家史。前面已簡單提及,呂夷簡仕途上的起步,離不開呂蒙正向宋真宗的極力舉薦。按輩分,呂夷簡喊呂蒙正為伯父,這就不難理解了,呂夷簡的父親,與呂蒙正是一母同胞的弟兄倆。
呂夷簡的父親叫呂蒙亨,也曾參加科考,可惜落選了。他落選的原因,不是成績不優秀,因為禮部將他作為進士甲科上報給宋太宗了,在廷試的時候,被宋太宗給刷了下來。和他一起被刷下來的還有李宗諤,他是當時宰相李日方的兒子。李宗諤落榜,是因為他有個做宰相的父親;呂蒙亨落榜,自然是因為他那個已做副宰相的哥哥了。
宋太宗當時是這樣說的:“斯并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太宗之慮,如果站在寒門學子的角度看,真稱得上是太英明了。呂蒙亨和李宗諤毫無疑問都屬權勢之家,而且權勢熏天,他們要與寒門布衣爭名利,不公的因素的確無可預測。
然而,在宋太宗這一理念的支撐下,呂蒙正仕途的得意,注定了弟弟呂蒙亨仕途的落寞。果然,終其一生,呂夷簡的父親呂蒙亨只做到了一個八品的大理寺丞。在宋真宗面前兩次極力舉薦弟弟的兒子,固然是因了呂夷簡的優秀,但也不能不說沒有一點兒彌補弟弟的成分在里面。或者說,父親的犧牲,某種程度上成全了兒子。
提起這個“奸”字,很容易就想起了呂夷簡與另一個宰相李迪的較量。李迪是個生性淳厚的人,與機變叵測的呂夷簡自然不是一個道上的車,同朝為相,二人少不了幾番交鋒。
李迪沒有心機,卻又素來看不起呂夷簡這個人,這就難免要吃些苦頭了。在稍后的范諷事件中,呂夷簡憑借高超的權術智慧,巧妙地挑撥了仁宗和李迪的關系,令仁宗對李迪產生了厭惡。不久,就將李迪罷了相。李迪悲憤交加,上疏指控呂夷簡為攀附私結荊王趙元儼,并為荊王的門客、和尚惠清補任為守闋鑒義一職,做了大相國寺的僧官。
呂夷簡不承認有這種事,是李迪在誣陷他,請求朝廷替他辨誣。辨誣的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和尚惠清的任命文書竟然是李迪親手簽發的。呂夷簡那幾日去歸德府視察去了,根本就沒在京城。李迪既羞愧又恐懼,知道又被呂夷簡算計了。任命惠清為守闋鑒義的確是呂夷簡的主意,只是公文上赫然是他的簽名,對此,他沒半點的印象了。直到此時,李迪徹底明白,在政治上,他不是呂夷簡的對手,這個人太奸詐了。
如此奸詐的一個人,在宋仁宗這個皇帝眼中,卻是一個大大的忠臣。這與呂夷簡在仁宗面前表現得萬分謹慎有關,換個角度說,這仍是呂夷簡“奸詐”的結果。淮揚一帶有種特產叫糟白魚的,非常的美味,呂夷簡老家壽州,當地官員隔三岔五地會給他送一些來。有一天,呂夷簡的夫人去后宮朝見皇后,皇后嘆道,說:“官家去年幸淮揚,回來后直夸那里的糟白魚好吃,這兩天又開始念叨。然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于京城四圍以外,因此內宮沒有這種魚,相公老家壽州,呂府或當有之。”
呂府當然有。回到相府,呂夫人讓人備了10奩糟白魚,準備獻進宮去。恰逢呂夷簡從外返回,問這是做什么?呂夫人就將原因告訴了他。呂夷簡略一沉思,說道:“送去兩奩就行了。”呂夫人大感奇怪,“這是進獻皇上的,還在惜多那么幾奩嗎?”呂夷簡看女人一眼,嘆道:“皇宮里都沒有的東西,做臣子的家中,隨便就能拿出10奩來,這會讓皇上作何想?”呂夫人瞬間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內心充滿了敬佩。
小事上能謹小慎微,滴水不漏,在大事上,呂夷簡同樣高瞻遠矚,有著超人的謀略。還在劉太后垂簾聽政期間,呂夷簡就選擇了站在宋仁宗一邊。曾有一個叫劉渙的小官,其官職好像是從七品下的將作監主簿,卻膽大包天,上疏懇請劉太后撤簾還政于仁宗。劉太后大怒,要把劉渙貶到嶺南去,當時滿朝沒一人敢站出來為劉渙說話,唯獨呂夷簡上書劉太后替劉渙講情,并扣壓了貶劉渙的公文。不久,劉太后病逝,這事也就不了了之。等仁宗執政后,還問起過這件事:“卿就不怕太后問罪于你嗎?”
呂夷簡笑笑,淡然地說:“臣深知太后不會怪罪于臣。”
宋仁宗狐疑地打量著呂夷簡,呂夷簡解釋道:“這事發生在劉渙身上,臣敢站出來說話,倘若放在別的大臣身上,那么臣就不敢站出來了。”
宋仁宗更加地狐疑:“此又為何?”
呂夷簡回答:“若是大臣,太后會懷疑是陛下指使,臣再站出來,無異于火上澆油,更加導致太后對陛下的懷疑。而劉渙就不一樣了,他的官職太低,太后不會作他想,臣也就趁機為陛下保留住一個忠臣。”宋仁宗十分感動,在他眼中,呂夷簡愈發是個忠臣了。
不管怎么說,呂夷簡能前后為相20年,肯定與宋仁宗的信任分不開。也的確,呂夷簡這樣的宰相值得宋仁宗去信任。關鍵時刻,呂夷簡使大宋避開了一場浩劫,也替宋仁宗免去了一場宮廷之變。北宋有一段公案,叫“貍貓換太子”,說的就是宋仁宗。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宸妃,生下了一個男嬰,卻被告知生的是一只貍貓。其實是被劉皇后掉包了。宋仁宗后由劉皇后撫養成人,他繼位之初仍不知道李宸妃就是他的生母。李宸妃死后,劉皇后想像葬宮女那樣草草打發了她。呂夷簡勸劉皇后這樣會埋下禍端。
劉皇后聽不進去,厲聲喝問他:“你想干預后宮之事嗎?”
呂夷簡也不讓步,說:“臣不想太后給劉家留下禍患。”劉皇后終于明白了呂夷簡的用意,像皇妃那樣厚葬了仁宗生母。
果然,劉皇后病逝,有人就將仁宗“貍貓換太子”的真相揭露出來,并說像下人一般埋葬了李宸妃。仁宗悲憤交加,一邊讓御林軍圍了劉府,一邊讓人打開李宸妃的棺槨,如真像人所說,就抄斬發配劉家后人。打開棺槨后,李宸妃鳳冠霞帔,并不是傳言的那樣,才消了心頭之火。一場浩劫得以化解,這是呂夷簡的一大功績。
盡管種種原因,呂夷簡也數被罷相,但仁宗對呂夷簡的信任和依賴從沒動搖過,常是很快就復歸相位。晚年呂夷簡病重,需要“龍須”做藥引子,仁宗毫不猶豫就剪下自己的胡須,讓人送到呂府,如果宋仁宗不認為呂夷簡是忠誠的,絕不會如此。因此,當呂夷簡病逝,仁宗親往吊唁,哭著說:“朕再也找不到夷簡這樣憂國忘身的宰相了。”
韓琦
韓琦的宰相氣度,在他做左司諫時就顯現出來了。左司諫這個官職,是北宋端拱元年以后才設立的,以前沒有過。左司諫之外,還有一個右司諫,都是主掌規諫諷諭的,正七品官銜。
當時的政壇是這樣的,有一左一右兩個宰相,一個是王隨,另一個是陳堯佐。這兩個宰相都已上了年紀,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王隨的名字可能要陌生一些,而陳堯佐卻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有個哥哥,就是那個在澶淵之戰中和王欽若一起鼓動宋真宗南遷的陳堯叟,陳堯叟中過狀元,不知為何彼時昏聵到這種地步。
陳堯佐還有一個弟弟,叫陳堯咨,名氣在民間可能更大一些,他的名氣來源于一篇文章,《賣油翁》。陳堯咨善射,射銅錢,能穿錢孔而過。不僅善射,他的書法,尤其是他的隸書,幾乎可以與蘇子美的行草書齊名。更重要的是,陳堯咨也中過狀元,宋真宗成平三年的那一榜。這一榜出現很多著名的人物。
陳堯佐兄弟三個,只有他這個老二沒能中狀元。話說回來,兩個狀元都沒做上宰相,他卻做了宰相。可見,這世上的事就是這么蹊蹺。
王隨和陳堯佐,一度都把韓琦恨到骨髓里去了。在此之前,他們二人卻是對一見面就眼紅的老冤家,同朝為相,幾乎沒有尿到一個壺里過。和王隨相比,陳堯佐資格要老一些,他拜相時都75歲高齡了,而王隨整整比陳堯佐小了10歲。但王隨不服他,二人常發生爭吵,陳堯佐有眩暈癥,一吵架就犯眩暈,犯起頭暈來十天半月上不了朝。
還有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二人同齡,都是66歲,年老昏聵,但有一點卻十分的清醒,知道提拔自己的親戚門生。人老子孫多,他們到了這個年紀,都想給子孫謀個好的前程,不惜以私害公。那個韓億,有四個子孫同時參加科考,全部中第,無一落榜,朝野嘩然。韓琦看不下去了,連續上疏彈劾他們,奏章到了中書,即被這幾個人扣壓,拒不上報。韓琦直接面見仁宗,痛心疾首地問:“陛下,祖宗八十年太平基業,坐付這幾個庸腐老臣,是白壞江山啊!”
面對韓琦的發問,宋仁宗仍有些猶豫。看著眼前這四個年紀加起來快300歲、皓首白發顫顫巍巍的老臣,宋仁宗被惻隱之心所攫獲,他不忍心痛下狠手。韓琦一人挑戰這四個背景深厚的朝廷重臣,也絲毫不肯退卻。他懇請宋仁宗,將他的奏疏轉交御史臺,召集文武百官來定曲直,決是非,將仁宗逼得無后路可退,迫于輿論壓力,只得下詔罷免了四人的職務。
韓琦挫敗了四大執政,聲名震動了朝野。仁宗想擢拔韓琦做他的知制誥,以對他敢言的賞賜,令宋仁宗沒想到的是,韓琦拒絕了這次升遷。在稍后韓琦所上的奏疏中,他這樣說道:“臣上疏進諫,是在做一個言官應盡之責,陛下從諫如流,臣愿已足。今因之而得美官,不是臣的本意,況這讓世人怎樣看臣呢?”仁宗覽疏而嘆,非有大德量,誰能做得到這些,內心已有重用韓琦之意。
等到了慶歷年問,仁宗銳志革新,選撥干臣以治理朝政,他首先想到了韓琦,讓他做了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入執政之列。這時兩府核心由三人組成,韓琦、富弼和范仲淹。三人都是北宋有名的賢臣,賢人治天下,文武百官各司其職,循理奉法,百姓安居樂業,一派太平景象。但在一些改革問題上,因政見各不相同,三人也常會在仁宗面前發生爭執,甚至爭得面紅耳赤,然一旦下得殿來,朝堂上相爭的不愉快瞬間煙消云散,或填詞賦詩,或舉杯對飲,談笑晏晏,看如此的一團和氣,哪里還有半點朝堂上相爭的影子?
政見歸政見,友誼歸友誼,這就是君子相處的原則。有議論者拿這屆執政與王隨、陳堯佐那屆相比,一語中的地道出了二者之間的區別。韓琦被任命宰相之后,所面臨的最棘手問題,就是冊立皇太子一事。這一年,仁宗皇帝已經在位四十一年,諸病纏身,隨時都會駕崩殯天,尋求皇權繼承人迫在眉睫。早些年,仁宗親生的三個太子全部夭折,立儲之事就一直懸在那里。群臣百官充滿憂慮,然又都在逃避這個話題,怕不小心觸怒了天子,自己受到責罰。韓琦去面見仁宗,向他進言:皇嗣關系到天下安危,歷史上有很多禍亂,都是因不早立皇嗣而起,現在陛下春秋已高,為宗廟社稷計,宜在宗室中選一個賢德者立為太子。
仁宗面帶怒容,一句話也沒說,就下了逐客令。韓琦并沒就此罷手,過了幾天,他再次向仁宗提及這個話題。這次仁宗沉思良久,最后同意下來,打算把英宗過繼到自己膝下,立為儲君。這可戳了馬蜂窩,那些宮女、宦官,開始圍著仁宗啼哭不已,說皇上龍體安康,這么早立太子做什么?更有那些大小臣僚,為著各自的盤算,在暗地里散布流言,指責韓琦居心叵測,有著不可告人之目的。仁宗又有些動搖。
下次臨朝,看見韓琦,仁宗面色陰郁。韓琦看在眼里,便知道仁宗受人蠱惑,似乎有了悔意。果然,仁宗退朝后單獨對韓琦說:“立太子一事,不如先放一放。”韓琦面色依舊,從容說道,此事已朝野盡知,若突然擱置,必遭天下妄議,不利于朝廷。仁宗恍然有悟,對韓琦說:“若非卿,朕幾成社稷罪人。”立儲君之事隨決。
仁宗駕崩,英宗順利登基。按宋朝慣例,英宗要著龍褂在仁宗的靈柩前守孝,然而,意想不到的的事情發生了,英宗一進靈棚,還沒跪地哭孝,突然發瘋,散發跣足,目光甚是駭人,一連聲大呼大叫,間雜謾罵俚語,沒誰能聽懂他喊的是什么,罵的是什么。宮女、太監紛紛躲避,大臣錯愕癡立,相顧不知所措。韓琦正替英宗拿著靈杖,這時急忙扔在地上,抱起英宗進到帷幕后面,邊走邊大聲問:“是誰激惱了官家?”韓琦的這一問,把英宗發瘋的真正原因遮掩過去了,避免了一場宮廷風波。
韓琦叫內臣去喊御醫,可內臣早已驚散,遠遠地站著觀看。韓琦將他們呼至跟前,把懷抱里的英宗交予當值者,再三叮囑,“用心照管好官家。”對內眷細心安慰,說陛下悲痛所致,很快就會好起來。然后方走出帷幕,厲聲對眾大臣說,今天這件事,只有我一個人了解根梢,你們都絲毫不知內情,不要到處亂說。然后,撿起地上的靈杖,伏在仁宗的靈柩旁,開始哭泣,好像英宗之事就根本沒發生一般。歐陽修目睹了整件事的經過,后來對人說:“韓公遇大事之冷靜,真無人能及。”
關于宋英宗的突然癲狂,有大量史料作了記載,說無人能辨真假,一部分人懷疑他這是在借癲狂來發泄對曹太后的不滿,因為曹太后所率下的內宮對立他為皇太子曾作過阻撓。這的確有蛛絲馬跡可尋。宋英宗驟然由宮外而宮內,沒有根基,亦少人脈,加上做了皇帝后對內侍甚少推恩,整個后宮里的人對他這個皇帝都很疏遠,人心世情都傾往曹太后那里。這令韓琦極為憂慮,怕英宗在內宮遭遇不測。于是,有一天,韓琦對垂簾后的曹皇后奏稟道:“臣等只能在外面見得皇上,后宮里的安危要全靠太后了。”垂簾后面悄無聲息。群臣百官感到了氣氛的緊張,偷眼去看韓琦,韓琦神情自若,又奏道:“若皇上有什么閃失,太后也難得安穩。太后只有把皇上照管好了,內外方能相安無事。”同列的幾個大臣將頭縮在官袍里,臉上汗流不止。等走出大殿,吳奎擔心地對韓琦說:“話說得是不是太過了點?”韓琦回答:“只得如此說,皇上才可保無虞。”
其實,在其他一些事情上,韓琦并非都如此苛刻。他做宰相經年,對于某件事亮明態度之前,都會反復地論列,正面反面,進進退退,就像油漆匠刷器具,一點兒造次都不敢有,直到他認為已接近事實真相了,方才著手處置。接觸的人越發復雜,處理的事情也越發地多起來,在外人看起來,韓琦遇事從未慌亂過,大有定而不亂,靜而不煩的雍容氣度。這一點群臣都很佩服他。韓琦還有一過人處,作為宰相,每天案牘堆積于前,這些文字中,有些是揭露攻擊別人隱私的,往往惡毒無比,每見到這樣的文字,韓琦即手就封存起來,再不讓傳播他人。韓琦曾有感慨,做宰相最難的,就是有些事情絕難一碗水端平,即使端平了,也絕難盡如人意,因此,對別人的不滿甚至謾罵,須要容忍,把苦水咽到肚子里去,不然這個宰相一天都做不下去。
有一段時間,宰相空缺,歐陽修做參知政事,朝中大小事務都交由他處理。歐陽修涇渭分明,凡事都很直接,只要他認為不合乎圣賢之道或朝廷法理的,都當面嚴加斥責,很多官員都很怨恨他。韓琦當宰相后,處事風格與歐陽修截然相反,從不當面責人之過,而是擺出能讓人折服的道理,令對方心服口服。有的時候,大臣間政見不同,相持不下,雙方便揮以老拳,然后,都怒氣滿腔地來找韓琦。如果是歐陽修,他會給辨出曲直,對理屈的一方進行訓斥。韓琦不這樣做,先讓雙方坐下,拉一些閑話,讓雙方都冷靜下來,再一起來分析引起爭論的原因。一分析,是非全明白了。好勝的一方雖還有些不平,卻也無話可說了。
等宋神宗即位,根據朝廷慣例,韓琦上疏乞請外放,出任大名府知府。在任上,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府衙的內壁上,有一首太宗皇帝作的詩,墨跡宛然。意在收復燕,豪氣干云。韓琦到大名上任時,神宗降旨,要他修繕保護太宗墨跡,不得使之漫漶脫落。韓琦的門客獻策,將此詩拓成墨本,進獻神宗。韓琦說:“圣旨只令修繕,未讓進獻。”可是,韓絳接替韓琦做知府,第一件事就是將此詩拓制成摹本,進獻給宋神宗。韓琦聽說了這件事,長嘆道:“昔日我豈不知進獻以邀寵,只是圣上年輕,正銳意西征,老臣不想推波助瀾,致使邊境民不聊生。”這一年,韓琦已經6l歲,與當年的王隨相比,年紀幾乎相當了。
到了這個年紀,人都變得寬容了。連意志堅如磐石的韓琦也不例外。在大名府期間,還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有人給韓琦送了兩只玉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玉酒杯,從墓冢里挖出來的,好像是西漢的東西,一點兒瑕疵都沒有,可稱得上是玉中極品了。韓琦酬以百金,視若珍寶,平時藏于錦匣,只有宴請貴客的時候才拿出來,用它給客人勸酒。有一天,宴請新來的漕使,又拿出了這兩只玉盞。勸酒時,其中的一只玉盞被一個官吏不小心拂到地上,“叮”,碎成數瓣。滿座的客人瞬間都愣住了。這個官吏慌忙伏在地上,一個勁兒賠罪。韓琦卻神情自若,對在座的客人說:“凡物的得與失,成與毀,都是時數使然。”又扶起地上的官吏,“不必如此,你只是失誤罷了,又不是故意為之,沒有什么罪。”在場的人無不佩服韓琦的大度和寬厚。
說不出為什么,韓琦對王安石頗有偏見。當年他與富弼曾有一段對話,前提是富弼向韓琦舉薦王安石,想讓王安石出任翰林學士,不想被韓琦拒絕。
富弼說:“像安石這樣的經術飽學之士,你為什么不用?”
韓琦回答:“若令安石常伴皇上左右,必多生事端。”
韓琦出任相州知州時,王安石的改革正進展得如火如茶。盡管這時的韓琦年老體衰,但依然關注著朝中的風吹草動。每當聽到王安石今天變革了一項法度,明天更替了朝廷的一款綱紀,他都會憂慮形諸于色,嘆息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