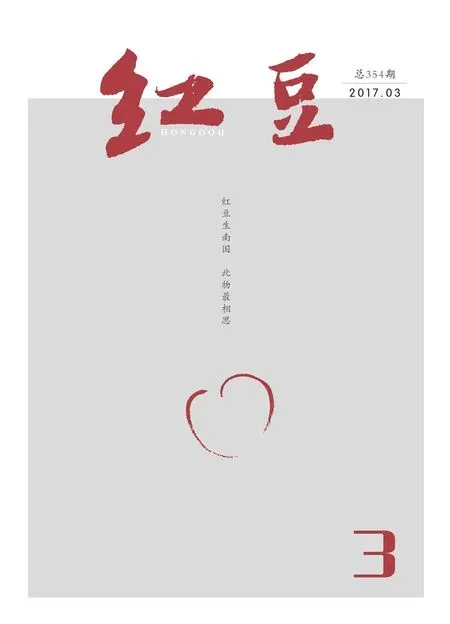異見三題
時瀟含
加萊的下午
加萊是一座很干凈的小城市,小到半天就能轉個一干二凈,但卻讓人想要留在這半個月,或者更久。加萊就是一個讓人一往情深、不會感到厭倦的地方。
我和阿鉉一起躺在厚厚的草垛上,讓溫暖的太陽光照在臉上,目光的盡頭是海天相交之處的英國。學校朋友們的喧嘩聲慢慢遠去,留給我們的只有一片靜謐。青草長得很厚,帶著一點水汽,人像是喝多了一頭倒在床上,蓋上厚厚的被子,切實感受到被包裹的柔軟。
阿鉉揚了揚手機,給我看他收到的一條短信,他手機里的地區被調成了英國,時間也成了英國時間。我說:“要不你干脆游過去算了,反正這么近。”他說:“不了吧,你看英國那邊的天空烏云密布,還是在這里曬曬太陽的好。”看來在里爾生活的人,都領教過寒冷又陰郁的天氣的厲害。我時常會想起《圍城》中的那句話:“你沒法把今天的溫度加在明天的上面,好等明天積成個溫暖的春日。”
里爾其實并不算非常冷,但無奈陰雨綿綿,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放晴過,而且還有不知疲憊的風。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收到朋友秋天的短信,短信說:“今天風太大了,走在我前面的鴿子被吹得一個趔趄。”如果不是要在里爾度過漫長的冬天,我差點就被逗笑了。
里爾的春天我不知道還能不能等得到,所以格外珍惜加萊這座能感受到溫暖陽光的小城市。就好像是聞一多所說的:“相思是不作聲的蚊子,偷偷地咬了一口,陡然疼了一下,以后便是一陣底奇癢。”我在里爾望著陰沉的天花板,躺在床上聽雨打屋檐的時候,不僅想念深圳的秋老虎,也想念在加萊那個躺在草地上的下午。這樣的陽光突然捂住我們喋喋不休的嘴,叫我們沉默。倒也不是無話可說,只是想留住這里的一份寧靜,留住這種踏實的感覺。
加萊最多的是法式花園、圣母院的后花園,用花組成了一只開屏孔雀的小公園都值得駐足,在別的城市我好像從來沒有看到過人們如此熱愛園藝。春天沒有在這里遺失寂寞的花朵,這里也沒有瘦弱的街道和荒郊的月亮,有的是花團錦簇的繁華熱鬧,色彩繽紛卻并不顯得雜亂。這里甚至在市政廳的旁邊建了一個關于一個小男孩的夢想的花園,從入口走進去就可以看到這個男孩子的故事。我們在這個孩子的夢里徘徊。一開始我覺得加萊政府的童心實在是太浪漫了,甚至有點浪漫得過分。不過從花園的盡頭走出來,就看到了一座紀念碑,紀念那些在國外戰場上為法國犧牲的加萊男孩。對著紀念碑讀名字的時候,我突然想到,那個花園就是他們的夢嗎?
他們是那些曾經做夢的男孩子嗎?加萊的古建筑其實整體上都透出一股笨重的感覺,乍一看并沒有高聳入云或是金碧輝煌的絕美,這是因為這些建筑之前都是抵御外敵的堡壘,所以都是用灰灰的磚瓦筑成的厚實建筑。這個時候想一想隔海相望的英國,再想一想那個男孩的夢境,又別有一番滋味了。
在小城市里走走,看看古老的建筑本身就已經很舒服了,本來就是沒有目的的旅行。一句玩笑似的“來都來了”的背后,其實是對遇到的一切都照單全收的樂觀。因為我早上喝了太多冰牛奶,急匆匆尋找洗手間時,才發現遍尋不到的不僅是我早已丟失的夢想,還有免費的洗手間。只能匆匆走去海灘,尋找海灘上的移動洗手間。
在我們離海灘還剩五百米的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為什么剛才街上的法國人都不見了,原來法國人都知道海灘才是加萊的心臟,早早就躺在海灘上曬太陽了。
加萊的海大概是法國北部的海中最干凈的。最先看到的是一片藍色的天空,就是丹麥舍友望向我的藍色瞳孔般的那種天空,連云都是薄紗狀的,薄而均勻地涂在天空中。海的顏色深邃,就如同一雙帶著酒氣的眸子。沙子細白,像幼兒園里小女孩的臉蛋那樣白皙。但是我們最先走到的海灘竟然是封閉的,認真一看,在海浪沖刷的地方有一片黑壓壓來回移動的東西,原來是上百只小海鷗。大海鷗遠遠地伏在沙灘上,坦然地曬著太陽。小海鷗在這片海灘出生,在這里長大,還沒有離開過,所以迫切地想要沖向海里,但是又被拍來的海浪嚇退。它們一直樂此不疲地隨著海浪的起落,向前跑又跌跌撞撞地退回來,不知道它們需要多久才能想起來自己有翅膀。現在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沖到開放的海灘上,躺下來聽聽海浪,看看明晃晃的天空。但是不行,我們要先去洗手間。
法國的洗手間很有意思。大多數洗手間是不分男女的,男男女女都排在一起,而且男生的洗手間都沒有門。這也就意味著每次去洗手間的時候,都要經過幾個正在解決個人問題的男生。而法國人恰好是很講禮貌的,萬一有眼神交流就免不了要打個招呼,打了招呼之后,在等待的那兩分鐘里,還要進行禮貌的聊天。在洗手間里聊天能聊什么呢?我連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有一次我從麥當勞的洗手間隔間走出來,一個風度翩翩的男生拉開門問我:“你好嗎?”還沒有等我思考完我今天到底好不好這個問題,他就已經閃身進了隔間。我長舒了一口氣,難道我要回答“上洗手間之前不太好,但是現在感覺好多了,你也快去吧”?我的法國朋友一邊洗手一邊毫不在意地說:“你說你很好就行了,他問這個問題沒有期待答案,只是禮貌而已,所以你也不用費心去想。”洗手間禮儀,我又學到了。
而加萊的海灘洗手間非常折磨人。本來大大咧咧的法國人突然講究得過分,洗手間的地板可以稱重,里面只能進一個人,大于一個人的重量就會報警,而且會無法關門。為什么會有人想要和別人一起進去呢?而且每使用一次洗手間,門就會在使用之后重新被自動鎖上,連馬桶帶地面清洗三五分鐘。清洗完成之后,下一個人才能進去。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衛生間慢條斯理地被清洗了四遍,和身后的法國大叔聊到無話可說,度過了人生中最煎熬的半個小時。
海鷗在湛藍的海上翱翔,海浪帶走白沙,又把白沙送回岸上,海灘上的歡聲笑語聲聲入耳。我遠遠地看見笑起來有一雙彎彎的眼睛的匈牙利小哥在沙灘上教日本小哥后空翻,還有一群法國學生在沙灘上一邊吃東西,一邊放聲大笑。
我們如愿以償地脫下鞋子,坐在沙灘上,把腳深深地埋進軟軟的沙子里,看著遠處純凈的天空,然后從包里掏出法棍,一邊聊天一邊用余光欣賞匈牙利小哥在空中畫出完美的弧線。
時間好像也不愿意離開了,在這里久久駐足。言簡意賅一點,給我一瓶酒和一個朋友,就能在這里從日出坐到日落,看潮漲潮落,看海鷗饑腸轆轆地飛出來再在夕陽中歸巢。在法國待著的短短的時間里,我們都快速地沾染上了法國的習慣。比如出門永遠帶著自己的小飯盒,寧愿坐凌晨的大巴也不坐會耽誤半天白天時間的火車,能一天回來的旅行就肯定不會過夜,還永遠不急不忙亂逛,畢竟有很多我們以為無法完成的事情最終都能被順利解決,索性好好看看風景。就像塞利納口中的法國人:“看上去老是忙得要命,實際上他們從早到晚都在閑蕩。何以見得?要是天氣不適合閑蕩了,比如過冷或過熱,就看不到他們了,因為他們都躲進室內,喝咖啡和啤酒去了。”
有一個漫長而無聊的下午,我打電話給Luis,問他想不想去公園,他說他有安排了。我絲毫沒有留情面地揭發他,他顯然是在床上,躲在厚厚的被子里接的電話,我甚至能感受到電話那頭的困倦和溫暖。他落落大方地說,這種寒冷的天氣,只有要上班和上學的倒霉蛋才會出門,他的計劃是躺在床上一邊喝啤酒一邊看書。
顯然,啤酒還是要冰的。喪失了直接又真實的思考方式,法國就不能稱為法國了。以至于我現在,在有人邀請我出去玩的時候都會提前說:“請在一個不下雨的晚上,帶我去一個不貴的酒吧,要不然我情愿在家里待著。”在那個躺在加萊的沙灘的下午,我還不知道法國具有如此神不知鬼不覺的感染力。
在布拉格看夕陽
布拉格廣場上,日落的光芒燒紅了遠處的一整片天空,鐘樓和雕塑全都沐浴在斑駁的光影中。夕陽消失得很快,天空的顏色迅速變化著,彩色的光暈在天空中游走。夕陽還沒有完全褪色,我就因為它終究會消逝而感到留戀了。這種美好的東西,禁不住分析,因為根本來不及思索,就快速地帶著你的挽留一起走了。
我看過許多美麗的日落,有一些讓我覺得這就是人生中求而不得的那一刻了;有的讓我希望身邊有一個人,能牽著手,一言不發地望著天空,直到完全被黑暗籠罩,一起看月如何缺又如何圓;還有的讓我想和朋友一起沖著日落的地方奔跑,大口呼吸。但是那天布拉格的日落,是那種讓人陷入沉悶悲傷的美,美到不可方物。當我望著那片天空的時候,一直在我腦海里徘徊的是:我這一輩子再也看不到這樣的日落了。
其實來布拉格之前,我對這里一點想法都沒有,只知道這里是一個久負盛名的地方。Tinka很不屑地說:“捷克是捷克,布拉格是布拉格,布爾諾才是真正的捷克城市。”
布拉格的城市整體差別不大,和布達佩斯的感覺很相像,好像整座城市都值得一逛,風格也是統一的,不像大部分西歐城市,老城區古色古香,出了老城區,建筑和街區就不再那么有味道了。在布拉格,不論是在河的哪一岸,建筑都以橙頂黃墻為主,風格古舊又統一。
第一天到的時候已經是下午,我和阿鉉在城市隨意走了走。在廣場上到了整點會報時,會有使徒從自動打開的窗戶里探出身子,為天文鐘駐足。又走到老城的對岸,在長長的橋上看一群快樂的大爺拉手風琴和褪了色的大提琴,還有各種叫不出名字的當地樂器。再看看天空中飛舞的鴿子、在河岸邊漫游的水獺,還有矗立在橋兩側的基督雕像。
基本上每次路過這里,都會有人賣唱。有一天清晨,橋上的人還不多,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在角落里吹薩克斯。天空藍得不像話,遠處是參差不齊的橙色房頂,伏爾塔瓦河河面波光粼粼,映著天空中的光。風吹過山上的樹,吹過山頂的城堡,吹過河面,吹過我,打著卷吹進尖頂林立的城市里,讓人覺著這樣的音樂和這座城市是渾然一體的。
老城區更繁華,也更有旅游氣息。河對岸的城市更加寧靜,街上不時開過閃著金屬光澤的老爺車。我信步走到法國大使館對面的列儂墻,心想這個選址也是下了苦心的吧。再看看卡夫卡在這里留下的足跡,那棟《變形記》誕生的公寓,他的“一生都關在了這個小圓圈里”的廣場。他就是那只一生被籠子尋找的鳥,是那個被一切障礙粉碎的孤獨背影。雖然他已經變成了布拉格媚俗文化的一部分,成了文化衫上惴惴不安盯著你的大頭像,但是他依舊是那個砸開冰河,問你“當你站在我面前,看著我時,你知道我心里的悲傷嗎?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傷”,還有告訴你“不要絕望,對你的不絕望也不要絕望”的卡夫卡。
他說“愛情就是,我覺得你是刀子,我用它攪動我的心”。他是桃園三結義里的桃花,伯牙、子期里的高山流水。被定格為永恒的蝴蝶標本成為燃燒的灰燼,脫掉自己的面具,還要把別人搓油摘粉、調胭脂捏出來的假面具也摘掉。
不久之后,天黑了,黑夜中的布拉格也別有一番風味。如果說白天的布拉格比布達佩斯更有味道,那么夜晚的布拉格就更有平靜的東歐城市的感覺,而不是像布達佩斯那樣燈火輝煌、氣宇軒昂。長橋上留著星點燈火,剛好能照亮腳下的路。遙望老城區,城里的燈火不算明亮,只有皇宮城堡之類的高大建筑被光照亮。河岸邊的燈光映在水里,拉出長長的光軌,就像慢慢走回家的我,在路燈下牽著長長的影子。好像城市里住著一個講《一千零一夜》的姑娘,而你正在度過第一千零二夜。躺下是這里,醒來還是這里。
回到住處之后,我聽到隔壁房間有聲音,洗澡出來發現隔壁的門上貼了用意大利語寫著“歡迎”的便利貼。
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反正大家終究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大家都為自己的做法感到自得,還要感嘆別人的荒謬。我也不想嘲笑任何處理方式,“不要絕望”,對別人不絕望也不要對自己絕望,大家總有自己解決的方式。人可以選擇是否讓自己生活在恐懼之中,也可以自由選擇,關上門,捂起耳朵,關心一些諸如鄰居家的貓爬進了我的花園,花園里的無花果結了果實,墻角長出了迷迭香之類,對一個人來說是更加重要的事。
之后的幾天,是在老城區河對岸山上的皇宮里度過的。那里有攝人心魄的彩窗,走到深處還有由天使提著床罩的巨大雕塑。原來我們以為是虛構的東西,對于原來的皇家來說都是可以用金錢和權力實現的。
舊皇宮的窗外是布拉格的全景,陽光把窗欞的影子斜斜地打在柜子上,窗子變成了畫框,窗外的城市就是一幅經歷了漫長歲月的畫。卡夫卡說有很多人爬到伏爾塔瓦河的橋上自殺,但我覺得,不如爬上觀景臺,看看這個城市。窗外有這樣的風景,真會讓人想要長長久久地活下去。不遠處還有一條小巷,是以前煉金的工坊,建筑里還保留了當年的煉金工具,還有各種中世紀的兵器和盔甲。總之在這里打發時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有趣的是,臨走的前一天我又來了皇宮一次,正好遇到皇家護衛隊換崗。一隊穿著華服的士兵,踏著整齊的節奏走出皇宮的大門。門外的兩個流浪歌手看見他們走出來,便用手風琴給他們配上了莊嚴的音樂,他們也就這樣其樂融融地踏著鼓點走遠了。
布拉格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尤其是在短短的兩周之后,重新想起這座城市,讓人不禁想起那天夕陽下淺淺的難過。因為過于美,讓人有一種不真實之感。
布拉格的夕陽之美不在于天空遼闊,也不在于波瀾壯闊。只是因為天空中飄過的那一片云形成的層次感,那一片陰影投下的不完美。不是竭盡全力的盛放,而是帶著一點點蕭索的味道,讓人想起長橋上的薩克斯,想起卡夫卡書房窗外的那個小廣場。
鉆進斯洛文尼亞溶洞里
斯洛文尼亞真是一個神奇的國家,雖然面積不大,但是自然資源極其豐富,山川、湖泊、洞穴、森林、海洋,不管到哪里都值得待上一周,到自然里去。
可是我們沒那么多時間。這里的冬天的風景雖美,但天氣卻不那么宜人,山上雪能有齊腰深,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也堆著被清掃收集起來的雪堆。在爬了兩座被冰雪覆蓋的山之后,我們捂著被摔疼的屁股,決定換一個方向,鉆入地下。
斯洛文尼亞最有名的幾個景點,除了布萊德湖之外,就是洞穴城堡和波斯托伊那溶洞了。
我向來對城堡之類的地方沒有興趣,即使那些城堡有著很多后人杜撰的吸血鬼故事和靈異事件,可我總覺得不過是吸引游客的噱頭罷了。
于是我睡眼惺忪爬上了清早的巴士,在風雪中到了波斯托伊那溶洞。波斯托伊那溶洞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石灰巖溶洞,和我們在國內見過的鐘乳石洞穴沒有太大區別,唯一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巨大。在國內我到過不少鐘乳石洞穴,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一個要坐著小船才能進去的溶洞,我早已忘了名字,但是洞里的水極其清澈,無論多深都可見底的水,現在想起還能帶給我極大的恐懼。
想象一下,頭頂上是向下延伸的嶙峋怪石,身處飄忽的小船之上,托舉起你的是幽深的、清冷的水,而且它們還被彩燈打上了各種顏色,更顯得深邃神秘。在波斯托伊那溶洞,即使是坐著火車,也要二十多分鐘才能進入洞穴的深處。火車行駛的過程中,巖壁低低地壓在人們的頭頂上。有時穿過巨大的、能容納上百人的石室,而有時窄小的石洞剛好容許我們縮著脖子穿過。洞穴深入地下一百多米,占地近三百平方千米,我們坐著火車,再加上一段步行也還是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走完已開發的那一部分洞穴。而且這里在雨季的時候還能看到地下洶涌的暗河,冬天比較干旱,只能看到薄薄的一層水。從一百多年前開始,人們就坐著火車進入溶洞,不過那時候洞穴里面沒有安路燈,要使用火炬照明。那多刺激呀。
聽說以前只要愿意花錢,再提前預約,就能在官方指定的向導帶領下,戴著頭燈,徒步走到洞穴通往的任何地方,一走就是幾個小時,實在是讓人心生向往。
其實洞穴內的各種石筍石柱沒太多值得特別描述的地方,這類溶洞里的鐘乳石,雖說總有些體積形狀之類的區別,但終歸是大同小異。它們層層疊疊地向上或者向下生長,加上燈光的效果,就給人帶來一種石頭紛紛在輾轉掙扎著、在鮮艷的石叢中流血死去的美麗效果。溶洞里面的石頭自然都是濕潤的,在燈光的映照之下,就像是蘸著波光。
我實在是太喜歡波斯托伊那溶洞的講解詞了,很少能在景點的語音講解器里聽到這種如詩一般的語言。
它說,洞穴里面的那些石柱生長緩慢,即使只有三四十厘米長,也有埃及金字塔的年紀,看到它們,我們就能感受到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渺小……有的石柱從洞穴的頂部生長下來,我們可以把它們想象成石化的大雨;有些從地上生長起來的石柱因為石灰巖的地表不夠堅硬,在生長到一定重量或高度之后就倒塌了,然而這并不重要,因為它們會在廢墟上重建一個自我,在殘骸上重新生長,緩慢,但堅定。
而且洞穴里有時會突然關掉所有照明幾秒鐘,講解器說大家不要害怕,因為這是讓我們感受一下幾百年前第一批進入洞穴的探險家所看到的場景。在燈光重新打開的那一瞬間,突然從黑暗之中現身的洞穴更能讓人感受到它的巨大,令人震撼。
我喜歡這個溶洞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它除了打上些照明燈光之外,并沒有過多的渲染和生拉硬拽的神仙故事,只是克制又真實地向游客介紹洞內幾千年內發生的一切。洞內有一個特別巨大的石洞,能容納上千個人,向導說之前游客多的時候就有表演,現在沒什么人,表演也就停止了。在這里還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那就是蕭瑟。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來這里的人絡繹不絕,火車每天運行也架不住洞外排起長龍,但是現在人跡寥寥,而且大部分還是他們本國人來游玩。
從洞內出來之后,我們重新回到冰天雪地里等回程的大巴。為了躲避寒冷我們決定到一家路邊的餐廳吃點什么。餐廳里也是人跡寥寥,只有外面的吧臺還稍微熱鬧些,估計大家也是為了驅寒,大白天的就開始一杯杯地喝酒了。
我很喜歡這邊的蘋果派,外皮薄薄的,里面的蘋果先用黃油和糖炒過,酸甜兼具,還透著一股牛奶的香味。我們吃完了東西,大巴還是沒來,窗外白茫茫一片透著寒意,于是我們點了咖啡,百無聊賴繼續坐著。飯店老板見我們閑著沒事干就上來搭話,他問我們來自哪里,又問中國現在的疫情怎么樣了。聽完我的描述之后,他聳了聳肩說,如果一開始他們也用同樣的方式面對疫情,也許現在的情況就會好很多。他說他既是老板,又和他老婆一起當餐廳的服務員,大廚就是他媽媽。
他說,這一家小小的飯店可以說承載著他一家子的收入,然而現在因為疫情的緣故,原本大批大批到這里來的游客都銷聲匿跡了,靠著不多的本地人來這里消費,已經很難維持生計了。他還說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烏泱泱的游客回到這里,他希望他們能來看看他的家鄉,也希望他們的到來,能給這個快要被遺忘的小飯店帶來一點熱鬧的景象。
責任編輯?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 ?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