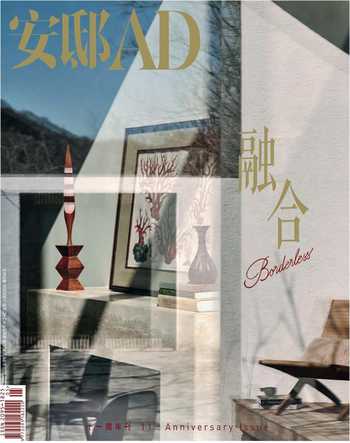都市間的清水島
天妮

在大阪市北區梅田,有一棟清水混凝土建筑。它位于JR線和源光寺附近,周邊是公寓和店鋪。順著圓弧狀墻面,沿緩坡向東,兩扇小圓窗間有一個帶雨棚的推拉門,這便是建筑的入口了。街巷旁的電纜微微垂落,連同樹影映射在狹長的玻璃窗上,目光所及之處嵌著一塊窄小的門牌,上面寫著“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Tadao AndoArchitect & Associates)”。除開窗和幾條表示高度的線腳外,立面上再無其他。建筑樸素、內斂且稍顯克制,近乎封閉的水泥墻在都市的拐角界定出清晰的一隅。

這里原是一對夫婦委托安藤忠雄設計的住宅,最早叫老富島邸。20世紀70年代,他買下此處用于辦公并親自設計,取名為“大淀工作室I”(Atelier in Oyodo)。20年后,既有建筑被拆除,并歷經多次改造,“大淀工作室II”誕生。現今的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有地上5層,地下2層,占地面積為91.7平方米,總建筑面積為451.7平方米。與強調并切分出獨立體塊的現代辦公模式截然不同,幾十年前,相互連通已成為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的關鍵詞。他說:“我的辦公桌在五層中庭的底部。也許是因為在一個傳統的日本小排屋中長大,我更喜歡洞穴式空間的避難所,而不是過于開放的房間。在設計工作室時,我最看重的是團隊空間的統一性。在狹窄的場地上,建筑物必須達到地面以上5層。在中庭,我可以通過大聲呼叫來聯系工作室中的任何人。從樓梯穿過中庭,我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臉。究其原因,也許是我將自己也置于客戶的角色吧。”
安藤忠雄認為,即使技術快速變革,設計仍需由人與人直接的溝通來完成。也正因如此,安藤忠雄最新完成的在中國的第一家餐廳設計“和美術館餐廳”中,微妙地演繹空間的不同對話。安藤忠雄說:“為了擴展現有博物館的想法,與畫廊同心的圓形體量與二樓的長體量相交,所以我在這里設計了與博物館相同的百葉窗,讓人們可以感受到光影的戲劇性時刻。正如博物館展覽是與藝術對話的場所,餐廳是人們交流的場所。我希望參觀者可以在山水自然的存在和光影的風景中進行對話。”
研究所的各個工作層以樓梯相接,并借由書架圍合出內向型的辦公區。自由開放的對話成為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的內核。5層通高的天井將充沛的自然光引入室內,隨時間變化,在混凝土墻面上投射出流動的光影。天井西側纖薄的樓板并非垂直,而是呈階梯狀逐級后退,同時以儲物隔墻打破冗長感,既保證了視線的連續通透,又形成了錯落變化的完整體量。



一眼望去,工作室由直線統合,幾根纖細的圓柱和位于盡頭的螺旋樓梯為全部的曲線。樓梯用簡單的金屬薄板制作而成,上旋串聯起4層和5層。動與靜、硬朗與柔和在這里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天井東側的大樓梯是另一個主要部分,平臺常用于方案展示。與此同時,擋墻也被充分利用,這里掛著喬治·尼爾森的幾何時鐘,還有拳王的簽名手套——要不斷迎接挑戰,要持續突破,“把麻煩變成樂趣”的精神已融入安藤忠雄的血液,成為他的生命底色。弗蘭克·蓋里的瓦楞紙椅斜放在樓梯轉角,搬一把椅子,讓人在方寸間即可小憩,靜坐其中,感受時間的流動。簡約且延續的直角欄桿不加掩飾地暴露在外。東西長墻和樓梯背后的全部墻面都是書,層層疊疊。
安藤忠雄的工作區位于他最喜歡的天井下方,他說:“我最喜歡的空間是我的辦公桌,當我從桌前抬頭看時,便可以看到天窗外的天空,感受來自上方的光影。我在這里凝練了對建筑的所有感知。”這里,一張超大白色方桌上常年疊摞著模型、圖紙和書刊,彩筆也必不可少。他經常抄起紙就畫,或許某個不凡的創意就誕生在信封背面或餐巾紙上。

有人說安藤忠雄個性剛強堅毅,就像他擅用的混凝土。關于和混凝土的相遇,他說:“我注意到這種材料源自路易·康的薩爾克生物研究所。”于他而言,混凝土獨特的質感與長久的力量——由厚重生出的精巧、由清冷生出的溫潤、由純粹生出的豐盈——是其設計初衷的表達,亦是他對自我的挑戰、對抗與超越,更以接近本源的哲學之美傳遞出直擊心底的精神意象和人文內涵。在安藤忠雄看來,清水混凝土可以讓建筑呈現“秀外慧中的統一飾面。它極具多元的表達方式和塑造力讓我能創造出任何想要的東西。這也是我今天仍然堅持使用這種材料的具體原因”。他為自己設計的工作室同樣選擇了不做表面處理和外覆裝飾的鑄造混凝土,結構細部依然直接咬合,由內及外,全無矯飾,清簡得只有空間本身。
他崇尚秩序和邏輯,探尋美與自然,且充滿斗志,從未改變。現今,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仍以傳統藝術家工作室的方式運轉,數十年如一日。他說:“我相信這種堅定不移的品質是我的工作室的特色之一。在經歷兩次大病和多次手術之后,我每天都刻意安排時間離開工作。早上散步,下午閱讀,這是我獲得靈感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