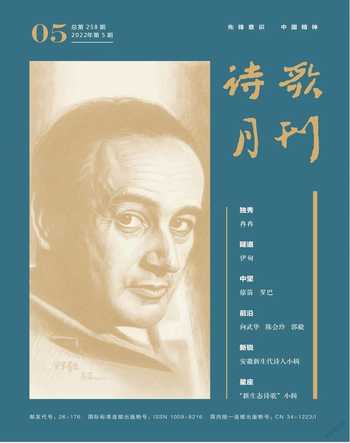隨想錄(隨筆)
冉冉
1.?你覺察到你與自己的文字彼此塑造共同生長時,它們已變得有血有肉,生趣盎然。它們不是你的孩子,而是你的師友和親人。
那種在文字里更新生命的感覺,要向內發掘多久,穿過多長的隧道才能獲得?你總是告誡自己,別抱怨,穩住在厄運中習得的正面習慣。如果你缺乏其他,總算還有忍耐和堅持的美德。
2.?寫作是在沉思中探尋真相的過程。啟示時隱時現,辨識出那些草蛇灰線,不僅需要眼力心力還需要意志,趨近真相的同時也趨近了善和美。
自以為是就是堅信你的直覺和可能見到的事物——盡管它尚未出現甚至永不出現,篤信并創造它,像變現其他的祈請一樣。這份底氣在于,詩人畢竟將匪夷所思的許多事物(愛是明證之一)成功召喚到了身邊。
3.?生命有限,愛和喜悅無限。當我想象到,我跟某顆遙遠的星辰的聯系,一種熱戀般的感覺擊中了我。與其說它是本初的記憶來源,不如說,我是某種不可知的力量的衍生。
對鏡寫作的習慣始于何時?你無法看見鏡中自己凝思的模樣,因為那一刻你的視力專注在文字上,同時也在內心盤桓。美和純凈像磁鐵吸引著它——它們滋生、修改、涵容一切。
4.?寫作中文字的表意至關重要。詩意是什么?是用文字運思時呈現的真知與力量,愛和喜悅。
從害怕觸碰到勇敢面對痛苦,你花費了整整十年。十年間,你重新認識了能指和所指,自己和周遭。
5.?重讀自己的詩,如同攬鏡自照。有時你感到扭捏害臊:不是因為靈魂的裸裎或愛情的泄露,而是因為述說的傻氣和粗陋。急切和幼稚的我們曾說過多少“二氣的話”?但也許,正是那些笨拙和簡單保全了一個詩人的天真。
6.?從某種意義上講,進入并沉浸于寫作狀態的詩人,跟置身催眠的人有幾分相似——譬如其間的專注與放松,自由與喜樂。就是接近催眠中的狀態,同樣也會改變塑造我們的心靈與精神。作為完成狀態的詩歌,是寫作者經驗(或超驗)的析出,是考驗存留和反復回放的幻境,是化妝的白日夢,是我們祈愿的尚未看見的看見,抑或是,我們暫時無法實現的祈愿之愿的替代。
7.?回憶是迷人的。我喜歡追憶的口吻。在追憶里,物迅捷地找到對應,真切而自然,被細節連帶的一切接踵而至,被五官吸附的音聲形色川流不息。你甚至不用特別地尋找,只管撿拾那自動到來的一切。
8.?我要坦白從詩歌中獲得的利益和力量——閱讀寫作重塑了我的生命和生活,在此過程中,我得以反芻、觀想體察身心的景象際遇。通過看和見,我得以遭遇包括自己在內的她和他們——尤其是她,她的自省自律,隱忍擔當,柔韌曠達,幽默篤定,讓我對自性的顯現葆有信心。她根于他們,深藏于達人身內,這是我們自凈的勇氣和愛的希望。
9.?對小場景、小事物的敏感和呈現,依舊需要視野與慧眼,以及對語詞的精嚴選擇和安放。再小的事物都有可以細分的抽屜。
對細節的抓取及層次感的拿捏,需要果敢巧智,也需要不厭其煩的訓練。突發而至的神來之筆,便是對你耐心的報償。
10.?扎根于自己的東南西北。在最不起眼或隔膜疏離的事物那里找回你的親緣。萬物都是你的前身,是幫助成就你的順緣或違緣。在一閃即逝的美善那里尋找真知的蹤跡。
11.?晨光初臨,鳥兒將萬籟凝結為一大段高音和低音。它清澈的氣度與識見,完美的結構和細節,值得我們效仿。
12.?當你身心放松,新奇的感受會撲面而來。在深呼吸里,你看清了它們精密的肌理。越是深刻的感受在表達上就越是含混不清(梅特林克語)。說出那些隱匿在覺知里的陌生和本質——準確明晰地說,胸有成竹地說。
非說不可的時候,強行按捺不是好的選擇,沉默也不是,而是要以少說多。那些有分量有質感的東西在哪個時刻經過你的潛意識,仿佛經過熔煉。
13.?一生里,我們都在做各種練習。練習造句,練習擺渡,練習愛和離別。白天練習生,夜晚練習死。這漫長的經驗之流即是詩歌之源。幸運的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增長了智慧,也收獲了快樂。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了我們的是笨拙和實誠。至誠,遠勝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