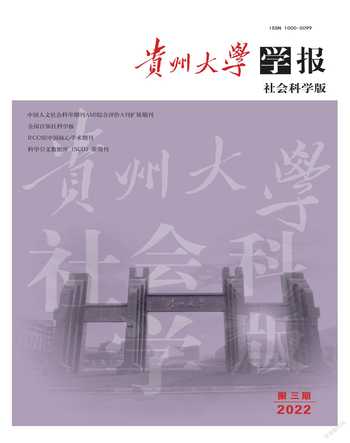論福柯的空間思想
摘要:福柯的空間理論起步于他的早期講演《他種空間》,后來在《規訓與懲罰》等一系列著作中,亦多闡發。福柯認為伽利略開啟的世俗空間傳統,今天依然有待開拓。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文化空間與實用空間等的對立,依然沒有破除。故他推崇巴什拉,即揭示了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同質的空洞的空間里。在《他種空間》里,福柯提出的“異托邦”是他空間思想的一個核心。異托邦是真實的地方,不是虛構空間。異托邦在又不在,歷時與共時并存,將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實場景同時呈現出來,又同時彼此沖突和反轉。但誠如烏托邦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反烏托邦,異托邦同樣也走向它的真實存在過的反異托邦。因此,規訓空間當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關鍵詞:福柯;他種空間;異托邦;規訓空間
中圖分類號:B5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099(2022)03-0001-08
言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間思想,福柯早年的一個講稿文本《他種空間》在當今風起云涌的后現代“空間轉向”中廣為傳布,并已成為一個經典。雖然這篇講稿的刊布,是在他去世的同年1984年。多年以后,在今日亦成故人的美國人文地理學家愛德華·索亞(Edward W.Soja)看來,當時福柯已經在醞釀類似于他本人“第三空間”那樣的理論體系了。索亞對福柯的空間思想與列斐伏爾有過一個比較:跟列斐伏爾相反,福柯自己的空間理論建構從未進入高度自覺的細節,他也很少把自己的空間政治學轉化為明確定義的社會行動綱領。不過我們依然可以說(福柯若經提示也會同意),他的全部著作,從《癲狂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癲狂史》(1961)到1984年他去世前不久(以及之后)出版的多卷本英譯性史的著作,其核心就是對空間性進行全面的批判的理解。[1]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本人在1974年出版的標志性著作《空間的生產》中,已經注意到福柯在《知識考古學》里也談到了空間。但列斐伏爾寫作此書時,顯然還未讀到福柯先時以及后來的空間熱情,并認為福柯沒有解釋清楚他所說的空間到底是指什么東西,以及它如何溝通理論領域和實踐領域。福柯當然知道空間是什么。作為讀者,我們反倒納悶,假若列斐伏爾寫作《空間的生產》時,業已聞知福柯《他種空間》這篇著名講演的內容,是不是還會埋怨福柯談論空間不夠深入?
一、空間的歷史
福柯在1967年3月14日的一次建筑研究會(Cercle détudes architecturales)上,發表過一個題為《他種空間》(Des Espaces Autres)的講演。這個講演的刊布姍姍來遲,直到福柯本人去世之后的1984年10月,才發表在《建筑,運動,延續性》(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雜志的第5期上,后收入《福柯言述集》(Dits et ecrits)第四卷。因為發表的文本未及經作者本人審核,故福柯的正式文集通常不收此文。但在福柯謝世前不久,這個講演的手稿在柏林的一個公共場合有過一次展示。由此可見,《他種空間》作為福柯空間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其著作權是不成問題的。
1967年是結構主義方興未艾,或者說是如日中天的年代。所以不奇怪福柯的這個《他種空間》講演,開篇談論的也是結構主義。福柯說,19世紀的一大困頓是歷史,發展與停滯、危及與循環、過去的不斷積累與世界降溫,諸如此類的主題叫人迷茫。故而,19世紀的神話資源從根本上說是來自熱力學第二定律;即是說,能量可以從溫度高的物體傳遞到溫度低的物體上面,但是反過來不能從低向高傳遞。但是今天卻不同,今天的時代是空間的時代,其特征是共時性而不是歷時性。我們處在一個并列、遠近和散布的時代。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不復是時間串聯起來的悠長生命,而成為一張用它自己的線索交叉連接起點與點的大網。故而:陸揚:論福柯的空間思想結構主義,或者至少集聚在這個稍許有點籠統的名號之下的東西,是在可以連接到一根時間軸線上面的諸多元素之間,建立起一種關系集合,以使這些元素呈現為并列的、彼此沖突的,又彼此包容的模樣,簡言之,呈現為一種建構。事實上,結構主義并不意味著否定時間;它認真關系到某種同我們稱之為時間和歷史的東西打交道的方法。[2]752這是說,空間本身有一段歷史。結構主義雖然奉行共時性的空間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著排除歷時性的時間線索。這以空間出現在我們今天的理論以及各種體系的視野里,并不是新鮮事情。對此福柯指出,在西方的經驗里,空間有空間的歷史。回溯歷史,中世紀就是不同地方的等級有序的集合,有神圣地方和世俗地方,被保護的地方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地方,城市地方和鄉村地方等的對立,所有這些地方都關系到人們的真實生活。而在宇宙學理論里,下面是陸地人間,陸地上面有天國,天國上面還有超級天國。有些地方的事物已經被劇烈移位過,有些地方的事物則天生穩穩就在那里。而正是所有這些地方的等級排列、反向排列,以及交叉排列構成了我們大體可以叫作中世紀空間的那東西。簡言之,中世紀的空間,就是“確認方位的空間”(espace de localisation)。
這個“確認方位的空間”,在福柯前一年出版的《詞與物》中,被表述為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之交被新柏拉圖主義復活的一個古老概念——“小宇宙”。據福柯所言,它是將兩個具有相似性對象的相互作用,應用于所有的自然領域之中。它意味著知識主體在每個事物中都能發現自己的映像,以及對浩大宇宙的深信不疑。反過來,最高領域中的可見秩序,將同樣反映在地球最深處的黑暗世界中。所以它表明:存在著一個巨大的世界,它的四周勾畫了所有被造物的界線;在世界的另一端,存在一個享有優先權的創造物,它在自己的有限向度內,產生了有關天空、星星、山脈、河流和風暴的巨大秩序;相似性的相互作用正是在這一基本的類推的有效界線內展開的。因這個事實,從小宇宙到大宇宙的距離無論有多大,但都不可能是無限的。[3]很顯然,這里以人為小宇宙,對應于自然大宇宙的空間觀里。在福柯看來,它們終究還是有邊界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大自然,類似符號與相似性的相互作用,依據宇宙的復制形式,把自身封閉了起來。
福柯認為這個確認方位的空間,是始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因為伽利略遭受迫害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發現或者重新發現了地球圍繞太陽旋轉,而在于構建了一個無限的開放空間。在這個無限的空間里,中世紀的方位紛紛消解,不復具有任何意義,而化解成為其運動中的一個點。換言之,從伽利略和17世紀開始,“廣延”(eténdue)替代了方位確認。空間由此從中世紀的方位確認轉移到近代的擴展模式。及至今日,廣延又被“位置”(emplacement)所替代。“位置”可以定義為點與點之間的關系。而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位置或者生活空間問題,并不僅僅是探究世界是不是有足夠空間供人類生存,同樣也在于探問人類因素以什么樣的相鄰關系,怎樣儲存、循環、標簽和分類,方能在特定環境中達到特定目的。所以,位置與位置之間的關系,就是我們今天時代里的空間形式。這也導致今天時代的焦慮,何以從根本上關牽著空間,而遠勝于關牽時間。
問題是,伽利略開啟的世俗空間傳統,在福柯看來今天依然有待于開拓。對此福柯指出,今天我們的生活依然是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所統治,我們的制度和實踐依然沒有摧毀這些空間。例如: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家庭空間與社會空間、文化空間與實用空間、休閑空間與工作空間等,不一而足。對此,福柯高度推崇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的詩學》,認為巴什拉此書中的現象學描述可以給予我們許多啟示。福柯說:巴什拉的劃時代著作和現象學描述教導我們,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同質的空洞的空間里;恰恰相反,我們生活的空間也深深浸潤著各種特質,甚或通盤就是異想天開。我們第一感知的空間、夢幻空間和激情空間,各各具有自身的內在特質:有亮麗的、輕盈的、透明的空間,也有晦暗的、粗糲的、蒙障重重的空間;有高高在上的最高空間,也有深深塌陷的泥淖空間;還有涌泉般流動不居的空間,以及石頭或水晶般凝結固定的空間。[2]754但福柯也認為,巴什拉的分析對于思考今日之時代固然提供了一個出發點,但主要還是涉及內部空間,而他現在同樣希望來談一談外部空間。
福柯所說的外部空間,也就是我們的生活空間。他認為在這個空間里我們的生命、時間和歷史在不斷遭受侵蝕。這個空間說到底,本身也是一個“異質空間”(espace hétérogène)。異質空間不是真空,不是我們在其中可以隨意安置某人某物,可以把它點綴得五光十色的空間。反之,它是一系列關系,而正是這關系在界定著我們的交通、街道和運動。通過這個關系群集,我們可以描述咖啡館、影院、海灘這些休閑場所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描繪封閉或半封閉的棲居地,如住宅、臥室、床榻,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場所之間,福柯指出,他最感興趣的是那些在這一大張關系網里,具有特別屬性的地方,因為這些地方可以質疑、抵制,甚至顛覆它們所反映的關系集群。這些特殊的空間,福柯認為主要存在兩種類型:一種聯系著所有其他空間,那是烏托邦;一種對立于所有其他空間,那是“異托邦”。
二、異托邦
“異托邦”(hétérotopia)是福柯空間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所謂異托邦,是相對烏托邦而言。福柯對于烏托邦的定義:它是沒有真實方位的地方。但總體來看,這些地方同社會的真實空間多多少少有著曲曲直直的關系。它們以完美的形式表現社會本身,或者把社會顛倒過來,那是反烏托邦。不過說來說去,大凡烏托邦,指的都是非真實的地方。
但異托邦不同,異托邦是真實的地方。福柯指出,在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文明里,都有這樣一些確實存在的真實地方,它們有時候就像沒有方位的烏托邦,落實在了真實場地,同一文化中的所有其他真實場景,同時呈現出來,又同時彼此沖突和反轉。這樣的地方,其實是在一切地方之外,即便它們在現實中能找到具體方位。這樣一個歷時與共時并存,在又不在的地方,便是福柯的“異托邦”。對此,福柯做了一個鏡子的譬喻:因為這些地方跟它們所反映和言說的場所完全不同,考慮到跟烏托邦的對比,我將它們稱之為異托邦。我相信在烏托邦和這些完全不同的他種場所,即異托邦之間,還可能有某種混合的、聯合的經驗,那可能就是鏡子。鏡子說到底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它是一個沒有方位的地方。在鏡子里,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看到自己,那是一個敞開在平面背后的非真實的虛擬空間;我就在那里,可是我并不在那里,是一種影子讓我看到了我自己,讓我在我不在場的地方看到自己,這就是鏡子的烏托邦。但是就鏡子存在于真實世界,就我占據的位置起到反作用而言,它也是一個異托邦。[2]756對此,福柯進一步的解釋是,從鏡子出發,我發現我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鏡子里我的目光從虛擬空間的深處看過來。我在照鏡子,這本身是真實的,但是鏡子里的我卻是真實又不真實的幻相。這面處在真實與虛擬空間之間的鏡子,在福柯看來,其功能就照出了烏托邦和異托邦的雙重屬性。
那么,異托邦的意義又當何論?即是說,在一個特定社會中,我們如何來系統研究、分析、解讀這些他種空間呢?福柯提出,圍繞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異托邦空間,其真真假假的論爭可以稱之為“異托邦學”。福柯進而條分縷析,闡述了異托邦學和異托邦的六個原則。
福柯認為烏托邦學的第一原則,就是普天之下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構成異托邦。這是說,異托邦無所不在。但即便無所不在,異托邦卻沒有絕對統一的形式。它形態各異,不過大體可以歸結為兩大類型。其一見于原始社會,可名之為危機異托邦。比如說有一些圣地和禁地,專門留給處在危機狀態的人眾,如青少年、處于經期的女人、懷孕婦女、老人等。迄至今日,危機烏托邦已日漸消失,但也有若干剩余,如19世紀的寄宿學校,年輕人的兵役服務等。福柯并舉了“走婚”(voyage de noces)這個一直到20世紀中葉依然存在的古老例子,指出女孩子失落貞操,可以發生在許多“烏有之地”,火車和蜜月旅館就是這一類烏有之地,它們都是沒有地理標志的異托邦。
異托邦學的第二個原則是同一個異托邦在社會歷史中,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功能。對此,福柯舉了公墓的例子。墓地當然不同于普通的文化空間。但是它跟城邦村莊都有關系,因為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親人埋葬于斯。福柯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公墓事實上一直存在,但是經歷了很大的變化。直到18世紀末葉,公墓還一直位居城市中心,緊挨著教堂。公墓里也有等級,有骸骨教堂、個人墳墓,教堂里還有墓穴。但是從19世紀開始,隨著骨灰盒普及大眾,公墓向城市邊緣遷移。這跟擔憂墓穴傳染疾病的恐懼直接相關。如是公墓不復是城市的不朽神圣心臟,反之變身為了“他種城市”,每個家庭在這里都有一個幽冥居所。
第三個原則是指異托邦可以將互不相容的若干空間和場所,并置在同一個地方。在這一方面,舞臺和電影院便是例子。舞臺上互不相干的地點接連展開,影院中我們在一方二維的銀幕上看到了大千世界的三維空間。但這一類異托邦里,最典型的例子是花園。對此,福柯高度贊賞古代東方花園,指出波斯的傳統花園是一個神圣空間,它的長方四邊形代表世界的四個部分,中心有噴泉水池,它較外圍更要神圣,好比世界的肚臍。花園里各種草木匯聚到同一空間,構成了一個微觀宇宙。就此而言,波斯地毯也是花園的復制品,它將整個世界的完美符號聚于一體,是在空間中流動的花園。因此,花園就是一個普世性的幸福異托邦。今天的動物園,就是從花園脫胎而出的。
第四個原則指的是異托邦經常聯系著的時間的片段。這是說,為了對稱的緣故,異托邦經常走向所謂的“異托時”(hétérochronies)。對此,福柯又舉了墓地的例子,他指出,當人們同傳統的時間徹底割斷,異托邦就開始全力以赴了。所以,墓地是異托邦的典型地方,因為人生到頭,墓地就伴著這個古怪的異托“時”,開始進入貌似永恒的另一種時間。而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異托邦和異托時錯綜復雜交合在一起。比如在博物館和圖書館里,異托邦就在無窮無盡地積累時間,將各個時期的文物、文獻和檔案,所有的時代、所有的形式、所有的趣味,集聚在同一個空間。福柯指出,這個無限積累的理念是屬于我們的現代性。不同于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永久性,福柯發現異托邦和異托時的連接方式還有一種轉瞬即逝的形式,那就是節慶。節慶的場合通常是在市郊的一片空曠地上,一年一度或一年兩度,三教九流各式人眾匯合過來,摔跤的、耍蛇的、算命的,無所不有。這是為異托邦和異托時的另一典型景觀。
第五個原則,異托邦應是一個既開放,又封閉的系統,彼此隔絕又彼此滲透。總體來說,異托邦的空間并不像公共空間那樣可以自由出入。進入是強制的,如兵營和監獄。有一些地方要事先提出申請,或者經過潔凈儀式,方可入內,如穆斯林的土耳其浴室。還有一些地方仿佛是敞開大門,誰都可以自由出入這類異托邦空間。然而,那只是幻覺。如巴西過去有些大農莊的著名臥室,游人盡可以推門進去,睡上一晚。但是,這些臥室跟主人家庭區域并不聯通,所以游客到底是過客,并不是主人邀請的貴客。你以為是進去了,實際上還是沒有進去。
最后一個原則是在異托邦跟剩下來所有空間的關系中,在兩極之間發揮功能。兩極都旨在創造一個虛幻空間,可是在這個虛幻空間里又見出一切真實空間,它們是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反過來說,兩極的功能是意在創造另一個真實的空間,一個完美的、精工細作的、有條不紊的他種空間,而不似我們自己的空間那樣雜亂無章。所以,它可以作為真實空間的一種補償。對此,福柯舉了殖民地的例子。他指出第一波殖民熱潮發生在17世紀,英國人在美洲建立的新教徒社會,就是絕對完美的他種空間。與此相似的還有南美洲耶穌會的殖民地,井井有條堪稱奇跡。如巴拉圭的耶穌會村莊,就嚴格按照長方形來布局,矩形的底部是教堂,一邊是學校,一邊是公墓,教堂前方有一條街道伸出,跟另一條街道十字相交,沿著這兩根軸線,居民各就其位,如是完美演繹了基督的十字架符號。是以不奇怪,在福柯的《他種空間》這篇講演中,最后的話是:封閉屋舍和殖民地,是異托邦的兩種極端類型。說到底,我們可以想象船是一種漂流空間,一個沒有地方的地方,它自給自足,將自己封閉起來,同時又漂向無限的大海,從港口到港口,從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從屋舍到屋舍,一直漂到殖民地,尋找它們藏在花園里的珍貴寶藏。這樣想象下來,你就會懂得從16世紀到現在,為什么船是我們文明中經濟發展的偉大工具(今天我不談經濟),而且同時也是最偉大的想象載體。船是最典型的異托邦。沒有船的文明中夢想枯竭,間諜替代冒險,警察替代了海盜。[2]762至此我們發現,福柯談他種空間再是云遮霧罩,終究還是圍繞著以大西洋為中心的海洋文明展開的。烏托邦也好,異托邦也好,大陸文明跟它們沒有關系。大陸文明在福柯看來,在他的“他種空間”里不值一道。
三、規訓的空間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在1969年面世,該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質疑歷史研究的連續性。用福柯本人在該書“引言”中的話說,那些被稱為思想史、科學史、哲學史,以及文學史的學科,不管它們叫什么名稱,大都業已偏離傳統史學家們的研究和方法。在這些學科中,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從原來描繪成“時代”或“世紀”的廣闊單位,轉向斷裂現象。故人類思維的連續性,今天正在受到挑戰,反之斷續性的重要性呼之欲出。就他本人而言,福柯指出,對于精神病理學、醫學、政治經濟學這一類傳統學科,他不會貿然深入它們的內在形式和潛在矛盾,但是他會提出問題:它們根據什么樣的規律形成?它們在什么樣的話語事件基礎上被割裂出來,以及它們最終是否在它們被接受的并且近乎成為制度的個體性中,不是那些更為穩定單位的表層結果?我接受歷史給我提出的這些整體,只是隨即對它們表示質疑;只是為了解析它們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合理地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或者是否應把它們重建為另一些整體,把它們重新置于一個更一般的空間,以便在這個空間中驅除它們表面的人所熟知的東西,并建立它們的理論。[4]福柯這里的意思是明確的,那就是他的新歷史主義話語研究是將主要使用空間的方法,放入傳統史學想當然的連續性形式之中。惟其如此,可望打開一個更為寬廣的領域,將澄清原始材料即話語空間中的事件群體,作為視為一切批評行為的先決條件。
福柯1975年出版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被認為是受早期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與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現代性批判家的影響,系統且細致描寫了現代世界的空間轉化譜系。批判的主題固然一如既往,但福柯在此書中表現出來的空間意識,則被認為是以身體為中心,通過追溯刑罰體系的變遷,來寫權力機制的衍變。酷刑、懲罰、規訓、監獄,由此成為該書的四個典型場景。在該書中,福柯從落筆開始即不厭其詳,細數18世紀以降作為“公共景觀的酷刑”慘不忍睹地撕裂肉體。進而表明,西方現代世界形成的歷史,同樣也是一部空間轉化的歷史,故必須在權力、知識和肉體的關系之中,來分析現代社會的轉型。
《規訓與懲罰》開篇寫的是公共空間中的公開處決,描述了18世紀的劊子手如何在廣場上搭起行刑臺,用燒紅的鐵鉗子撕開犯人的胸膛和四肢,用硫磺來燒犯人執弒君兇器的右手,再用融化的鉛汁灌入撕裂的傷口,然后四馬分尸。對此福柯的感想是,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是消失了,這是事實,即在數十年間,對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臉上和手臂上打烙印、示眾以及暴尸,這些現象終究是消失了。但是懲罰沒有消失:因此,懲罰將逾益成為刑事程序中最隱蔽的部分。這樣便產生了幾個后果:它脫離了人們日常感受的領域,進入抽象意識的領域;它的效力被視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見的強烈程度;受懲罰的確定性,而不是公開懲罰的可怕場面,應該能夠阻止犯罪;懲罰的示范力學改變了懲罰機制。結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與其實踐相連的暴力而承擔社會責任。[5]至此,我們可以說,福柯下沿的是與他的本國同胞列斐伏爾迥異其趣的另外一個空間的批評傳統。誠如福柯《他種空間》和《權力的地理學》等文獻中闡述的他種空間與異托邦理念,多被嗣后學者賦予多元空間的后殖民解讀和性別解讀。從《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對18世紀中期以來刑罰機制現代變革的分析,以及對全景暢視監獄機制下空間、身體、權力的關系考察,也都啟發了我們對社會空間與主體認同的新認知。
福柯的這一思想,直接導致了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批評對文藝復興戲劇的重新解讀。格林布拉特本人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暴風雨》中通力破解權力關系,讀出普洛斯庇羅對卡列班的無情殖民,即為一例。福柯的權力—空間地緣政治學,終而演繹為性取向—性別建構的主體性空間對峙。這一方面,大衛·貝爾(David Belle)等人的《繪制欲望:性的地理學》、羅賓· 朗赫斯特(Robyn Longhurst)的《身體:探索流動的邊界》以及琳達·瓊斯頓(Lynda Johnston)等人的《空間、地方和性:性向地理學》等一批文獻,都可以顯示福柯的影響怎樣在性別和地緣政治的每一層面蔓延。
就規訓與懲罰的主題而言,在福柯看來,歐洲社會的規訓,是從空間的分配起步的。具體來說,為了實現規訓的目的,需要以下數種機制的配合。第一是需要一個封閉的空間,圈定一個自我封閉的、有別周圍世界的場所。這方面有對流浪漢和窮人的“大禁閉”,也有一些更謹慎也更為隱蔽的措施。還有逐漸采用修道院式寄宿制的大學和中學,以及兵營,它可以約束大軍,使不至擾民,避免駐軍與地方當局的沖突。福柯枚舉的統計數字是,直到1745年,法國大約有320個兵營。1775年,兵營內的總人數達到20萬人。此外,工廠也逐漸形成大面積的單純而明確的工業空間。日趨集中的管理模式,便于獲取最大利益,消除偷盜、怠工、動亂等不利因素。
第二,有鑒于“封閉”原則在規訓中不可能一勞永逸,第二種機制是根據單元就位或者分隔。它意味著規訓空間可以進一步細致化,按需分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個位置上都有一個人。如是便于監督施行,誰到場了,誰缺場了,誰盡力了,誰開小差了,一目了然。這是用紀律組織起來的一個可解析的空間。福柯發現這個機制類似修道院的密室,它通常是分格單元式的,適合禁欲主義之需。他并引法國18世紀警官尼古拉·德拉馬爾(Nicolas Delamare)《論警察》中的描述:“睡覺是死亡的影像,寢室是墓地的影像……盡管寢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擋,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寢都不會被人看見。”[6]163即便如此,福柯認為這一方式,也還是顯得粗糙。
第三是按用途分隔出特殊空間。比如陸軍醫院和海軍醫院,就有嚴格的隔離區域,以防傳染病的流行。每個病人都被記錄在冊,分床隔離,對癥處置。隨之形成一種行政空間和政治空間,借此醫療空間形成了。還有18世紀末葉出現的工廠,它將人員分配、生產機制的空間安排,以及其他崗位分配結合在一起,構成的布局是一方面可以統攬全局,一方面可以監督到每一個崗位。工人的體力、敏捷性、熟練性、持久性都歷歷在目。這一規訓空間的形成,故而成為大工業興起時期的必然。
第四是教育空間的等級排列。等級替代作為統治單位的領土和作為居住單位的地點,成為新的規訓空間形式。福柯舉了班級的例子,他指出在耶穌會的大學里,每個班級有二三百名學生,十人一組。這呼應了當年羅馬和迦太基行伍中的“十人團”基本形式。每個學生的位置,根據他作為“十人團”中一名戰士的角色來加以確定。從18世紀開始,“等級”愈益彰顯,學生在課堂和校園中的座次和位置、每個學生完成各項任務和考試后的名次、學生每周每月每年獲得的名次、年齡組的序列、依難度排列的科目序列等,皆排定在等級空間之中而交替換位。對此福柯說:這種系列空間的組織,是基礎教育的重要技術變動之一。它使得傳統體制(每個學生受到幾分鐘教師的指導,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學生無事可做、無人照顧)能夠被取代。它通過逐個定位使得有可能實現對每個人的監督并能使全體人員同時工作。它組織了一種新的學徒時間的體制。它使教育空間既像一個學習機器,又是一個監督、篩選和獎勵機器。[6]167空間與時間的因素在這里再度交叉起來,成就為多元并置異托邦的又一種規訓形式。據福柯自己的解釋,規訓的策略與自然分類法不同,后者是以特征與范疇為基軸,規訓策略則是以單數和復數的關系為基軸,既對個體作特征描述,又對特定的復雜對象加以整理,從而為“細胞權力”(cellular power)的微觀物理學打下了基礎。
福柯認為規訓空間的典型,是18至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發明的全景暢視監獄(panopticon)。這類監獄的構造是在一個環形建筑群中心,修建一個高高的瞭望塔。瞭望塔頂端有一圈大窗戶,面對包圍著它的環形建筑。環形建筑被分隔成一個個狹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筑群的橫切面,佩以兩個窗戶,一個朝里跟瞭望塔頂的窗戶相對,一個朝外用于采光。每個囚室里關進一個瘋人、病人、罪犯、工人或者學生,其一舉一動,假以跟瞭望塔恰好相反的光源角度,被塔頂的監視人看得清清楚楚。由于犯人知道自己時刻暴露在監視之下,以至于即便塔頂無人,他們的舉動也習慣成自然,變得規規矩矩。福柯認為邊沁設計的這一全景暢視監獄,顛覆了傳統監獄的原則,更具體說是推翻了它的三個基本功能:封閉、黑暗和隱蔽。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6]226。簡言之,權力不復體現在個人身上,而是變相體現在了空間與光的精心安排之上。作為《規訓與懲罰》中被引述最多的這個全景暢視監獄的建筑理念,它不妨說是肉體在空間中的另一種定位,這個身體為權力所規訓的定位,可見在福柯看來是無所不在。不僅是監獄,醫院、兵營、工廠和學校亦然。由是觀之,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空間,不啻是一個規訓和懲罰的大監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學》開篇即稱其為人類最高貴感官的視覺,由此也與權力狼狽為奸,成為了監禁與懲罰的幫兇。
美國批評家菲利普·韋格納(Phillip Wegner)在他題名為《空間批評》的文章中,認為福柯的空間思想是跟列斐伏爾分道揚鑣。列斐伏爾關注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化中的空間關系,福柯則致力于探究權力結構空間轉化的歷史譜系,特別是把聚焦的中心轉向了身體。如是在福柯筆下,個人的身體成為公共“劇場”中的主體,承受遠離日常生活的儀式空間中的嚴厲懲罰。然而,正因為這一體系變身為了驚心動魄的公共景觀,也導致它極不穩定,隨時有可能被顛覆過來。故而:在這一古老的權力邏輯中,逐漸滋生出來一個新的體系,其中每一個身體發現自己被定位在“一個巨大的封閉、復雜,有等級森嚴的結構里”,而屈從于一個監控與操控的連續體制。一個福柯名之為“規訓”的整個運作系列——“工具、機制、程序、應用層面、目標”——應運而生,以便生產出“規范”的主體,同時標記出一個精心完成的異常行為王國:“如此規訓生產出順從的熟練的身體”,“馴服的”身體。[7]韋格納上文引號中的文字,都出自福柯的《規訓與懲罰》。規訓的空間由是觀之,該是福柯謂之“他種空間”的一種資本主義權力壓迫的空間范式;更具體地說,這是他不厭其詳規定出的六條原則的“異托邦”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誠如烏托邦可以走向它的反面——反烏托邦,異托邦同樣也走向它的真實存在過的反異托邦。規訓與懲罰的空間,不過是不算姍姍來遲的一個重要例子罷了。
參考文獻:
[1]SOJA E.Third 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 Places[M].Malden:Blackwell,1996:147.
[2]FOUCAUL M.Des Espaces Autres [M].Paris:Editions de Gallimard,1994.
[3]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M].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43.
[4]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31.
[5]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10-11.
[6]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
[7]WEGNER P E.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uality[M]//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183.
(責任編輯:張婭)
On Foulcaults Thought on Space
LU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Abstract:Foucaults space theory, formed in his early speech “Des Espaces Autres”, is illustrated in a series of later works such as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Foucault believes that the secular spac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Galileo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today, an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rivate space and public 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practical space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yet. Therefore, he praises Gaston Bachelard for revealing that people do not live in a homogeneous empty space. Foucaults “heterotopia” concept, first proposed in“Des Espaces Autres”, is a core of his spatial thought. Heterotopia is a real place instead of a fictional one, both here and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the coexistence of being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resenting a collage of all real scenes in the same culture simultaneously, with every single scene conflicting and reversing each other though. However, as Utopia can go to its opposite Anti-utopia, heterotopia may go to its opposition that really ever existed as well, which is illustrated by the space of discipline, one of the important cases.
Key words: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heterotopia; space of discipline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項目: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15ZDB084)。
作者簡介:陸揚,男,上海人,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