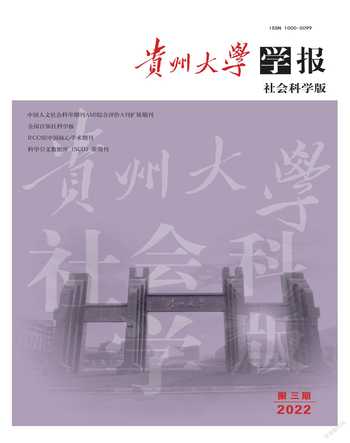15-18世紀廣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經濟開發與社會變遷
摘要:15-18世紀,廣西梧州經歷了從“軍事重鎮”到“商業重鎮”的社會變遷。正統年間,大藤峽瑤亂日益嚴重,開啟了梧州地區的軍事化進程。景泰、天順年間,動亂愈演愈烈,為統一事權、協調資源,成化六年,兩廣總督開府常駐梧州。此后,梧州軍政建設不斷加強,并成為嶺南軍事重鎮。明后期,隨著地方秩序的逐漸穩定,梧州軍事地位日益下降,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重視,開始向商業城鎮過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區得到大力開發,米糧、食鹽等傳統貿易亦保持興盛,逐漸形成以蒼梧戎圩為中心的商業貿易網絡。至18世紀,梧州成為商業重鎮,社會風氣亦漸趨奢華。梧州個案表明,邊疆重鎮的形成和發展與區域秩序控制、國家權力滲透、山區經濟開發等因素密切相關。
關鍵詞:廣西梧州;邊疆重鎮;國家整合;區域開發;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K291/29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099(2022)03-0082-11
廣西梧州地處南疆,歷史悠久,素有“千年嶺南重鎮,百年兩廣商埠”之稱,對華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目前,學界關于明清時期梧州地區軍事、社會、經濟等問題已有諸多成果①,并且認識到梧州為明代軍事重鎮和清代商業重鎮,然而對于梧州如何從“軍事重鎮”轉變為“商業重鎮”則缺乏細致的梳理和論述。其實,這一演變過程不僅源于梧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同時也與明清時期西江流域的人群互動與國家整合等問題密切相關,值得深入探討。本文擬以秩序控制與經濟開發為中心,對梧州地區②進行長時段考察,揭示其15-18世紀從“軍事重鎮”到“商業重鎮”的社會變遷。
一、明代中期地方動亂與梧州軍事地位的提升
明代中期,廣西大藤峽“猺亂”③爆發,對梧州等周邊地區的社會秩序造成嚴重影響。自宣德年間始,廣西潯、梧等府“蠻寇作耗,攻劫鄉村,官軍不敷”[1]309。正統年間,“猺亂”日益嚴重,正統五年(1440)十月至次年二月,大藤峽“山賊時常出沒”,流劫藤、容等縣,“被其殺死及傷者多,又擄去男婦六十余人,牛畜近百,強占近山一帶百姓納糧田地耕種,搶劫不已”[2]52。除大藤峽地區“猺亂”頻繁外,兩廣界鄰地區同樣爆發動亂。正統六年(1441)十一月,廣西總兵柳溥奏稱:“岑溪及廣東瀧水二縣,猺賊駱宗安等二百余人,劫殺岑溪縣連城鄉民,死傷者五十余人,復火其倉。”[1]1703廣西動亂的不斷加劇引發了明英宗的重視,他嚴敕地方官員必須“夙夜用心,以求安輯。”[2]52正是地方動亂開啟了梧州地區的軍事化進程。正統年間,明廷大量征調桂西狼兵進入梧州地區屯戍駐守,容縣、興業、北流、陸川“俱有狼總統領。”[3]卷28同時,梧州地區的城池得到大力整修。總兵柳溥充分認識到城池對于御寇的重要性,指出梧州等地“猺獞夷人叛服不時,所賴者,城池濠塹耳”,因此“每于農閑時,往來巡視,督工修筑,庶邊鄙有備。”[1]2179正統五年(1440),因“懷集守御千戶所逼近賊巢”,廣西按察司胡智“請甓其土城”[1]1257,正統十四年(1449)又“請筑以磚”[1]3474。正統十年(1445),梧州府城毀于戰亂,次年知府諸忠即加以重修[4]233。同樣為了抵御動亂,正統十一年(1446)廣西大量增設巡檢司,其中梧州地區共計二十七所[1]2907。
正統末至景泰初的北虜南亂對兩廣地區的軍事、政治形勢產生了重要影響。黃蕭養叛亂使朝廷意識到兩廣地區軍備松懈、事權不一的狀況;土木堡之變則迫使朝廷召回各地資歷較深的高級武將,以填補京營將領損耗的空缺,兩廣鎮守工作,則由資歷較淺的將領負責[5]。景泰年間,廣西蠻寇行劫郡縣,廣東、廣西總兵互相推托,擁兵自衛,致使寇亂蔓延廣東。鑒于兩廣官員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景泰三年(1452),明廷遂命右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但此時總督屬臨時差遣,事畢即還朝[6]。王翱回京后兩廣官員之間的事權問題又再次顯現。秦浩翔:15-18世紀廣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經濟開發與社會變遷英宗復辟后召回各地督撫,兩廣隨即動亂頻傳[5]。天順年間,大藤峽及周邊地區的動亂愈演愈烈,且波及甚廣,梧州地區的城鎮更是被多次攻破。天順二年(1458),藤縣地區蠻賊“不時出沒,攻劫縣治,殺擄人民,燒毀房屋”[1]6137。天順三年(1459)四月,梧州、潯州等地“猺、獞、苗賊攻劫鄉村、城市,殺虜軍民共一千九百余口。”[1]6404同年五月,“廣西流賊越過廣東,攻圍肇慶等處州縣,劫掠鄉村,為患不已”[1]6415,六月,“流賊攻破容縣,屠殺居民,劫掠官庫”[1]6424。天順四年(1460)二月,“強賊攻梧州府,哨守指揮蕭瑛逾江避之,賊遂攻破城池,殺虜官民及官庫財物”[1]6544。天順六年(1462),兩廣總督葉盛認為動亂難以平息的重要原因在于“兩廣將官,各無統攝”,且“謗毀日增,遂成嫌隙,爾我不顧”,因此奏稱:今臣等看得廣西梧州府是兩廣交界地方,北抵曾城,南抵交趾,程各半月,東抵廣東省城,順流而下,僅逾七日,最為緊關。中路控扼兩廣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由梧州北南兩江水面偷度。因無將官重兵總制其間,又因先年原守廣西地方,貴州、湖廣官軍一萬五千俱不赴調,舊守營堡,俱各廢棄,以此不能守把,賊人肆志。
伏乞皇上特勅該部會議,合無于梧州立為帥府,掛印征蠻將軍總兵官鎮守,節制兩省,會官專管軍馬盜賊事務……如此庶得耳目一新,號令丕變,將權歸一,地方行事才得爾我相和,彼此相顧,實為經久便益。[7]然而,葉盛的提議并未被朝廷采納,反而在不久后遭人彈劾而去職,但梧州的戰略地位已初步顯現。天順七年(1463),梧州地方秩序再次遭到嚴重沖擊。四月,“流賊攻破岑溪縣及郁林州,戕殺官民,剽虜財畜”[1]7045,其后“破懷集縣及守御千戶所,燒毀公廨,劫去官民財物”[1]7171。十一月“大藤峽賊夜入梧州城”,“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軍民無數,大掠城中”[8]27。鑒于天順末年,以侯大狗為首的大藤峽“猺亂”越發不可收拾,成化元年(1465)正月,明廷“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進剿大藤峽,取得大勝,“斬首無算”[9]。大藤峽之役告捷后,韓雍留任兩廣,繼續總理軍務。考慮到“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后,易動而難安”,為鞏固勝利,韓雍決定繼續加強大藤峽周邊地區的軍事控制。成化二年(1466),韓雍奏請設立五屯屯田千戶所,以千戶李慶為之酋帥,以僮首覃仲瑛為之吏目,“筑城分哨”,加強梧州西北部的軍事防御,借僮人之力抵御瑤人[10]。同時,韓雍還對梧州地區的城池進行大力整修。成化二年(1466),韓雍將郁林州城“重加筑砌”,“筑欄馬垣,立瞭望樓十、鼓樓一”,并新修博白縣城門樓,委知縣謝鉉用磚包砌藤縣縣城,委縣丞孔舒修筑北流縣城池。成化三年(1467),韓雍將府城“增高一丈,造串樓五百六十九間,城下設窩鋪三十六間,宿守夜軍士。浚濠深三丈,闊一丈,五尺內外皆樹木柵”。成化四年(1468),又將懷集縣城“砌以磚石”,并修建府城“東、南、北門甕城,重建五門樓、鐘鼓樓”[4]233-242。
通過韓雍征剿大藤峽的成功經驗,兩廣地方官員已充分意識到事權統一對于秩序控制的重要性,紛紛奏請設立總督,開府常駐地方,而梧州則是最為理想的地點。成化四年(1468)三月,韓雍即奏稱:“兩廣地方廣闊,軍民事繁,一人不能遍歷,乞各增文職大臣一員,分理巡撫,仍命文武重臣各一員,專在兩廣接界梧州府駐扎,提督軍務,總制軍馬”[8]1064。但未及朝廷回應,韓雍便于成化五年(1469)春,以丁憂去職,此后“賊勢復張”[8]1414。是年冬,廣東巡按監察御史龔晟、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再次提議:“兩廣事不協一,故盜日益熾,宜設大臣提督兼巡撫,而梧州界在兩省之中,宜開府焉。”“于是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與(陳)瑄開府于梧”[11]。成化六年(1470),總督衙署建成,兩廣總督常駐梧州[12]。開府之后,韓雍進一步加強梧州的軍政建設,使其軍事地位繼續提升。成化六年(1470),韓雍在梧州地區“設營堡三十余處,府境道、府江道皆置哨守,調廣東各衛所旗軍一萬員名,分戍各營堡江道,設坐營司統督之,并征派廣、肇、韶三府屬糧米五萬石,解梧以備行糧。”[13]卷10此后,廣東班軍戍守梧州成為定制。同時為了擴充軍餉來源,韓雍請立水關,“榷鹽、木諸貸,以充軍實”[13]卷4。
韓雍大征之后的數十年間,大藤峽地區的局勢相對安定,然而至正德、嘉靖年間,動亂再起,梧州地區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再次加強。正德年間,明廷再度征調大量狼兵至梧州屯戍駐守,崇禎《梧州府志》載:“正德間流賊劫掠,調狼人征剿,鄉民流徙,廬畝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輸納,一藉其戍守。”[4]128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平定瑤亂后指出,藤縣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夷巢穴,最為要害”,“宜設一鎮,增筑高城,而設守備衙門,取回五百兵,分調哨守”[14]2200。此議為明廷采納,梧州西北部防御再次得到加強。同時,王守仁奏請對桂西狼兵實行“更番戍守之法”,其中“戍梧者四千名”,來自左右江各土司,“一年一戍,周而復始”,“以其有頭目管之,曰目兵”[4]689。此后,目兵戍守梧州成為定制。成化初年,明憲宗尚稱梧州為“蕞爾小城”[8]27,及至嘉靖中期,梧州已是嶺南軍事重鎮。嘉靖《廣西通志》稱:“(梧州)地總百粵,山連五嶺,蓋二廣上游八桂門戶也,故于此建節鎮,則南援容邕,西顧桂柳,東應韶廣,北可坐制陽峒諸夷,而安南無宿憂。”[15]卷2楊芳在《殿粵要纂》中寫道:“梧踞五嶺之中,囊九疑、三江之槩,為粵東西咽喉。西枕藤峽、八寨,諸酋出沒無時。東接信宜、封川,鼠竊狼吞,窟穴其間。曩屢勤師出征,旋服旋叛。迄今百有余載。山防江哨,棋布星列,總一郡十屬,所戍守軍兵,凡一萬有余。蓋矻然稱重鎮矣。”[16]但同樣指出:“第頃來帑藏浸耗,內地虛曠,歲登物產不供,或半需于鄰,或半需于商,小大坐食,卒惰而將驕,客兵多不用命,識者謂此非細故也。”[16]嘉靖四十五年(1563),蒼梧道僉事林大春亦稱:“梧州為東南重鎮,實兩省冠裳之會,三軍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鄙,非通都大郡。供俗尚簡樸,無高堂華屋之觀。”[17]
可見,此時的梧州已為“重鎮”,但主要指“軍事重鎮”,其社會經濟尚難稱繁榮。原因在于連年用兵,使梧州財政匱乏。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即指出,自征剿思田叛亂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余萬”,“今梧州倉庫所余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18]張瀚亦稱,“招者履叛,兵連禍結,征調煩勞,財力匱竭”[19]。另外,府江、西江兩大水路交通要道動亂頻繁,嚴重制約了梧州社會經濟的發展。蔣冕在《府江三城記》中說道:“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洄洑湍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為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劫。官舟商舶往來,為所患苦,蓋非一日。”[20]蘇濬在《兩廣郡縣志》中亦指出:“(梧州)右枕藤峽、八寨,諸酋往往出沒;左接粵東,犬牙相結,而狐穴狼窟,時跳梁其間,烽火相望,刈人如蓬藋然。于是閭里蕭條,沃土為墟矣。”[21]
綜上分析,明代中期兩廣地區動亂頻繁,為了統一事權、協調資源,兩廣總督之設勢在必行,梧州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為開府的最佳地點,并在一系列軍事政策的影響下逐步成為嶺南軍事重鎮,發揮控扼兩省的關鍵作用。然而連年戰亂,軍費浩繁,交通不暢,梧州地區的社會經濟未能得到充分發展。
二、明代后期梧州地區的秩序控制與社會轉型
嘉靖中期至隆慶、萬歷年間,是梧州地域社會變遷的關鍵節點。這一時期,隨著大藤峽“猺亂”的逐漸平定,以及兩廣界鄰地區社會秩序的日益穩定,梧州軍事地位有所下降,行政事務的重心開始轉向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
1.兩廣界鄰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與梧州軍事地位的下降
王守仁大征之后,西江上游地區的社會秩序基本穩定,梧州地區的軍事任務也由征剿大藤峽轉變為招撫兩廣界鄰地區的“化外之民”。自嘉靖中期開始,明廷調動軍隊,增設兵營,對梧州山區的非漢人群進行征剿或招撫,將其編入戶籍,并征收賦稅。蒼梧縣羅峝、思馬等處瑤人“先年糾合焚家、東安等猺流劫,嘉靖十年編立排甲,耕佃”,石硯瑤人居兩廣交界,“嘉靖年(間)愿來屬蒼梧,約八百余人”。萬歷初年,懷集縣瑤戶作亂,官府“大兵剿滅”,并將其拋荒田地“歸官招種”,納稅征糧[13]卷8。岑溪縣六十三山“與羅旁接壤,猺獞嘯聚為患”,萬歷五年(1577),“賊首潘積善等畏威求撫,愿歸地輸糧”,總督凌云翼“設指揮千戶五員,分兵屯守,以防芽摩。”[22]1509萬歷六年(1578),容縣、蒼梧縣均有大量瑤人為明廷招撫。容縣,三山、山心等“皆東瓜山所屬,約五十余家,山巢崎險”,“萬歷六年,曾廷旺始愿輸田賦,興猺學”;山塘、黨入等“皆橫山所屬,約三十余家,先年流劫,萬歷六年,劉德厚始愿編戶入賦”;慶垌、柯木等“皆石羊山所屬,幾二百家”,“萬歷六年輸賦”;都盤、六壬等“皆雞籠山所屬,約六十余家”,有酋目駱廷鳳“倚山剽掠數年,萬歷六年始招服”[13]卷8。蒼梧縣,埇漢、員塘等處瑤人“叛服不常”,“萬歷六年設七山鎮彈壓猺峝”,老君峒、六寨等處瑤人“時與深源、焚家、北佗為害,后立大塘營彈壓之”。萬歷八年(1580),岑溪縣筑大峒城,“招獞目韋月統耕兵三百名,分十四營”,“屯耕把守”[23]卷2。萬歷九年(1581),岑溪縣六十三山諸瑤“仍負固不服”,明廷筑城,“設連城、北科等大營”,“以潯梧參將握重兵彈壓之”,并“招獞民百余人耕守”。萬歷十二年(1584),懷集縣于城西八十里立金鵝營,設耕兵防守[13]卷10。萬歷二十三年(1595)冬,岑溪縣再度發生動亂,粵東浪賊數百潛入七山,“誘諸猺劫掠”,“諸猺復仇,盡殺乾廂獞人,屠其村,復乘勢剽掠”。督臣陳大科“大破之,而猺患乃熄”[13]卷8。其后,陳大科提議:扎信地以重彈壓,將潯梧參將駐扎大峒;分割山界以便管轄,上七山專隸岑溪,下七山改隸藤、容二縣;拓修城垣以資保障[22]5751-5752。梧州地區的社會控制進一步加強。
隨著潯、梧地區社會秩序的不斷加強,兩廣動亂的核心區域發生轉移,梧州軍事重鎮的地位開始下降。嘉靖中后期,西江上游的“猺亂”雖基本平定,但東南沿海地區卻屢遭倭寇侵擾,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始,兩廣總督吳桂芳即頻繁移巡肇慶總督行臺。隆慶年間,廣西桂林、柳州等地一批士大夫身居要職,極力倡議明廷大征古田,要求兩廣軍門分割資源,解決桂東北地區長期存在的“獞亂”問題,結果朝廷在桂林專設廣西巡撫,使其取代梧州成為廣西軍政中心[24]。兩廣總督移駐肇慶是梧州軍事地位下降的重要標志,萬歷七年(1579)十一月,總督劉堯誨大規模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大概于萬歷八年(1580)春季完工,兩廣總督府址正式由梧州轉至肇慶,兩廣防務重心亦隨之東移[12]。
長期以來,梧州軍隊逃亡、耗餉過多等積弊一直未能解決,更為重要的是梧州班軍及其軍餉均來自廣東,直接影響到廣東地區的利益,因此隨著梧州軍事地位的下降,不少地方官員,尤其是廣東官員開始主張裁撤梧州駐軍。隆慶年間,廣東巡按王同道已有裁撤梧州班軍之議,指出“督府開鎮于梧”,而廣東“共撥官軍二班,計一萬余員名哨捕”,共派“本折糧五萬石,起解梧州廣備倉,以備行糧之用,度東資于廣西甚侈”,因此提議從班軍中“摘留二千名,赴督府輸班,其余發回衛所,糧米扣留三萬五千石,以濟廣東軍餉之用”。時任兩廣總督張瀚等人反駁道:廣東官軍戍守悟州,非守梧州也,所以守廣東之藩籬……守廣西而后廣東可固,守藩籬而后門庭可安。其勢真有不可已者。不然廣西猺獞千穴,土狼萬族,山深箐密,境壤相錯,設無梧州重鎮控扼之,朝發巢而暮踐郊矣!恐不止海寇之縱橫已也。廣東雖欲晏然,可得乎?此為廣東計,亦有不得不然者。[25]張瀚的奏章送達朝廷后即離任,繼任總督李遷考慮到“梧州地方雖屬廣西,實兩廣要害,故設立軍門”,而“廣東師旅繁興,奏議撤兵減糧,殊非得已”,因此提出折衷辦法,“請令戍兵如舊,其倉糧暫以三萬石解梧州,余二萬石留廣東,俟二年以后,仍復原數”,此議為朝廷采納[26]1427-1428。萬歷十五年(1587),免戍之議再起,時任總督吳文華復稱,“兩廣相為唇齒,梧郡實為咽喉”,“東省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軍虛弱,不得不籍東軍,還以仍舊為便”[4]696。及至明末,班軍俱“奉督院牌拔”,多寡不一,已無常額,“大略半守梧鎮,半守江道”[4]699。萬歷年間,除班軍外,目兵同樣被裁減。萬歷十七年(1589),總督劉繼文“題減一千名”,萬歷三十二年(1604),總督戴燿“題減一千名”,萬歷四十五年(1617),左江道“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方”,萬歷四十八年(1620),總督許弘綱“議全撤,尋復議調”[4]689。
隆慶、萬歷年間裁撤班軍、目兵之議,固然與兩廣地方官員的權力博弈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兩廣秩序的安定以及梧州軍事地位的下降,班軍、目兵等戍衛部隊已無往昔的重要作用,只是徒耗軍餉、徒勞無功。萬歷末年,同知陳煕韶即評論道:目兵以文成始,班軍以襄毅始,當年作法慮自深,長年來習于承平,遂成枝駢……班軍在國初其用足恃,沿至今日,市人等耳,其才不足于超距,其伍無禆于干城,計月而來,更番而去,徒縻官錢數萬,茍欲簡而練之,何似以官錢募市人,猶省往還之仆仆也。余謂班軍則去之便然,要折沖樽俎,安危有備,毋徒紙上陳言,積弊日深,捉襟見肘,此其時也歟。[4]701-702崇禎《梧州府志》的作者謝君惠亦稱:猺峝叛服無常,然其蠢動,必有奸人為響導焉,今咸就則壤矣。而七山、五屯、北科等營猶陳兵以戍,月費餉不貲,而半以虛伍冒也,一旦有急,保其不目逆送盜耶!汰冗為精,轉弱為強,可以固圉,可以省餉,斯籌國一便畫焉,斯今日之亟圖也![4]128此外,明后期梧州衛所旗軍的情況亦不樂觀,萬歷年間總督吳文華即已注意到“梧州所軍虛弱”的現象。崇禎《梧州府志》亦記載:梧州所原額一千五百七十四名,崇禎四年一百八十四名。
五屯所原額八百六十四名,萬歷間六百五十一名,今見在六百三十四名。
容縣所原額一千二百六十三名,萬歷間一百五十八名,今見在一百三十八名。
懷集所原額一千三百四十名,萬歷間二百五十二名,今見在二百五十四名。
郁林所原額一千二百六十五名,萬歷間一百零二名,今見在八十七名。[4]667-668可見,萬歷年間梧州衛所旗軍的額數已較原額大為減少,且存在大量兵士逃亡的情況。
2.梧州地區的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
嘉靖中后期開始,隨著大藤峽及府江流域的動亂逐漸平息,梧州行政事務的重心由地方秩序控制轉向社會經濟發展。明代兩廣食鹽貿易興盛,以官營為主,梧州是廣西食鹽囤積之地,廣東鹽商先將鹽溯西江運送梧州,然后散銷各地,因此鹽稅是梧州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27]。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將原本行銷廣鹽的湖廣衡州、永州等地改行準鹽。為確保梧州的財政收入,嘉靖四十四年(1565)兩廣總督吳桂芳上疏朝廷,請將湖廣衡、永二府復行廣鹽,“庶軍民便于得鹽,商賈利于通濟,而兩廣軍餉亦賴之裨益”[28]。萬歷二年(1574),應兩廣總督殷正茂所請,“梧州府添設副提舉二員,照例請給關防常輪一員,前往廣東買鹽運回梧州,候桂林船到轉發,仍于桂林、梧州二府原設管糧通判,令其兼理鹽法”[22]782。
梧州地區氣候炎熱,加之百姓習慣結竹為居,因此火災頻仍。然而嘉靖以前地方官員忙于軍政事務,火災問題并未得到足夠重視。嘉靖中后期,隨著梧州城軍事地位的弱化,社會經濟發展成為施政重心,火災問題逐步得到解決[29]。嘉靖二十四年(1545)“梧城大火,二十五年又火,二十六年知府翁世經修火墻甃街道”。嘉靖四十四年(1565),“梧城外大火”,次年夏六月“又大火,民舍幾盡”。總督吳桂芳等“合議添補火墻三道,共十三道,令通衢盡易陶瓦”[13]卷24。萬歷年間,地方官員開始重視倉儲的建設。懷集縣倉儲得到大力整修,萬歷十年(1582),知縣林春茂,創設義倉,次年新建預備倉二間,萬歷四十七年(1619),知縣謝君惠重修預備倉“廳三間,東西厫四間,又添建一間”[30]卷2。萬歷末年,容縣知縣區龍禎建常平倉二十七間[3]卷10。萬歷四十八年(1620),梧州知府陳鑒“于闔屬州縣各發銀平糴谷五百石,貯預備倉,以備賑濟”[30]卷2。
同時,嘉靖末年至萬歷年間,明廷開始加強府江、西江水陸交通的疏治,為梧州地區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容江“當梧郡西南孔道”,“諸灘舟行甚險,猺賊藏匿林菁”,“鉤劫無已”,嘉靖三十九年(1560),兵巡僉事章熙“親詣各洲,刊木掘根”,疏浚河道,“賊遂遠遁,往來民商賴之”[13]卷24。萬歷十六年(1588)“從兩廣督臣吳善請”,“改平、梧二府清軍同知各加江防職銜,府門等五驛為水馬驛。”[22]3702萬歷二十二年(1594),“從撫按陳大科、涂宗濬請”,“開府江,桂林、蒼梧水陸險阻,斬木劃石,決淤疏湍,俾猺夷不得出沒叢薄,江流無沖激之患。”[22]5170蘇濬針對萬歷年間梧州地區的社會治理說道:“今上神武震于遐方,于是辟榛涂為周行,變丑夷為編戶,管壘基置,材官星列,而梧人始獲安枕以嬉。”[21]《明史》亦稱:“自數經大征后,刊山通道,展為周行,而又增置樓船,繕修校壘,居民行旅皆帖席,猺獞亦骎骎馴習于文治云。”[31]
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水陸交通的暢達,使梧州逐漸向商業城鎮發展,及至明末,梧州城已有不少外省商人,且多為富商,崇禎《梧州府志》載:“客民閩楚江浙俱有,惟東省接壤尤眾,專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歸。中之人家,數十金之產,無不立折而盡……鹽商、木客、列肆、當壚,多新(會)、順(德)、南海人。”[4]133綜上分析,明代后期,隨著地方秩序的日益穩定,梧州社會開始轉型,原有軍事地位逐漸下降,而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得到重視,逐漸由“軍事重鎮”向“商業重鎮”過渡。
三、清前中期梧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清初,南明抗清戰爭與“三藩之亂”使廣西再次陷入動亂,梧州因地理位置重要,成為各方勢力反復爭奪的焦點。至“三藩之亂”平定,廣西社會秩序基本穩定。但明清易代之際,梧州大量衛所軍戶借戰亂之機,躲入兩廣交界的山區,以此逃避賦役,并時常引發地方動亂[32]。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皇帝即指出:“猺人所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向來持此險僻,頑梗不馴。近復突出搶奪村民,殺害官兵。”[33]卷207因此清前期,地方官員仍需動用軍事力量將這些“化外之民”重新納入國家權力體系。雍正年間,孔毓珣、金鉷等地方大員大舉征剿“猺獞”,使梧州山區得到有力控制。乾隆《梧州府志》將《猺獞》附于《戶賦》之后,并稱:“猺人、獞人盡服疇食德之民矣,用并附載。”[13]卷首作者還在《猺獞》結尾感嘆道:自是(雍正年間大征后),諸猺、獞莫不翕然怗服,革面洗心,土田盡隸版圖,耕織無殊編戶,愚者荷鋤耒,秀者業詩書,泮宮芹藻之間,彬彬稱弟子矣。遍歷四境,衣服、室廬、飲食、禮節,其人俱同一色,為蠻為民無非族類,一道同風,于斯為盛,猗歟休哉!載筆至此,而不禁欷感嘆于王化之及人者,深且遠也![13]卷8也正是隨著地方秩序的日益穩定,梧州地區逐步開始了大規模經濟開發。梧州地區“俗尚簡樸,務本者多,逐末者少”[13]卷3,且氣候多變,溫熱多雨,適宜農業生產,加之百姓充分利用水資源,“甃磚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筧,樹柵畚土以潴之曰陂”[13]卷8,“凡近溪澗之區,可設陂車以資灌溉者,不可勝紀”[23]卷1,為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考慮到廣西地處邊疆,“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清廷亦對廣西百姓予以特殊恩惠,將“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次第蠲豁”[33]卷160,使戰亂后的廣西社會得以盡快復蘇。乾隆《梧州府志》稱:“梧界高山,大川平原叢薄,間或數十里無煙戶,地本曠也。近自久濡圣澤以來,井廬日增,生殖滋廣……其鄉一望,村墟熙皞成象。”[13]卷2乾隆《北流縣志》亦“按”:“自康熙二年以來,生齒日蕃,恭遇圣明,愛養蒼生,諄切勸墾,民皆踴躍開荒,昔為棄土,今則大半熟田矣。”[34]卷1反映出在清王朝的帶動下,梧州地區的鄉村和農業得到大力發展。
米糧是梧州地區的重要農產品,尤其是蒼梧縣,素為魚米之鄉,所屬南五鄉、東六鄉,連城廂,共十二鄉,物產豐富,尤其以谷米為最[35]40。加之清代廣東嚴重缺糧,而梧州地處西江要道,與之界鄰,成為供應廣東谷米的主要地區[36]。蒼梧戎圩每日有六七十萬斤谷米銷往廣東佛山等地,“糶不盡戎圩谷,斬不盡長洲竹”的俗語在乾隆時期廣為流傳[35]39-40。也正因如此,清代梧州地方官員尤為重視倉儲問題,較之崇禎《梧州府志》,乾隆《梧州府志》新增《積貯》條目,并引言道:“民為邦本,食為民天,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在邊土為尤要。兩粵地相唇齒,東人之粟仰給于西,梧州則又比鄰之挹注也。故常平、義倉、社倉而外,兼設備東一款。處漏巵之勢,而謀備豫之藏,倉儲重攸繁矣。”[13]卷9
明末至清中期,隨著東南省區人地矛盾日益激化,大量外省移民向廣西遷徙,梧州即是移民較為集中的地區[37]。移民的大量遷入,推動了梧州地區的山林開發和經濟作物的種植。岑溪縣,大峝山顛種植茶葉,“葉粗味厚,故有峝茶之名”,漆山“各鄉有之,干者入藥”。[13]卷3藤縣土人“沿江種甘蔗,冬初壓汁作糖,以凈器貯之”[38]卷5。容縣物產尤為豐富,花生“去殼榨油,品在茶油、菜油之上”,苧麻“取皮如筋者,可績布控線”,芝麻分黑白二種,“取油以白者為勝,服食以黑者為良”[3]卷5。木材成為梧州地區的重要物產,多用于筑室制器。藤縣朔木、杉木、茶木各鄉廣植繁盛,“人稠用閣,起造多資于此焉”[38]卷5。容縣,杉木“紋細條直”,“南人屋棟、船材及一切器物皆取資焉”,樟木“紋細質堅,可雕刻花鳥、造船、作聯扁”[3]卷5。許多經濟作物的種植呈現商品化趨勢,推動了梧州商品經濟的發展。藤縣藍靛“多在山種之,其利甚溥”[38]卷5。乾隆年間,岑溪“各鄉近山處皆植”茶葉,“謝孟堡山場所植尤伙,遠近販鬻,民資以為利”[13]卷3。容縣“土人挖甜竹、大頭竹之嫩者,曬干為筍脯,販賣出境”,黃楊木亦可“販賣出境,頗食其利”,沙田柚“秋后金丸滿樹,獲利頗厚”,鐵力木“為南方美材”,“廣州人多采之制幾案等器”[3]卷5。容縣外來移民以竹造紙,“火紙以丹竹為之,福紙以蒲竹為之”,“康熙間,閩潮來容,始創紙篷于山中”,乾隆年間“有篷百余間,工匠動以千計。”[13]卷3“郁林土產除五谷外,以藍取靛、花生取油、甘蔗取糖三者為大宗,歲得厚利,茶次之”。郁林藍靛“與北、陸、興三縣靛,俱從北流江販運廣東,蘇杭人通謂為‘北流靛’”,郁林所產茶葉,因“土人不善制之”,故“有遠商來收買,焙碾好,始運去”[39]卷4。
自明代開始,梧州即為兩廣食鹽貿易的轉運樞紐,清代中期這一地位繼續保持并得到強化。乾隆年間,兩廣總督鄂彌達奏稱:廣西梧州為通省運鹽總匯,鹽道駐扎桂林,相距既遠,又因責任較繁,未能離省,一切轉運鹽包、給發水腳、稽查夾帶,向俱委梧州府同知代辦。然究非專管鹽政之員,請照廣東潮嘉汀贛分司之例,即于梧州府添設鹽運分司一員,鑄給關防,催征餉稅,以專責成,仍歸驛鹽蒼梧道管轄。[40]卷30正是考慮到梧州之于廣西食鹽運銷的重要地位,地方大員奏請在梧州添設鹽務官員,“以專責成”。梧州府蒼梧、懷集等縣有多處礦山,但清前期廣西嚴行礦禁,一直未得到開發[41]。例如,蒼梧縣之芋莢山“界連懷集、賀二縣,并廣東肇慶府之開建、封川等處,山路險峻,出產礦砂”[42],雍正四年(1726),即有廣東饑民同廣西本地百姓潛往偷挖,地方官員擔心其“蟻聚無常,貽害地方”,因此“嚴拿驅逐”[43]。雍正六年(1728),廣西巡撫金鉷奏稱:粵西一省,田少山多,其山可以布種者,雜糧竹木,罔不隨地之宜以盡利。乃有一等不毛之山,頑石犖確,綿亙數十百里,既已農力之難施,復苦材產之有限,獨其下出有礦砂,分金、銀、銅、鐵、鉛、錫數種,實為天地自然之利,不盡之載。[44]同時,為了保證地方秩序的安定,“止用本地窮民刨挖、挑運”,“概不用外省流民”[44]。在金鉷的極力奏請下,廣西礦禁解除,除梧州蒼梧縣芋莢山“地形四達,其砂產金”,“獨宜官辦”,“其余府州,凡有礦山者,俱令商人承辦”[45]565-566。雍正、乾隆年間,梧州多所礦山由官府招募商人開采,并抽課收稅。懷集縣將軍山“銀、鉛、銅并產,商人韓茂亨于雍正七年承認開采”,“照例抽收稅課”[45]291。乾隆二年(1737),商人黃丹山“承認試采懷集縣屬銀、鉛并產之荔枝山礦廠”,獲準開采,并由知縣“就近督察煎煉,照例抽課具報”[45]366。同年,商人金在中承認開采“蒼梧縣之金盤嶺金礦,抽收稅課”[45]566。清代廣西開發的礦產大多作為原料運至廣東貿易,以滿足廣東手工業生產的需求[27]。
隨著商品經濟日益繁榮,梧州地區的墟市數量迅速增長。至清中期,梧州及其周邊地區形成了以蒼梧戎圩為中心的商業貿易網絡。戎圩是廣西最為繁榮的商業圩鎮,有“一戎二烏三江口”之稱,高州、信宜、羅定、雷州、欽州、玉林、容縣、陸川、博白、平南等地商人均到此經商[35]39。乾隆年間的《粵東會館甲申年創造壩頭碑記》稱:(戎墟)袤延十里,煙火萬家,西通潯貴、南寧,東接肇、高諸郡,故西粵一大都會也。富庶繁華,貿易輻輳,幾與粵東之佛山等,故俗號□佛山。凡舟車之絡繹往還,皆泊于此。[46]69外省商人會在梧州的繁華市鎮修建會館,“以貯百物,以敦梓誼”[46]69。蒼梧戎圩“居貨之商以粵東人為最盛”,康熙五十三年(1714),粵東商人捐資將本地關夫子祠更為會館,“歲時習禮其中,展恭敬之情,序鄉鄰之誼”。其后會館又于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五十三年(1788)、嘉慶四年(1790)三次重修。乾隆五十三年(1788)戎圩《重建粵東會館碑記》稱:“吾東人貨于是者,禪鎮揚帆,往返才數旦。蓋雖客省,東人視之,不啻桑梓矣。”[46]71體現出粵東商人的本地化及其對梧州的地域認同。梧州地區河流眾多,且氣候多變、地形復雜,因此水旱災害頻仍,對商賈經營造成嚴重影響[47]。外省商人多會修建祠廟,祈求神靈消災賜福,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當屬龍母信仰。至乾隆時期,梧州地區已有多處龍母廟,府城附近即有兩處,“一在城西北二里許桂江上”,“一在西南十里長洲尾”,“俱濱江商民虔祀,祈禱輒應”[13]卷7。雍正八年(1730),本地商民“共發誠心,樂為捐助”,對城北龍母廟“重為修葺”,知府甘湛泉親自撰文加以紀念,并稱贊龍母“凡有所求,靡不響應”,對其安定民心的作用予以肯定[13]卷21。
至18世紀,梧州已成為嶺南商業重鎮,“市中貨物盛于他邑,鄰封日用所需,皆取資焉”[48]卷32。雍正年間,廣西巡撫李紱即稱:“桂為省會,梧為通衢,皆商賈湊集”[49]。梧州知府甘湛泉亦稱:“梧為西粵要衢,襟連三江,冠蓋絡繹,行商坐賈往來不絕,亦一大都會也。”[13]卷21廣西巡撫陳輝祖在乾隆《梧州府志》序言寫道:“梧州粵西一大都會也,居五嶺之中,開八桂之戶,三江襟帶,眾水灣環,百粵咽喉,通衢四達,間氣凝結,人物繁興,形勝實甲于他郡。”[13]序
清代以前,梧州地區的民風尤為淳樸,崇禎《梧州府志》稱本地百姓“惟知力穡,罔事藝作”[4]131。雍正《廣西通志》亦載,梧州“民之近山者樵,近水者漁,有陂池山澤之樂,鮮商賈經營之事,故俗頗淳古,而家少蓋藏”[48]卷32。受外省移民的影響,梧州社會風氣開始轉變。府城附近“商賈輳集,類多東粵人,里民為其漸染,行事漸尚紛華”,“雖僻遠鄉落,久知以陋習為恥,彬彬日變矣”。[48]卷32梧州地區的語言也受到移民的影響,城郭街市“亦多東語”,乾隆《梧州府志》特意將本地方言與粵東音進行對比,可見粵東音已成為梧州主要語言之一[13]卷3。隨著城鎮不斷發展,經濟日益繁榮,民風漸趨奢華,社會教化問題也顯得尤為重要。乾隆《梧州府志》之《風俗》結語道:志稱里人質直好信,士大夫貴節尚氣,坊廂之間彬彬稱首善焉。奈何風之所移,君子積愒成廢,小人積惰成窳。迄今,淳樸之氣未散,而鴻鉅之光亦未融,俚僿之習未開,而黠猾之風已漸長。夫移風易俗,存乎其人,則所以主持其風會,而齊一其教化者,士大夫之責歟,抑循良者之善治也,將于今日有厚望焉。[13]卷3這段按語不僅道出了梧州社會風氣的變化,同時反映出地方官紳已對此深有感觸,對“君子積愒成廢”“小人積惰成窳”“黠猾之風漸長”等現象表示不滿,并希望后世官員善加教化。
四、結語
15-18世紀,梧州經歷了從“軍事重鎮”到“商業重鎮”的社會變遷。正統年間,日益嚴重的地方動亂開啟了梧州地區的軍事化進程,地方官員大力整修城池,明廷大量增設巡檢司,并不斷征調班軍狼兵等軍事力量進入梧州屯戍駐守。景泰、天順年間,大藤峽“猺亂”愈演愈烈,且波及廣東,為了統一事權、協調資源,明廷遂設兩廣總督總領軍務,并于成化六年(1470)開府梧州。其后,在韓雍、王守仁等人的提議下,廣東班軍、桂西目兵(狼兵)戍守梧州成為定制,梧州地區的軍政建設亦得到逐步加強。至嘉靖年間,梧州成為嶺南軍事重鎮。嘉靖中后期至萬歷時期是梧州地域社會變遷的關鍵節點,隨著兩廣秩序日益穩定、大量化外之民被納入版圖,梧州社會隨之轉型,原有軍事地位逐漸下降,而財政、火政、倉儲、交通等社會經濟問題開始受到重視,由軍事重鎮向商業重鎮過渡。明清易代之際,梧州作為軍事要地,成為各方政權爭奪的焦點,至“三藩之亂”平定后,地方秩序基本穩定,雍正年間的大征使兩廣交界的山區亦得到有力控制。明末清初,外省移民大量遷入梧州,推動了山林地區的開發,經濟作物得到大力種植,并走向商品化生產,米糧、食鹽等傳統貿易亦保持興盛。雍正中期,清廷解除礦禁,招商開采,以盡地利。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梧州地區的墟市數量迅速增長,并形成了以蒼梧戎圩為中心的商業貿易網絡。外省商人,尤其是粵東商人,在本地悉心經營,積極修建會館、神廟,呈現本地化趨勢。及至清代中期,梧州已由軍事重鎮轉型為商業重鎮,社會風氣亦由淳樸漸趨奢華。梧州的個案表明,邊疆重鎮的形成和發展與區域秩序控制、國家權力滲透、山區經濟開發等因素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1]明英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2]明英宗.勅總兵等官撫安桂平等處地方[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3]易紹德.(光緒)容縣志[M].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4]謝君惠.(崇禎)梧州府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3.
[5]楊景秀.博弈與平衡:明代兩廣總督的權力運作[D].廣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3.
[6]趙克生.經略西江[J].中國史研究,2014(3):23-28.
[7]葉盛.地方事疏[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112.
[8]明憲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9]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2015:571-575.
[10]韓雍.斷藤峽疏[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113-114.
[11]應槚,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70:15-16.
[12]吳宏岐,韓虎泰.明代兩廣總督府址變遷考[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3):50-61.
[13]吳九齡.(乾隆)梧州府志[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4]明世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15]林富,黃佐.(嘉靖)廣西通志[M].明嘉靖十年刻本.
[16]楊芳,編纂,范宏貴,點校.殿粵要纂[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240.
[17]林大春.肇造全鎮民居碑[M]//汪森.粵西文載:第三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289.
[18]王守仁.奏覆田州思恩平復疏[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143.
[19]張瀚撰,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5:164.
[20]蔣冕.府江三城記[M]//汪森.粵西文載:第二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191.
[21]蘇濬.兩廣郡縣志[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276-277.
[22]明神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23]何夢瑤.(乾隆)岑溪縣志[M].清乾隆九年刻本.
[24]任建敏.萬歷本《蒼梧總督軍門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論明代兩廣總督地位的變遷與成書因由[J].文史,2021(1):187-205.
[25]張瀚.議復梧鎮班軍疏[M]//汪森.粵西文載:第一冊.黃盛陸,校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206-207.
[26]明穆宗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27]黃啟臣.明清時期兩廣的商業貿易[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4):31-38.
[28]吳桂芳.議復衡永行鹽地方疏[M]//應槚,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70:282.
[29]麥思杰.“以火為政”:明清時期梧州城火政與區域社會的變遷[J].社會,2018(1):81-103.
[30]顧旭明.(乾隆)懷集縣志[M].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31]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8216.
[32]趙世瑜.“不清不明”與“無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區域社會史解釋[J].學術月刊,2010(7):130-140.
[33]清圣祖實錄[M]//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34]張允觀.(乾隆)北流縣志[M].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35]饒任坤,陳仁華.太平天國在廣西調查資料全編[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36]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史,2020:38-42.
[37]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06-407.
[38]邊其晉.(同治)藤縣志[M].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39]馮德材.(光緒)郁林州志[M].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40]清高宗實錄[M]//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41]鄧智成.清代廣西礦產開發研究[D].云南大學碩士論文,2018.
[42]署廣東總督阿克敦奏報拏獲偷挖礦砂渠魁李亞展等情形折[M]//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九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0:308.
[43]廣西巡撫汪漋奏拿獲狂徒情形折[M]//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七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0:465.
[44]廣西巡撫郭(金)鉷奏陳開采地方礦砂管見折[M]//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十三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0:252.
[45]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等編.清代的礦業[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6]唐凌,熊昌錕.廣西商業會館系統碑刻資料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47]秦浩翔.明清時期廣西梧州地區水旱災害及其社會應對[J].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19(6):81-86.
[48]金鉷.(雍正)廣西通志[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9]廣西巡撫李紱奏請九府分貯捐谷等事折[M]//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三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0:364.
(責任編輯:王勤美)
Order Contro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Wuzhou,Guangxi Province from 15th to 18th Century
QIN Haox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China,510257)
Abstract: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18th century,Wuzhou experienced a social change from “military stronghold” to “business hub”.During Zhengtong period,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turbulence caused by Yao ethnic group in Datengxia area,the militarization process got started in Wuzhou.During Jingtai and Tianshun period,as the turmoil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e,in the sixth year of Chenghua period,in order to unify authority and coordinate resources,Guangdong and Guangxi governor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office in Wuzhou.Since then,Wuzhou’s military construction continued to be strengthened,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military area of Lingnan region.In the late Ming Dynasty,with the gradual stability of the local order,the military status of Wuzhou was declining day by day,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me important,thus Wuzhou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a business hub.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as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Wuzhou was vigorously developed and traditional trade like grain and salt remained prosperous,a commercial trade network centered on Cangwu Rongxu was gradually formed.By the 18th century,Wuzhou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business area with a luxurious social atmosphere.The Wuzhou case show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border area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order control,infiltr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Key words:important border area; nat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social change
收稿日期:2022-02-15
基金項目:201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地方志纂修與國家認同、區域社會文化創造研究”(18AZS012)。
作者簡介:秦浩翔,男,廣西桂林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①主要包括:覃延歡:《廣西四大城市在明清時期的發展(上)》,《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侯宣杰:《西南邊疆城市發展的區域研究——以清代廣西城市為中心》,四川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吳宏岐、韓虎泰:《明代兩廣總督府址變遷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3期;吳慶洲:《“水都”的變遷——梧州城史及其適洪方式》,《建筑遺產》2017年第3期;麥思杰:《“以火為政”:明清時期梧州城火政與區域社會的變遷》,《社會》2018年第1期;孫將來:《梧州城市空間形態及其演變研究(漢-民國)》,廣西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何俊宇:《明代梧州府軍事地理研究》,《廣西地方志》2020年第3期,等等。
②本文所指梧州地區以明代行政區劃為準,包括梧州府城及其所屬蒼梧縣、容縣、岑溪縣、藤縣、懷集縣、北流縣、博白縣、興業縣、陸川縣、郁林州。
③“猺”“獞”等稱呼包含歧視貶低之意,本文在行文論述時分別改為“瑤”“僮”,但在引用史料時為保留其原義,不做改動。而“狼”并非全為貶義,包含稱贊狼兵驍勇善戰之意,因此文中“狼”字一律不做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