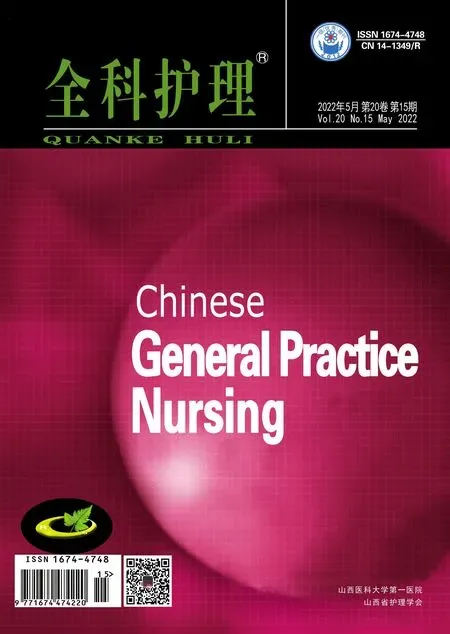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的干預在腦癱患兒家屬負性情緒管理中的實踐研究
崔茹潔,張雯雯,丁燕曙,殷 茵
腦癱又稱腦性癱瘓,是指患兒在腦發育不成熟階段受到非進行性腦損傷,造成中樞神經系統病變和神經肌肉控制力喪失,而引起的生理與運動發育持續性障礙綜合征。以感知覺障礙、智力和語言障礙為核心表現,部分伴有四肢痙攣型癱瘓以及其他繼發性肌肉骨骼問題,為當前造成兒童殘疾的主要疾病[1]。臨床針對該癥主要以康復治療為主,因其具有治療周期長、療效慢、治療費用高等特點,給其家庭與主要照護者帶來巨大經濟與心理負擔。研究表明,腦癱患兒家屬在長期照護壓力、經濟負擔以及社會性影響因素介導下,過度焦慮、易怒、抑郁等負性情緒發生率高達68%,并嚴重降低其照護信心與能力,影響患兒整體康復和預后[2]。因此,關注腦癱患兒家屬心理體驗與壓力負荷,利用外源性干預措施促進個體進行心理調適,提升其照護能力與身心健康狀況尤為重要。Gross情緒管理理論是以重視個體負性情緒現狀、來源為基礎的心理干預理論,其認為情緒調節是個體對情緒現狀、情緒相關的行為及情緒誘發情境進行監控、評估、修正的動態調整過程,通過重視情緒發生過程的控制點實施相應調節方式,可提高情緒管理成效[3]。大量臨床證實,該理論在學生情緒調節、慢性疾病病人心理調節及提升癌癥病人心理彈性與康復信念中均取得良好效果,但在兒童護理領域研究較少[4]。為此,本研究將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干預應用于腦癱患兒家長負性情緒管理中,效果顯著。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20年1月—2021年6月收治的84例腦癱患兒及其家屬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對照組、觀察組各42例。對照組患兒:男26例,女16例;年齡2~7(3.58±0.34)歲;腦癱程度:輕度14例,中度19例,重度9例。觀察組患兒男24例,女18例;年齡2~7(3.63±0.42)歲;腦癱程度:輕度16例,中度16例,重度10例。對照組家屬:男13人,女29人;年齡20~45(35.46±1.46)歲;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4人,專科及以上28人。觀察組家屬:男15人,女27人;年齡20~45(36.84±1.18)歲;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6人,專科及以上26人。兩組患兒及家屬基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腦癱患兒:符合腦癱診斷標準[5];年齡>1歲;無任何出血傾向;無其他遺傳代謝性疾病。患兒家屬:年齡≥18歲;為患兒主要照護者;溝通與認知能力正常;對本研究知情且自愿參與。
1.3 排除標準 腦癱患兒:有嚴重營養不良者;伴有嚴重肝腎損害等并發癥者;合并其他腦部病變性疾病者;臨床資料不全者。患兒家屬:既往有精神疾病史者;合并心腦血管或惡性腫瘤者。
1.4 干預方法 對照組實施常規心理護理,包含通過口頭宣教或發放健康手冊等方式為家屬進行疾病健康宣教,定期實施心理咨詢與疏導、給予家屬信息與技能支持,普及家屬患兒病情現狀、預后和相關護理內容,幫助家屬掌握疾病發展過程,告知患兒生活管理知識與并發癥預防知識。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實施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的干預(見圖1),具體如下。

圖1 Gross情緒管理框架
1.4.1 明確家屬情緒現狀表達(what) 入院時以家屬文化程度、年齡、家庭背景、職業類型等作為信息收集重點,采用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6]和貝克焦慮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7]調查家屬當前焦慮、抑郁評分現狀,并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掌握病人心理健康以及患兒照護期間情緒困擾,結果顯示家屬焦慮、抑郁評分均處于較高水平,且悲傷、自卑、回避、失望及絕望、疲乏等為其照護期間主要負性情緒。
1.4.2 究其情緒來源(why) 對測評結果進行綜合性歸納和分析,利用根因分析法究其原因,并結合奧馬哈問題系統中護理問題評估體系,明確家屬心理情緒來源,該體系從認知、行為狀況、心理社會3個方面評分,如表1所示。

表1 負性情緒來源分析
1.4.3 Gross情緒管理(how) 由主治醫生1人、護士長1人、護士2人以及康復治療師1人共同成立護理小組,明確組內成員工作職責,并對成員進行專業培訓及考核,內容包括腦性癱瘓類型與專科知識、Gross情緒管理臨床應用、發展和意義;方案實施流程與注意事項、資料收集方法、問卷使用方法等。最后經小組成員查閱文獻、咨詢專家、案例分析后,共同制訂Gross情緒管理方案,見表2。

表2 Gross情緒管理內容
1.4.3.1 動機性訪談 將家屬按照4~10人制分成小組,通過組內動機性交談、匿名形式書寫紙條等方式引導病人表達當前情緒以及主要原因,針對家屬心理壓力來源與主要影響事件進行統計,結果發現家屬非理性信念(見表3)為其主要原因,以此作為后續調整策略制定依據。

表3 非理性信念統計
1.4.3.2 同伴介入干預 邀請既往腦癱患兒且康復良好、心理狀態穩定的家屬,互相分享患兒康復期間照護經驗。內容包含:講述個人身心健康觀,健康認知獲取方法、心理調節方法及健康行為轉變等經驗,并傳播積極生活態度,為家屬普及良好心態與情緒患兒及病情康復的重要性,樹立其照護信心。培養自身興趣愛好和與他人的社會團體活動,如繪畫、聽音樂、讀報、下棋、戶外團建、舞蹈、唱歌等,引導病人表達自身情感、宣泄情緒、訴說疑難,釋放壓力,增強自我認同感和社會適應能力。
1.4.3.3 正念減壓療法 ①正念冥想[8]:使用輕松舒緩音樂配合緩慢規律的呼吸完成眼部與臉部肌肉的緊繃與放松,隨后引導其想象自己在一片花園里、草地上或大海邊,發揮想象去冥想那些場景中的人物、景色與物品,促使其達到身心合一,注意力集中的狀態。②肌肉放松法[9]:頭部放松,即雙眼緊閉、眉頭緊皺,鼻子、臉頰緊繃,用力鼓腮保持5 s后放松;上肢放松,即雙手緊握拳頭使左右前臂緊繃,隨后將雙臂伸直并同時握拳維持7 s后放松;軀干放松,即分別完成雙肩聳起、挺胸、背部拱起、屏住呼吸等動作,各維持5 s后放松;下肢放松,即將左右腿向前用力蹬墻維持7 s后放松。
1.4.3.4 多形式信息支持 通過播放視頻影像資料、一對一交流等形式進行疾病知識宣教,講解腦性癱瘓相關知識、治療方式、康復期間常見問題與應對策略、預后的影響因素、自身情緒對患兒以及疾病造成的影響等。通過自制康復指導手冊與建立微信康復群為家屬提供持續且專業的照護技能支持,康復指導手冊內容涉及疾病知識、常見癥狀、用藥知識、圖文并茂的康復訓練知識(項目、內容、方法、建議頻率和康復時間)、日常飲食注意、生活注意事項、科室電話等。微信康復群由康復治療師為群主,護士為管理員,完成院內外心理評估與疏導、知識與技能解答與指導的全方位醫療支持。
1.5 觀察指標
1.5.1 應對方式 干預前后采用父母應對方式量表(Coping Health Inventory for Parents,CHIP)[10]評估兩組患兒家屬應對方式,該表共45個條目,由保持家庭團結、合作與樂觀態度,尋求社會支持、維護自尊和心理穩定,積極向醫護人員或其他父母了解疾病3個分量表組成,采用1~5分計分法,總分225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屬應對方式越好。該量表可信度0.93,Cronbach′s α系數為0.9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5.2 心理負擔 干預前后選取Zarit照顧者負擔量表(ZBI)[11]評估兩組患兒家屬心理負擔,該量表共22個條目,采用1~5分計分法,總分110分,得分越低表明家屬心理負擔越輕。該量表可信度0.88,Cronbach′s α系數為0.9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5.3 照護能力 干預前后采用照護者照護能力問卷(FCTI)[12]評估兩組患兒家屬照護能力,問卷包含尋求疾病信息、協助進食或服藥、與病人溝通、提供良好環境、滿足日常需求5個維度,共25個條目,采用0~2分計分法,總分0~50分,分數越低表明照護者能力越高。該量表可信度0.87,Cronbach′sα系數為0.89,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結果

表4 兩組患兒家屬應對方式比較 單位:分

表5 兩組患兒家屬心理負擔評分比較 單位:分

表6 兩組患兒家屬照護能力評分比較 單位:分
3 討論
3.1 Gross情緒管理理論臨床應用優勢 腦性癱瘓屬慢性中樞性神經系統功能障礙綜合征,由于其病癥復雜且難以治愈性特點,多數患兒治療效果欠佳,社會生活能力較差且預后不良,已成為導致兒童致殘的主要疾病,給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13]。父母作為腦癱患兒的直接照顧者,其身心健康直接影響患兒照顧質量與康復效果。相關研究表明,焦慮、抑郁為腦癱患兒家屬最常見的負性情緒體驗,主要體現在擔心孩子無法得到治愈、害怕因為疾病影響孩子后續生活、害怕自己無法給孩子專業和正確的照顧、恐懼疾病導致的致殘現象等方面[14]。負性情緒過度將誘發其持續關注、無助等消極應對行為,照護能力與信心下降及康復希望水平低下等心理行為問題,影響患兒整體康復。Gross情緒管理理論是由詹姆斯·格羅斯等學者提出的情緒管理模型,其核心內容為在客觀認知情緒特征發生基礎上,有意識地發現和探索負性情緒來源,并建立科學、專業的情緒宣泄和控制機制,幫助去克服和消除負性情緒以及對個體的影響[15]。段衛芳[16]將該理論應用于艾滋病病人中,能有效提高艾滋病病人康復與治療信心,減輕其身心壓力,維持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
3.2 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干預在改善腦癱患兒家屬應對方式中的應用分析 應對是指個體為解決當前面臨緊張或壓迫環境下而做出的刻意性反應或行為,主要體現在個體為解決壓力來源或自我保護時所采取的習慣性處理方式(消極應對或積極應對)[17]。積極應對方式有利于促進個體對疾病的正確認識及管理,而消極應對方式則會加重其疾病恐懼感,增強生理、心理不適反應,進而加深個體心理創傷應激。本研究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干預后,結果顯示觀察組患兒家屬應對方式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其原因可能與該理論重視病人認知、情緒等方面的提升有關。梁蘭梅等[18]認為,個體認知、情緒和行為以及疾病帶來的心理創傷均為影響腦癱患兒家屬應對方式的關鍵。本研究通過依據情緒管理三部曲對家屬進行情緒現狀掌握、情緒來源分析、情緒正確干預等步驟的護理措施,并貫穿Gross情緒調整核心內容,分別制訂針對性情緒改善計劃。其中情景選擇能幫助家屬學會主動傾訴和表達,注意分配中能有效緩解家屬身心壓力和情緒,認知改變中能使病人糾正錯誤認知和非理性信念,重建疾病認知與照護信念。通過心理支持、轉移注意力與改善疾病認知等綜合性干預,進而促進家屬認知、情緒、行為等方面均得到顯著提升,有利于改善應對策略。
3.3 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干預在提高腦癱患兒家屬照護能力及改善負性情緒中的應用分析 照護者負擔是涵蓋生理負擔、心理負擔、社會負擔和經濟負擔等方面在內的身心/經濟壓力的體現,且與患兒病情程度、照護資源與照護能力密切相關。大部分家屬在疾病診治與居家管理中因缺乏持續專業知識與技能指導,導致照護能力低下而引起較為強烈的心理負擔,影響疾病居家康復與患兒居家生活質量[19]。本研究干預后結果顯示,觀察組患兒家屬照護能力評分低于對照組,觀察組患兒家屬心理負擔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該結果與程詩巍等[20]研究中結論相似,分析其原因可能與本研究同伴介入干預、正念減壓療法與多形式信息支持等內容的實施有關。其中同伴介入干預不僅能加強疾病理解,引導病人逐漸正視疾病,并提升其照護信心,還能引導同伴間互相傾訴與表達,促進負性情緒的宣泄。戚雯雯等[21]認為,正念減壓療法作為非藥物性心理治療方法,能有效培養病人情緒管理和調節能力,減輕壓力和緩解癥狀。本研究正念減壓療法中正念冥想、肌肉放松法的應用可提高其對當下事情的內在專注力與感知能力,幫助其獲取更多緩解心理情緒的有效策略,開闊和穩定家屬心境,增強家屬認知與自我行為的調節能力,達到情緒緩解的目的。多形式信息支持能幫助病人認知行為的構建,學習積極應對疾病的重要性,增強正性評價與有效應對的信念,主動學習和練習相關疾病康復知識及技能,進而提升其照護能力。
4 小結
情緒管理是個體對情緒發生、如何進行情緒體驗與表達,且施加影響的動態發展過程。本研究對腦癱患兒家屬應用基于Gross情緒管理理論干預后,有助于消除家屬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提高其處理應激情境的能力,增強其照護信心,幫助其建立良好照護態度和行為,進而提升其照護能力。但本研究屬單中心研究,且樣本量較少,未來仍需擴大樣本量,增加多中心臨床研究對該結論加以證實,為臨床重視患兒家屬心理健康,促進患兒康復質量提供更多的指導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