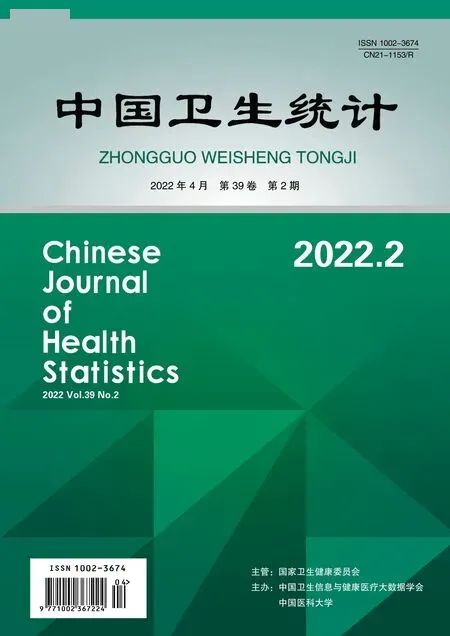沈陽市12~18歲青少年近視相關因素的探討及Nomogram預測模型的建立*
李 婷 王 梅 張東紅 李荔荔 黃彥紅△
【提 要】 目的 探討沈陽市12~18歲人群中導致近視的相關因素,并對影響因素進行預測評估。方法 對沈陽市4所中學的12~18歲青少年進行視力調查和近視相關影響因素的問卷調查。使用單因素和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將篩選出的影響因素建立12~18歲人群近視Nomogram預測模型。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1033名調查對象,近視率為56.15%,影響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父親不近視、母親不近視、從不吃甜食、無不良閱讀習慣、睡眠時間8~10h、正確的閱讀姿勢,是12~18歲近視發生的保護因素;父親近視≥300度(OR=2.352,95%CI:1.461~3.787)、母親近視≥600度(OR=4.732,95%CI:1.275~17.560)、不良閱讀習慣(OR=1.955,95%CI:1.432~2.699)是近視的危險因素。基于logistic回歸建立的Nomogram預測模型,Hosmer-Lemeshow test擬合優度檢驗P=0.027,ROC曲線分析風險總分的預測能力曲線下面積(AUC)為0.719(95%CI:0.688~0.750),采用Bootstrap內部驗證法驗證,校正后的AUC為0.695,說明該Nomogram模型的精準度和區分度尚可,但仍需大樣本高質量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修正模型。結論 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與12~18歲人群近視發生均相關,Nomogram預測模型有利于篩查近視相關因素及采取相應防治措施。
近視是一個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問題,也是當前學生健康的重點問題。據研究發達國家成人近視患病率從15%到49%不等[1],預計到2050年全球將有一半的人患近視[2]。根據2018年的調查發現,我國學生近視率達到53.6%[3]。近視除了影響視力和增加矯正費用外,也是眼部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4],增加青光眼、白內障、黃斑病變和視網膜病變等風險[5-7],給醫療和人群健康帶來挑戰。近視的成因機制目前還不完全清楚。本研究納入近視的相關資料,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近視發生的相關因素,在影響因素基礎上建立Nomogram預測模型并定量評價近視風險,為近視預防和治療提供依據。
對象和方法
1.研究對象
2018年5月在沈陽市抽取4所中學的1033名12~18歲中學生進行調查。其中,初中學生537人,高中學生496人;男生492人,女生541人。
2.研究方法
(1)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在沈陽市2所初中和2所高中隨機抽取10個班級,共計1033名12~18歲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自行設計眼健康狀況調查問卷)和視力檢查,調查12~18歲人群的近視相關影響因素和健康行為。
(2)視力檢查,使用5m標準對數視力表。檢查方法采用裸眼遠視力實測值,按照GB/T 11533-2011[8]和GB/T 26343-2010[9]的規定。
(3)屈光檢測,臺式自動電腦驗光儀進行檢測。每只眼測量3次,取平均值,如任意2次的球鏡度測量值相差≥0.50D,則進行額外的測量,再取平均值。
(4)近視標準:符合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即為近視:
①裸眼視力<1.0,電腦驗光等效球鏡度數≥-0.50D,其中≥-6.00D為高度近視,-6.00~-3.00D為中度近視,<-3.00~-0.50D為輕度近視;②佩戴角膜塑形鏡。
3.統計學分析
采用R studio(3.5.3)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logistic回歸方程篩選獨立危險因素,列線圖采用R rms程序包,建立Nomogram預測模型。應用caret程序包進行bootstrap法做內部驗證,rms程序包計算曲線下面積AUC。采用ROCR及rms程序包繪制ROC曲線。
結 果
1.近視組和非近視組人群的基本信息比較
本研究調査中學生共計1033名(2066眼),近視組580例(56.15%),非近視組453例(43.85%)。近視組的年齡、身高、父親近視、母親近視、父母配鏡年齡、甜食習慣、閱讀習慣、平均每日使用手機及平板時間、平均每日寫作業時間、平均每天戶外活動時間、閱讀姿勢、平均每天睡眠時間、寫字姿勢與對照組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組間性別、體重、飲食習慣、隔代親屬近視情況、父母教育程度、父母生育年齡等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人群各項指標比較
2.影響近視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近視組和非近視組單因素分析P<0.1的變量(年齡、身高、父親近視、母親近視、甜食習慣、閱讀習慣、用眼情況、睡眠情況、閱讀姿勢)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采用變量輸入法,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

表2 影響近視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建立Nomogram列線圖預測模型
本研究基于是否發生近視為因變量,以多因素logistic回歸篩選的變量作為預測變量,R軟件進行Nomogram分析,各因素不同數值對應的評分見圖1,計算各因素評分的總分,總分的范圍為62~340分,對應的風險率范圍為0.1~0.95;總分越高發生近視的風險越大。

圖1 近視發生風險的 Nomogram 分析圖
4.受試者工作曲線(ROC)分析
根據Nomogram分析結果,進行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風險總分的預測能力曲線下面積(AUC)為0.719(95%CI:0.688~0.750),本研究Nomogram模型的精準度和區分度尚可,見圖2。

圖2 Nomogram模型預測近視的ROC曲線
5.內部效度分析
本模型的Hosmer-Lemeshow test擬合優度檢驗P=0.027,提示模型的預測概率與實測概率存在一定的差異,仍需高質量大樣本的流行病學調查提高模型是預測能力,本研究使用bootstrap內部驗證法對該模型進行驗證,重抽樣1000次,校正后的AUC為0.695,校準曲線驗證圖見圖3。

圖3 Nomogram模型預測近視風險的驗證圖
討 論
近視是最常見的需要治療的疾病,臨床近視的治療方法,大多數是光學矯正,而限制其進展的效果還在研究中。目前對近視的機制研究歸納為遺傳(內因)和環境(外因)兩大類,兩者相加超過一定的閾值即會發病,個體發生近視眼與否,可能與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均相關,或是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從遺傳和環境兩方面因素進行這項研究,目的是為近視防治提供證據。
本研究調查12~18歲青少年人群的臨床資料,發現12~18歲青少年近視的發生率為56.15%,與2018年調查的結果(53.6%)相接近[3]。陸軍等通過構建多狀態馬爾可夫模型預測顯示,至2030年我國6~18歲學生近視眼患病率將為61.8%(55.4%~69.5%),初中81.3%(72.6%~91.0%),高中90.5%(82.4%~96.7%),若無有效干預措施,未來10年我國近視眼患病率將持續上升,但是此項研究未對近視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10]。通過分析其近視相關因素和健康行為,單因素分析篩選出近視的影響因素13個:年齡、身高、父親近視、母親近視、父母配鏡年齡、甜食習慣、閱讀習慣、平均每日使用手機及平板時間、平均每日寫作業時間、平均每天戶外活動時間、閱讀姿勢、平均每天睡眠時間、寫字姿勢。與謝東成等[11-12]研究調查的部分近視危險因素相似。
本研究進一步以單因素分析的9個變量(年齡、身高、父親近視、母親近視、甜食習慣、不良閱讀習慣、平均每日使用手機及平板時間、閱讀姿勢、睡眠情況)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年齡越高患近視風險越大(OR=1.129,95% CI:1.040~1.225),符合人眼屈光狀態發育的規律,青春期人群近視增多的特點[13]。平均每日使用手機及平板時間等將增加近視的風險,表明控制長時間視近行為是預防近視的有效措施。不良的閱讀習慣,如在光源差的環境下閱讀、躺著閱讀、以及其他不良用眼習慣等因素對近視的發生有促進作用,而正確的閱讀姿勢則是保護因素[14-15]。有研究顯示,增加戶外活動可以減少近視的發生[16-17]。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平均每天戶外活動時間可以減少近視發生的風險,而卻未能進入此研究回歸模型,原因可能是影響視力的不完全是一次戶外活動時間長短,而應考慮戶外活動的頻率。營養充足是保證青少年眼球正常發育的重要因素,而有關調查證明營養不良學生的視力不良率相對較高[14]。然而,在本研究單因素分析中,除喜甜食習慣者近視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外,其他方面不同飲食習慣者,近視差別無統計學意義。可能是這些條目的設計與近視關聯不是很密切,希望在后續研究中更加準確地量化標準來探索近視與飲食營養的相關性。
本研究采用的是橫斷面設計調查近視相關因素,可能存在學生和家長在回憶時一些具體日常行為的發生和持續時間存在偏差而出現回顧性偏倚。另外,由于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的用眼情況復雜交錯,問卷調查難以做到具體且全面。本次研究中12~18歲人群的各種用眼狀況以及行為的變化和發展的動態沒能全面覆蓋,還需要更多的觀察,進一步研究進而提供更可靠的結論。
本研究以是否發生近視為因變量,以多因素logistic回歸篩選的變量作為預測變量,建立Nomogram列線圖預測模型。國內外一些研究在logistic 回歸等模型基礎上建立了不同疾病的生存概率列線圖[18],也有應用于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預測[19],但應用于青少年近視的風險預測則鮮有報道。過去我們通常應用logistic回歸等方法評價青少年近視的危險因素,但不同危險因素對發病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本次調查研究在應用Nomogram模型預測12~18歲青少年的近視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各因素對應不同數值的評分,計算各因素評分的總分,總分越高發生近視的風險越大,此模型預測風險能力為0.719(95%CI:0.688~0.750),使用bootstrap內部驗證法對該模型進行驗證,校準曲線趨近于標準直線,實測值與預測值基本一致,說明本研究的Nomogram預測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能力,有一定的臨床價值。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列線圖中子代發病風險并不是隨著父親近視度數增加而增加的,可能是父親近視≥600度的樣本量較少引起的;其次,此模型采用內部驗證法,未進行外部驗證,因此應從建立新生兒眼病檔案開始,結合既往研究,運用多中心大樣本進行驗證,逐步優化篩選有臨床和統計學意義的預測因素,以期為不同的人群(如小學生、學齡前兒童) 提供更為實用、精確的預測模型,從而有效地應用于近視的個性化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