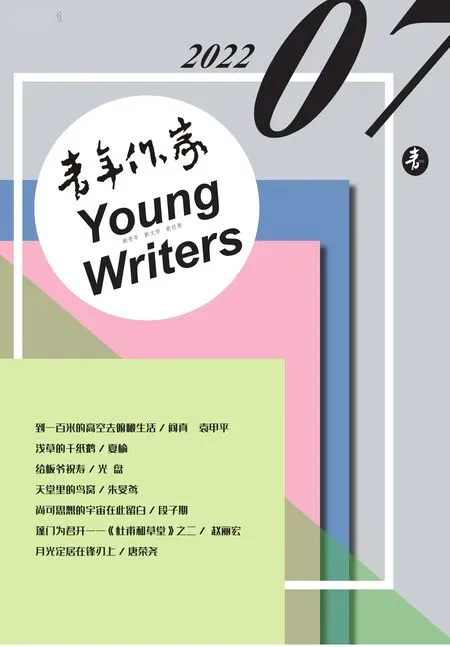牛錄往事
郭曉亮
外公家距離牛錄最北端的果園走路只需要二十來分鐘。連接它們的是一條落滿新鮮牛糞、馬糞的橫穿牛錄的大馬路。四月的最后一個早晨,我的蘇花表姐由南向北走在這條馬路中央。她身上穿著具有那個年代標志性特征的一身綠裝,腰間扎著寬腰帶,小小的個頭,長著一張粉白的圓臉。當她邁著碎步向前走去時,頭發后面的兩支小辮子,一甩一甩的,煞是好看。蘇花表姐這一年滿十八歲,她中學畢業下鄉來牛錄接受再教育,被生產隊分配到果園里勞動。果園里不但生長有種類繁多的果樹,而且在果樹下面的地里,還種著西瓜、甜瓜、梨瓜一類作物。果園的四周有著近兩米高的干打擂土圍墻,春天的這個時候,越過圍墻,遠遠地就能看見,果園里開滿白色、粉色或者是桃紅色花朵的那些杏樹、桃樹。它們成排成行,列成隊列郁郁蔥蔥地出現在走向它們的人的視野中,分外賞心悅目。今天是蘇花表姐去果園參加勞動的第一天,為了給在果園里勞動的生產隊其他社員留個好印象,她特意穿成現在這個樣子。它們至少在那個年代看上去,顯得十分的時尚、活潑、干練。當然,從南疆大城市喀什來到地處邊遠的牛錄,接受農村生活對蘇華表姐而言,完全是自愿。因為在當時,她是響應號召走出校園的。作為千百萬知識青年中的一員,表姐堅信:走出校園,走進鄉村就是人生美好的開始。如今她抬頭挺胸走在這條散發著牛糞味、馬糞味以及塵土氣息的牛錄的大馬路上,已經預感到自己正一步一步在邁向那理想中的廣闊天地了。
晚飯后,蘇花表姐坐在葡萄架下面的小板凳上一直在唱歌。我聽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覺得她的聲音好聽。我用右腿支撐著自己,把身子斜靠在大院盡頭的柵欄上,一邊聽她唱歌,一邊吃著手里的蘋果。有幾只麻雀停在牲口棚的草垛子上,在瞅著我。一只麻雀飛下來,鉆進牲口棚里邊的鳥窩里。在蘇花表姐唱完第四支歌時,天色朦朧下來,穿在蘇花表姐身上的短袖花襯衣,因暮色而顯得更加好看。我扔掉手中吃剩的蘋果核,走進外公家的屋子去,也取了個小板凳,繞到葡萄架的另一頭,坐下來繼續聽蘇花表姐唱歌。“過來呀!小亮,干嘛坐那么遠呢!”蘇花表姐突然大聲說起話來,要我坐到她身邊去。我提著凳子走過去,靜靜地坐下。我聽到蘇花表姐在咯咯地笑,她一臉開心的樣子。“你喜歡聽我唱歌嗎?”她問。“喜歡。”我說。“能聽懂唱的什么嗎?”她又問。我搖搖頭。她再次咯咯地笑起來,而且笑著從坐的地方站起來。我覺得她笑的樣子也好看。笑聲停止了,蘇花表姐哼著曲子,展開雙臂,開始擺出舞蹈的動作。她在那里哼著曲子慢慢跳起來,她的花襯衣,隨著她在轉動,我呆呆地看著她,看著她如同一枚柔軟修長的羽毛在飄逸、在綻放。天色完全黑下來了,夜來到葡萄架下。夜經過蘇花表姐的臉、手臂、哼著的曲子,遮蔽了我的視線。現在,我只能盲著雙眼,聽她舞蹈了。啊,長長的夜,在那個地方快速生長著,生長出它全部的黑暗。
通向果園的那片天空遠遠地敞開著,月亮和世界隱身于牛錄下方的黑暗中。夜鳥飛過的風呼呼作響,我的一個耳郭探進風刮過去的黑暗里,傾聽樹林中發出一種陌生的聲音。那里有一扇窗戶,忽閃忽閃地從果園里透出一束燈光。燈光向黑夜環視,樹林變得更加昏暗了,離開果園近一點的鄉道上,有一個人影在走。現在已經是秋天,天氣依舊很熱,夜深時難以入眠的兩個女孩,正靜靜地坐在果園的土屋里。一個女孩手捧著一本書聚精會神地讀著,另一個女孩面對面坐在木板床邊織毛衣,掉到地上的毛線團不停滾來滾去,滾進了床下邊的黑暗里。“歇一會兒吧,蘇花。”織毛衣的女孩抬起頭來沖著對面的另一個女孩說。叫蘇花的女孩合上書靜靜地瞧著窗外,果園里一片寂靜,不時有一只蝙蝠從窗前橫飛過去,劃過空蕩蕩的夜空。“今天是我來一牛錄果園勞動的第60天了,時間過得好快呀。”蘇花看著窗外若有所思地說。從她的眼神中能看出來,她的思緒已經飄向遠方,她在思念遠在南疆的父母。“蘇花,你都記著呢,想家了吧?”織毛衣的女孩說。“有一點。有一點。”蘇花柔聲細語地說,聲調低低的,多少有一點凄涼的感覺。“你可以向大隊請個假,回家看看父母。”“是的,我準備過了八月就請假回一趟家。”就在說話的當兒,蘇花聽到屋外有嚓嚓的腳步聲,腳步聲貼著地面清晰地傳過來,蘇花機警地挺直身子看向那里。但是,夜幕像一面厚重的墻擋住了她的視線。除了越來越近的腳步聲,一切都是黑洞洞的、靜悄悄的。“梅芳,我聽到有人走過來了。”蘇花回過頭來朝織毛衣的女孩說。“真的嗎?這么晚了什么人會來呢?”織毛衣的女孩起身靠近蘇花,倆人一同望著屋外。隨著心跳,嚓嚓嚓的腳步聲越來越近,黑暗中終于出現一個男人的輪廓,男人邁著八字步不緊不慢地走來。“是民兵隊長佟林,好像還背著槍呢。”叫梅芳的女孩子口對著蘇花的耳朵小聲說。“夜里他來果園干什么?”“是來巡邏的吧。”“以前不都是白天來的嗎?今天怎么夜里來了?我有點討厭他。”“我也是。自從他當了民兵隊長,整天背著一支槍在女孩子周圍轉游。”說話間,一個男人的影子走到了屋前,果然是民兵隊長佟林,右肩上背著那支長長的步槍。他在屋外停了一會兒,從肩上取下步槍伸了個懶腰,又朝前走了幾步,咚咚咚地敲門了。
門被向外推開了。黑魆魆的夜和一個男人的影子涌進屋內。站在明閃閃的燈光中面對兩個女孩直逼的目光,民兵隊長佟林多少顯得有點緊張和不知所措。他先是把手中的步槍立在靠門邊的墻角,又迅速地整理了一遍扎在腰間寬皮帶下面的衣角,然后滿臉通紅地沖著蘇花和梅芳張開嘴想說什么卻沒能說出來。“佟林,這么晚了你來果園干什么?”梅芳帶著不歡迎的口氣詢問道。“我在巡邏,過來看看你們。”佟林的表情不太自然。“有什么好看的,我們要睡了,你走吧。”梅芳的聲音尖尖的,音量十足。“讓我坐下休息一會兒不行嗎?我口渴了,請給一碗水喝。”佟林猶猶豫豫地說,并且用眼睛掃視了一遍屋子。這是一間坐南朝北的土房子,南面墻的中間位置有一扇大窗戶,緊挨著窗戶的兩邊各放著一張床,蘇花和梅芳就站在窗戶的前面。佟林瞧見屋子里面正對著窗戶的墻邊放著一把椅子,便走過去要坐下。“誰讓你坐下了?我已經說了我們要睡了,你趕緊走吧!”梅芳氣呼呼地趕過去叫住了他。佟林顯得十分尷尬,身子被地面吸住了似的僵持在那里。“算了吧梅芳,讓他坐下。”蘇花心軟,不忍心立刻趕佟林走,她走出屋子從外面端了一碗涼水給佟林喝。“還是蘇花妹妹好!”佟林笑嘻嘻地說著,接過蘇花手中的碗將水咕咚咕咚地喝了個精光。這時佟林已經坐到那把椅子上,臉上還堆著未散盡的笑容。蘇花和梅芳都不再理他,各自坐到兩邊的床上分別看起書和織毛衣。三個人就這樣默不作聲地坐了足足有十分鐘,顯然佟林心里也清楚現在兩個女孩都不愿理自己,但他又不甘心馬上離開。于是取過來立在墻角的那支步槍,坐在椅子上玩起了它。他不停地拉開槍栓又合上,弄出咔嚓咔嚓的響聲,而且槍口隨著擺弄轉來轉去,不時地對準坐在床上的兩個女孩。“佟林,不要在屋里擺弄槍!要擺弄到外面去!”梅芳大聲沖佟林喊,并且站起身躲開了槍口。佟林并沒有立刻停下,只是動作幅度稍稍小了一些。“蘇花,快離開那里!槍口老是對著你呢!”梅芳高聲喚著蘇花。蘇花這才合上書本要站起身來。就在這時候,“砰”的一聲,佟林手中黑洞洞的槍口突然發出可怕的聲音。槍走火了!剛從床沿半站起身的蘇花,尖叫了一聲便痛苦地倒在床上。躲在另一邊的梅芳霎時完全給嚇呆了,大張開嘴雙腿一軟癱坐在地上。
風從指尖上滑過去,帶走了牛錄的夏天。一只蝙蝠緊貼著房檐飛過,在我的視野里留下空洞洞的夜晚。草叢里的蛙鳴消失了,一動不動的白楊樹站在我走過的小渠邊上,白楊樹的葉子隨著我的腳步在飄動。我的身旁還有風給村落上方吹來的土地氣息。我感覺到我的身子很輕,輕得仿佛沒有了骨架和肉身在走路。又長又彎曲的土路,我看不見自己的影子,也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我的呼吸把我帶到了村邊的一排房子前,這里有大片的陰影和亂糟糟的狗叫聲。陰影中一盞馬燈被一只手點亮了,燈光照出了由一匹馬套著的一輛兩輪馬車,馬車上躺著痛苦呻吟的蘇花表姐,蘇花表姐的身上蓋著一床被子,被子上面有大塊鮮紅的血跡。馬車周圍人影晃動,一張張表情極度緊張的臉,我看見大哥和二哥,以及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大隊民兵隊長富林,另一個是木鄧保的三哥木力克。二哥的手中牽著馬的韁繩,民兵隊長手提馬燈垂頭站在馬車的另一邊,大哥和木力克坐在馬車上一左一右扶著蘇花表姐的身子。二哥使勁拽了一下韁繩,馬拉著馬車開始快速向前行進。馬車頂著死黑的夜色行進,滿是車轍的石子路,我的影子靜靜地跟隨馬車移動。拋在后面的亂糟糟的狗叫聲漸漸遠去,馬車走過了一戶又一戶人家,走過了一個又一個路口,很快從一牛錄走進三牛錄地界。我的影子靜靜地跟隨馬車移動,我的目光盯著躺在馬車上的蘇花表姐的身子。我能想象到那里有一個疼痛的深淵,我能感覺到它的深度,它像旋渦一樣包裹住了蘇花表姐嬌小的身子,死亡在一步步走近。死亡的前頭是一盞馬燈顫顫巍巍地跟著踉蹌的時間走向夜的深處,夜是那樣的死寂和空茫。
大哥額頭上的皮膚在顫動。汗珠從那里一粒粒冒出來,順著臉頰向下滾落。“堅持住!蘇花妹妹。馬車很快會把你拉到六牛錄的,六牛錄有縣上的大醫院,你的槍傷會被救治好的。”坐在馬車上的大哥俯下身子,臉對著蘇花表姐在安撫。蘇花表姐臉色蒼白,嘴中不斷地發出呻吟聲,而且伴隨馬車的加速行進,呻吟聲在加劇。她的一雙眼睛一直睜著,有幾次沖著大哥說:“我要死了嗎?我不想死啊!”馬車在筆直的鄉路上行進,路兩邊是連片的玉米地,民兵隊長佟林手提著馬燈在前方引路,二哥手中緊緊地抓著韁繩專注地駕著馬車,車轱轆的每一次轉動都揪著他的心跳。二哥努力地把馬車趕得平穩些,再平穩些,以減輕因馬車顛簸給蘇花表姐帶來的痛苦。架在車轅里的馬是一匹棗紅色母馬,馬的鼻孔里不時發出噗噗的響聲,聽上去好像在打噴嚏。夜幕中有股氣流,忽前忽后地圍著馬車流動,給人一種不祥的幻覺。我的影子依舊跟著馬車移動,像條甩不掉的尾巴。這時前方傳來汪汪的狗叫聲,狗的叫聲提示我們前方就是四牛錄。黑乎乎的玉米地盡頭出現了高高的土城墻,城墻下面立著幾間房子,馬車趕到時一只大狗跑出來發瘋似地狂叫。人和馬車繼續前行,穿過了四牛錄的城門,然后又穿過了沉睡的四牛錄。“富林,快把馬燈提過來!”這時馬車上的大哥朝前邊的民兵隊長喊了一聲。馬車停下來,民兵隊長佟林小跑過來,把馬燈舉起交給車上的木力克,木力克接過馬燈照在蘇花表姐的臉上。蘇花表姐的雙眼緊閉著,她的臉不再是慘白慘白的了,而是變得鐵青鐵青,而且整個身子在不停抽動著,每抽動一下她的嘴里都要傳出呼呼的聲音。“蘇花妹妹,蘇花妹妹,醒一醒!你睜開眼睛看元兒哥一眼好嗎?”大哥雙手抱著蘇花表姐的頭在喊。喊聲從馬車上方傳過去,在黑茫茫的夜空中傳向曠野的深處。
馬車周圍全是夜的深淵。夜無法愈合的傷口也在流血,大面積潰爛。僵硬的道路和無邊無際的秋夜,死亡又向前靠近一步。大哥的喊聲終于使蘇花表姐慢慢地蘇醒過來,睜開了眼睛。但是她的呼吸是那樣微弱,微微張開的嘴幾乎發不出聲音來,過了半晌才斷斷續續地說出一句:“我……不行了,你們……把我……送回……去吧。”大哥終于抑制不住悲痛哽咽起來,眼淚撲騰撲騰地往下掉,他輕輕地用雙手抬起蘇花表姐的頭,放在自己的懷里,泣不成聲地對木力克和二哥說:“人已經不行了,怎么辦?六牛錄還遠著呢,繼續往前走嗎?”木力克伸手摸了摸蘇華表姐的兩只手和腳,發現都是冰涼冰涼的,他搖了搖頭說:“是不行了,不能再往前走了,那樣會讓蘇花受更多的罪。”二哥則發愣似地站在馬車旁,一個勁搖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民兵隊長富林開始全身哆嗦,已經癱坐在地上,全然像瞬間枯萎了一樣。這當兒,先前那股前后轉著圈在馬車四周竄動的氣流,已經停止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夜頓時變得萬分沉悶、壓抑,讓人透不過氣來。腳下的大地仿佛突然間像陀螺似地轉動起來,而且轉速越來越快、越來越劇烈,這讓受到驚嚇的我,感到毛發聳立,毛孔全部張開了,太陽穴上的血管也都鼓起來,撲通撲通地跳動。是的,在這個時間里,一切都變得令人窒息和絕望。經過內心一番極其痛苦的爭斗之后,大哥使出全身的力量向二哥擺擺手,說:“回去。”二哥拽住韁繩讓馬慢慢地掉轉身子,馬車在鄉路上原地轉了個圈,開始往回走。深深的夜幕中,躺在馬車上的蘇華表姐的身子在變小、變小,小到漸漸地變成一個黑點,看不見了。
夜靜得可怕。黑暗中只有馬蹄和車轱轆在路面上踩壓出的響聲。我看不見腳下的路面和土地,但我能聞到一股陰陰的死亡味道。鄉野是古老的,莊稼地被黑夜淹沒了。四下里飄動的是黑乎乎密麻麻的死亡的影子。當馬車再次穿過四牛錄時,蘇花表姐的呼吸完全停止了,她離去時的面容和神態很平靜,如同剛剛睡著了一樣。大哥依舊在懷里緊緊地抱著她的頭,并用一只手輕柔地撫摸她的臉。“好妹妹呀,怎么說走就走了?”木力克終于按捺不住,雙眼含著淚花說。他把身子猛地轉向前方的佟林,伸出右手指著佟林吼著說道:“佟林!都是你害死了蘇花妹妹!當了民兵隊長很了不起,是嗎?你成天拿著一支槍到處炫耀。如果不是你他媽的夜里在果園里玩槍,那槍能走火打著蘇花妹妹嗎?”佟林黑黑的身子提著馬燈,直呆呆地走著,沉得像一根木頭。馬車行進三牛錄地界時,牛錄的公雞開始三三兩兩地叫了,這時大哥挪動身子,把蘇花表姐的頭輕輕放下來,放在起先枕著的枕頭上,接著和木力克攜手把蘇花表姐的身子在馬車中間擺正、擺平,這個時候蘇花表姐的眼睛是睜著的,大哥用手掌緩緩地撫閉了它們。
在一個陌生的黎明,你不用心看或聽,就能感受到你周圍發生的事情。當你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看見一群男人簇擁著一輛馬車走進外公家大院時,惶恐和絕望便已經牢牢地占有了你的內心。在這個黎明,首先打破平靜的是女人們的哭聲,外婆、二嫂和街坊幾個姨姨輩的女人迎著馬車撕心裂肺的哭聲,很快沖出院子,傳向牛錄的每個角落。哭聲引來更多的族人,他們絡繹不絕地走進外公家的院子,個個表情凝重悲傷。尤其是女人們趕來時,都要先進屋去探望外婆,然后在里面哭成一片,我在院子外面能聽見她們談話和走動的聲音。門板一直咣當地響著,談話聲和哭聲交織在一起,如同無數布條撕碎的聲音,帶給你渾身針扎般的痛苦。男人們進了院子就忙了起來。他們和大哥、二哥一同,很快在長廊一樣的葡萄架下七手八腳地用長凳和木板搭起一個長方形的平臺,平臺上鋪上了干凈的褥子枕頭,蘇花表姐被抬到平臺上,然后男人們散開,退到院子的另一頭。屋里的女人們出來了,外婆帶著她們開始給蘇花表姐擦洗身子,哭聲再次響成一片。“蘇花啊!你小小的年紀怎么說走就走了?往后的日子叫我如何受得了!”外婆一遍遍重復地說著這句話,說著說著突然一陣眩暈就要倒下去,幸好有大姐攙扶著才沒讓她倒在地上。外婆依舊堅持守在蘇花表姐的身邊,女人們擦洗完身子給蘇花表姐穿上新衣褲和鞋子,整個過程莊重而肅穆。之后,女人們又給蘇花表姐的臉上蓋上一塊白布,身上蓋上一大塊黑布,然后都靜靜地守在一旁,等著給死去的人出殯。